外滩美术馆以新展“再·再”重开,再定义“后美术馆时代”的艺术体验
2021年10月中旬,外滩美术馆结束了自2019年底起的闭馆翻修阶段,再次向公众开放,并推出了瑞士艺术家约翰·阿姆莱德(John Armleder)在中国举行的首次大型个展“再·再”(Again, Just Again)。
11年前,当上海当代艺术机构进入萌芽发展时期时,外滩美术馆在前身为上海亚洲文会大楼的虎丘路20号亮相。首个展览“蔡国强:农民达芬奇”的现场,美术馆整面外墙上写着大大的“不知该如何降下”,在周围民居和空旷的广场的衬托下显得有些突兀又像是某种宣言。

外滩美术馆外景,图片来源:外滩美术馆
在“降落“后的十多年间,美术馆曾先后推出了蔡国强、陈箴、宋冬、林天苗、马克·布拉福德(Mark Bradford)、波拉·彼薇(Paola Pivi)、菲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Felix Gonzalez-Torres)等重要中外艺术家的个展,同时也展出过“日以继夜”、“百物曲”、“告诉我一个故事”和”Highlight”等一系列关注亚洲地区议题或以美术馆场域为基础进行现场创作表演的展览。


约翰·阿姆莱德肖像,图片来源:Annik Wetter

"再,再"展览现场,图片来源:外滩美术馆
乘坐电梯直达五楼后,蓝色和黄色圆点装饰的墙面、镜面迪斯科球转动时留下的斑驳光影以及四周墙上和玻璃柜内展示的手稿、海报、出版物以及迷你尺寸的玩偶装置,让人一下子很难掌握关于这次展览的信息,如同在观看好几个艺术家的创作合集。这也符合艺术家约翰·阿姆莱德五十多年来创作的一贯特色:他的拥有着艺术家、策展人、出版商、画廊主等多重创作身份;如果硬要对他的作品进行细分,可以从中看到达达主义、极简主义、超现实、激浪派、新几何主义等各种艺术运动的特征不时出现。阿姆莱德曾在和《Artforum》的访谈中表示:“我一直很喜欢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归在哪个新的艺术运动中,即便贴上的标签有很严格的限定,或者某个运动只是一时的风潮。但在我看来,正是这样的断言才让作品发生改变。每当有新的理解产生时,作品就被打开了一个新的维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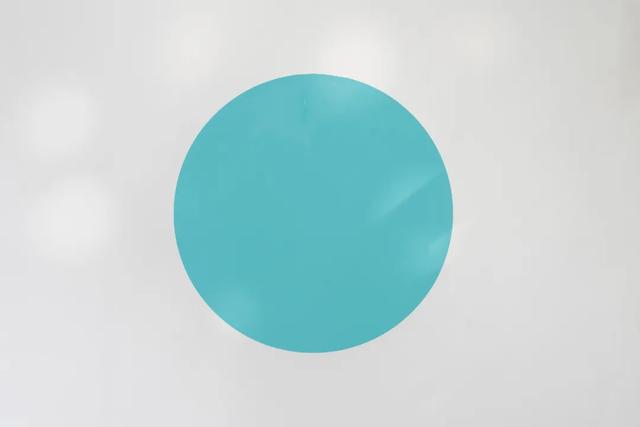
约翰·阿姆莱德,《无题》(特定场域墙面绘画),2021年,图片来源:艺术家

《闪烁》与《粉末》系列在展览现场,图片来源:外滩美术馆
作为当代艺术界独具影响力的人物,来自日内瓦的约翰·阿姆莱德在不同身份与艺术领域中实践。他的创作横跨素描、绘画、行为、装置、声音、写作和合作型艺术,在种种机缘下结识了约翰·凯奇后,受到激浪派精神的影响成立了艺术探索实践小组ECART (écart 在法语中意为“间隙”、“分歧”)及同名替代性空间,策划组织了一系列与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的多元而深入的合作,包括约瑟夫·博伊斯和安迪·沃霍尔等。在开放与合作外,阿姆莱德选择拥抱偶然,在创作中坚持避免各种形式的掌控,将艺术行为授权给观众。

约翰·阿姆莱德,《de M&GH》,2015年,图片来源:艺术家和MASSIMODECARLO

"再,再"展览现场,图片来源:外滩美术馆
这次的展览似乎也有意将最大的解释权交给观众。策展人拉瑞斯·弗洛乔(Larys Frogier)并没有按照时间、艺术风格或媒介来归类阿姆莱德的作品。外滩美术馆的资深策展人曾明俊(Billy Tang)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把每一层展厅都视作一个舞台布景,各种规模和年份的艺术品都像装置艺术一样呈现,可被视为一个新的集体,而不是孤立的。”例如带有蝴蝶图案的邮票,被装在墙上的一个玻璃框里,用制作标本的方法用大头针把邮票定在了盒底,下方的玻璃陈列柜里则摆放着各种ECART的出版物以及被封在一个塑料包里的小人偶。物品变成了一个个符号,被抹去了原有的信息,像是被重新编排过的乐曲由观众来自行品味。


"再,再"展览现场,图片来源:外滩美术馆
戏剧式的展览呈现在三楼再次得以凸显。由艺术家发起、摄影师张家诚负责布景的《虎丘公园》里,拱廊下的长凳、熊猫外形的垃圾桶以及公园中心的假山和塑胶健身跑道将整个楼面改造成了带有上世纪90年代风格的中式公园。阿姆莱德著名的雕塑系列《蓝色约翰(氟)》突兀地出现在布景中,蓝色沙发与墙上的彩色圆点绘画组成了家中常见的客厅景象。艺术家在此探讨了本作为艺术品的绘画被挂在墙上后,转变为装饰性的家具之一。


"再,再"展览现场,图片来源:外滩美术馆

约翰·阿姆莱德,《155家具雕塑》,1987年,图片来源:艺术家
这种对于物的意义的转变、对于艺术和设计边界的探讨,也延伸到了二楼展厅里一系列家具设计和绘画共同组成的大型现场装置。几幅色彩明快丰富、画面肆意自由并带有各种现成物拼贴的综合绘画作品中,阿姆莱德用浇注和飞溅颜料的方式,抛弃了传统绘画工具的使用,将画面的颜色、纹理和形式定义为一个偶发的结果。

约翰·阿姆莱德,《加里奥克》,2021年,图片来源:艺术家

约翰·阿姆莱德,《玫瑰河岸》,2021年,图片来源:艺术家
根据外滩美术馆副馆长刘迎九的介绍,阿姆莱德在绘画上的突破也是这次展览的出发点,美术馆能够借此来探讨绘画这种媒介和实践在艺术中的可能性。而曾明俊则表示:“阿姆莱德突破各种边界的创作,注重众人分享的创作自由,也是美术馆DNA的一种体现——让本土和区域性的观众一起加入到展览中,形成新的知识、生产出独特的知识框架。”然而,如何呈现这样一场偏重西方艺术知识背景、对观看方式实则有一定要求的展览,是否会造成水土不服或是能将信息有效传递给本土观众,则对美术馆的相应公教项目策划提出了一定的挑战。

回顾成立至今美术馆在展览和公教活动策划的转变,外滩美术馆副馆长刘迎九在接受《艺术新闻/中文版》采访时表示:“外滩美术馆在各个阶段的使命一直在改变,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实践来定义美术馆。比如在美术馆初期会着重艺术家的在地创作,支持艺术家完成难以实现的大胆尝试;而到了2016年左右,随着上海乃至全国越来越多私人美术馆的兴起、国际艺术家的大型个展纷纷涌现,外滩美术馆则转向精细化的打造,结合美术馆合理的空间大小,策划一些体量不大但可以让观众深度观看体验的展览。如今,美术馆在处于‘后美术馆’时期,我们的理念就是要跨越美术馆在传统语境下的实体存在,以不同形式和形态出现在各个地方,并深度根植于当地的历史和文化。”

"帘幕"展览现场,图片来源:香港Para Site艺术空间
除了陆续推出西方艺术家的个展,从2017年左右开始,外滩美术馆的多个展览和研究项目如“百物曲”、“亚洲策展实践”等将重点放在了对亚洲问题的探讨以及对影像创作的关注,通过艺术作品中有关亚洲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的现实,让大家对这个地方有更为细腻和丰富的认识。而在美术馆翻新期间,他们也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当代艺术中心展开的驻地研究计划,以及与香港的Para Site共同策划了群展“帘幕”,并开展为期三年的同名长期研究项目,展开跨机构合作、拓展与艺术家的对话并发起线上平台,以促进多元的公众参与。
在以“亚洲”为焦点的研究与实践之外,曾明俊还透露,年底美术馆将与非盈利艺术机构黄边站合作,委任年轻艺术家谭晶呈现有关华侨的研究。这种机构之间的合作也开启了外滩美术馆在新的实践方面的探索,在碰撞中获得失败的教训或是新的能量,从而打破自己观念上的局限和做法。此次美术馆空间的升级也进一步地体现了其对于延展公共性的尝试。

步入重新开放后的外滩美术馆一楼大厅,原本被简单分为售票和商店两部分的空间,如今被曲线形的木质长凳、商品展台以及弧线形柜台所取代,柔化原本的建筑风格及空间气氛。观众在大厅四周浏览美术馆商品之余也能在位于中间的开放式问询处得到需要的帮助。动线更丰富、空间更紧密的感觉也体现在六楼的美术馆咖啡厅里。
谈到这次的空间改造特色,刘迎九表示:“这次一楼和六楼的公共空间改造最为明显,用交错的曲线代替了原来偏极简的直线形动线。希望借此一方面让观众的体验更为丰富,不再觉得美术馆只是一个快速消费艺术的停留,而是有更多的停留。同时,美术馆工作人员的工作方式也会发生变化,不再只是坐在柜台后面,而是通过开放的柜台和观众有直接的交流,这样参观体验也会不同。”

美术馆六层与七层空间,图片来源:外滩美术馆
在天气适宜的时候,美术馆新开辟出来的七楼露台也成为了一个新的时公共社交场合,配置有简单的木质长凳和几片小菜园。登上露台后,四周正在维护中的历史保护建筑、已翻新完成的半岛酒店和前身为中国实业银行总部的中实大楼,以及另一侧带着统一砖色斜顶的矮公房尽收眼底,也令人真实地感受到美术馆所处的这片地区无时无刻正在发生的改变。从电梯间旁俯视,能够看到正在施工的广场区域与为LED大屏所预留的墙面空间,让人对新的公共艺术通道充满期待。
曾明俊也提到,美术馆的动线改变后,也为策展人打开了更多角度,增加了利用场馆内外空间的可能性。而从与社区的联动来看,外滩美术馆历来通过“夜间美术馆”、公共艺术系列论坛、“客堂间”等多个公教项目,把美术馆的实践搬到了场馆附近的几个空间内,对外滩源的人文历史以及美术馆与公众间的关系做了不断的研究和探索。
刘迎九认为,随着外滩源片区的改造基本完成,观众今后还可以从圆明园路等小巷穿行至此,从美术馆另一侧广场的大电梯处直接进入场馆,打通了场馆前后的进出动线。近年来多家国内外画廊、拍卖行、书店及咖啡馆都先后在这里落户,形成了一个文化社区。美术馆这次的改造也顺应着这一变化,更为深入地与这里产生互动。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