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 | 从美术馆出走:做“社会雕塑”,为更多人服务
文/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实习生 陈晓楠
2022年1月4日,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新年首展《万言亦无声:生活的学术价值》开幕。这是首届“泛东南亚三年展”的第四个研究性展览项目,同期展出的还有《对于“参与式艺术”的两种回应》,以及《翻山越海:刘博智缅甸华人文化摄影展》。
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该系列展览展程过半,其中很特别的是,带来了以往国际展览中较少提及的“参与式艺术”的实践与成果。
该系列展览策划人之一、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陈晓阳是国内“参与式艺术”的实践者和推动者之一。近年来,她和她的同行在广东土地上进行了一系列“参与式艺术”实践,通过艺术家之眼,以人类学的方式,记录和留存华南大历史之下的小故事。

艺术家的“在地实验”
多年前,陈晓阳从美院雕塑系毕业。留校任教多年后,她转向人类学领域攻读博士学位。跨学科经验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当时,她对美术馆里的艺术作品产生了一些困惑:一些观众满怀期待走进美术馆的白盒子空间,面对那些或当代或传统的艺术作品,表示看不懂。有的艺术脱离了情境,很难产生影响力。
由此,陈晓阳在《中国雕塑》写了一篇文章,主张“从美术馆出走”。2008年,陈晓阳参与发起了“蓝田计划”。项目关注广州城中村和远郊乡村的传统民俗以及文化遗产,通过艺术家之眼,以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式,记录和留存华南大历史之下的小故事。
后来,“蓝田计划”团队的另一位发起人带她去看了沥滘村。在那个狭小、杂乱的城中村里,有十三间祠堂,令她印象深刻。他们带志愿者去做访谈和梳理,邀请村里的老人家绘制记忆地图。有一位老人讲到自己去周庄旅行时,眼见当地的小桥流水人家,念及风景旧曾谙:沥滘村原本也是这样的,可岭南水乡风情已不再。

这让陈晓阳感到一种文化震撼。他们想把这种发现告诉更多的人,于是邀请艺术家,以展览的方式讲述村落的故事。村委会和宗族里的热心人热情地资助了这个展览计划,修整其中最残破的祠堂作为“展厅”。
展览意外收获不错的社会反响。四座原本要被拆迁的明清祠堂,也因此得以保留下来。由此她更加相信,艺术的影响力不仅仅在美术馆。
回到美院后,陈晓阳在雕塑系开设一门名为“在地实验”的课程,引导学生走入社会、直面现场。其第一个实践项目选在大学城附近的南亭村,试图记录下一个800多年历史的村子在十年间迅速城市化的过程。
将休眠的文化唤醒
陈晓阳所在的雕塑系,可能是最早接受这种艺术转向的美院院系。
德国当代艺术家博伊斯提出“社会雕塑”,倡导艺术家主动走进社会,如同塑造石头、金属的外形一样去“塑造”身边的社会环境。自上世纪80年代,这种认识成为艺术界的一种思潮: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精英艺术,艺术同时也是面向大众的,可以为更多人服务。
“从杜尚开始,艺术已经完成了审美的任务,它更应该负起启发智识、重建其连接难于用文字和语言描述的感觉世界的功能。”陈晓阳说,随着“乡村建设”日益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参与到许多乡村社区的社会实践中,但“我们不画墙,要做一些看不见的东西,关注文化冰山的水下部分”。
从化北部的乐明村,村民不足千人。在这里,陈晓阳参与发起的“源美术馆”项目经过几年的实践后,却发现声音艺术比视觉艺术的传统更容易恢复。在传统山区村落,山歌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交媒介,它既是劳动与休闲互动的产物,也是纾解孤独、寻找对象的娱乐方式。这是山里人的艺术。
2018年,源美术馆项目邀请艺术家组合“西三歌队”来到乐明。他们被乐明山歌吸引,上山来与已经封嗓二十多年的本地“歌王”彻夜倾谈,了解山歌的腔调及歌词中讲述的山村生活,听“歌王”“歌后”们讲述当年通过山歌谈情说爱、排解忧愁的情境。

就此,乐队围绕村民的日常生活,重新创作了两首民谣《茶、酒、烟、蜜》和《条条水路》。而后驻地展开幕,在没有墙的山谷地坪上,中断了二十多年的乐明山歌,在西三歌队和村民的对唱中再次响起。
艺术家离开后,唱山歌的传统却如一夜春风来,在山上复生。陈晓阳介绍,如今微信上建立起了不少的山歌群,那些在城市打工的男女,在群里对歌,借此交友:“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见证到所谓中断的传统可能并没有完全丧失活力,通过艺术创造合适的场域,还可以将这些休眠的文化唤醒,重新回到社区中。”
广东是“参与式艺术”最活跃地区之一
近年来,陈晓阳重回“白盒子”,担任广美美术馆副馆长,将多年“在外”的思路和实践带回美术馆。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首届泛东南亚三年展序列研究展带来了诸多发生在越南、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与地区的相关艺术实践。
事实上,广东是当下“参与式艺术”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有官方艺术机构如广东美术馆,一直推动艺术进社区公教活动;也有民间艺术机构如时代美术馆,于2016年开始以“榕树头项目”召集艺术家与周边社区互动,等等。
老旧社区的“微改造”也将目光投向艺术项目。针对位于广州历史街区的旧南海县、盐运西和越秀洪桥街等社区,政府和各界机构通过公共艺术建筑、空间改造、教育活动、驻地工作坊等途径去提升社区的文化价值。

在网红打卡地东山口,与竹丝岗菜肉市场仅一墙之隔的扉美术馆,多年来持续推动艺术与社区的结合。从联手戴耘合作开展琶洲村“旧村改造×艺术拾遗”项目,再到宋冬策划的“无界艺术季”和徐坦的“农、林之路;竹、丝之岗”,都关注艺术对社区、城市发展的激活作用。
其中,《百家宴》《民众花园》等作品的参与度之高,使扉美术馆成为今日研究艺术介入社区的广州样本。
广州美术学院新美术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沈森认为,“艺术介入社区”作为一种艺术主动与社会沟通对话的当代文化现象,在广州尤为明显:“究其根本,一方面是为了改善广州虽在一线城市之列、却长期被边缘化的本土艺术生态;另一方面,这也与广州社区营造的需求密不可分,艺术和文化是一种与城市建设硬件条件相补充的互动机制。”
意外惊喜:关良后人看关良
“参与式艺术”固然让艺术家走出美术馆,同时也让美术馆得以“打开”,因此,戏剧也能成为美术馆的“主角”。
2020年岁末,广州粤剧院的演员们在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美术馆一楼大堂,开展一场别开生面的粤剧演出。在舞台旁展出的潮州木雕上,精细地记述着丰富的民间戏剧故事情景。
本次演出的观众中有不少是来自南亭村的村民,近代著名画家关良即出生于此。南亭村中至今保留着完好的关良故居和古老的关氏宗祠。
美术馆团队在田野调研中了解到,当地至今延续着年节庆典时观看粤剧的风俗,与关良的画作中常常出现“南亭”和“番禺关良”的印鉴相呼应,成为理解关良戏剧人物画的生动注脚。

团队更了解到,南亭村的关氏族人一直有个心愿,想看看同族大画家关良的原作真迹。由此,广美美术馆与顺德和美术馆的公共教育部合作,组织南亭村村民前往顺德,堪称“关良后人看关良”。
珠三角地区的美术馆通过馆际合作,推进了艺术参与社会连接与文化交流的创造性工作,促进观众、艺术家、机构与社区居民更有机、更深入地理解和互动。
在一年后的《对于“参与式艺术”的两种回应》中,观众甚至都可以参与到对作品的“再创作”。菲律宾艺术家施琳·赛诺在展厅中还原了一个保安室情景:工作台上放着日历、保温杯、对讲机、笔记本。
原本只是道具的笔记本,却被一些观众误以为是留言本,写下观展体会。而后来者“将错就错”,纷纷以保安的视角,用文字或插图,记叙下或真或伪的生活细节。
开展不到两周,笔记本已然是一本满满当当的“保安日记”。或许这就是“参与”带来的意外之喜。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访谈】
—— 在跨界中发掘艺术的更多可能性 ——

深入东南亚的田野调查
羊城晚报:为什么会策划“泛东南亚三年展”?
陈晓阳:我希望看到更多社会参与的艺术案例,一个很直接的想法就是去看我们的邻近地区。广东与东南亚关联密切,但以往国内对东南亚当代艺术的了解,往往是绕到欧美、日本去看。我们离得这么近,为什么不直接交流?如何看得更深入,更具体?参与式艺术就是一种进入的方式。
这就是我参与这个三年展策划的原因之一,希望可以打造一个直接交流的平台。这期间有不少有趣的发现,比如在开展这系列的国际学术论坛时,我们发现来自马来西亚的、来自新加坡的研究者和实践者都可以直接用国语交流,原来国际会议不一定要讲英文。在参与式项目中,我们发现东南亚和中国南方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我们对国际的理解,也在展览的个案中得以打开。有一个“庞克摇滚舍”的项目发现了当地木刻版画的传统,召集一个马来西亚村庄的居民一起创作,他们一同用脚踩印出一幅画作,试图缓解社区历史遗留的矛盾,将交织着冲突的村民转变为友善互助的社群。
这种深入的田野调查,也把我们的历史研究连接起来,看见原本不可见的东西,从而为木刻版画的海外历史做注脚。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对话和连接,将这个区域的主体性慢慢塑造出来。
就像以前我在一个社区做过的在地展览叫做“视而未见”。艺术是可以帮你开天眼的,去看见这些细微的东西,看见一种更整体的社会结构,看见各个板块之间的联系。

走出旧公共艺术同质化困境
羊城晚报:“参与式艺术”是如何进入本土的?
陈晓阳:参与式艺术这个概念,其实是在实践之后才慢慢提出来的。这种实践要求跨出艺术界。我因为跨学科的背景,所以是从人类学的视角和方法出发,把艺术的行动置放在社会情境中。
参与式艺术相信所有参与者都具有能动性。在当代艺术领域,博伊斯所说的“人人都是艺术家”也可以理解为:人人都有感知艺术的能力,这是人的天然属性。只是这种属性往往被一些刻板的观念遮蔽住了。
因此,在实践中最重要的是观看视角的转换。参与式艺术要求实践者放弃部分从自我出发的主位表达。
从上世纪60、70年代开始,世界各地都有参与式艺术实践发生,从拉美、欧美一直影响到亚洲的很多地区。到了90年代以后,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也有很多艺术家投入各种参与式实践中。那时候出现更多的是社区艺术,一种新类型公共艺术。
旧公共艺术比较常见的是城市雕塑,但城市雕塑的生成机制是自上而下的,往往由政府来规划。城市空间里到处都是举着球的女神雕塑,让人产生审美疲劳。公共艺术陷入同质化的困境。
而参与式的方法其实带来了一种新的公共艺术类型,这种公共艺术的创作和公共空间中的群体有密切关联。公众甚至可以参与到创作过程中,把想法汇聚其中,这是一种公共智慧。要相信“他者”的智慧。
后来有介入式艺术等概念。到了2015年之后,国内对一些相关实践的研究和翻译开始多了,就有更多的人参与这类项目的梳理和研究中。
之后,大家发现“参与式艺术”是一个能够比较合理地描述这一类事件的概念,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

羊城晚报:“参与式艺术”在各地的发展情况怎样?
陈晓阳:可以说在国内,广东的这些项目是最多样的,与不同的社团和机构合作,涵盖了不同年龄层的实践者。可能因为广东的教育系统跟港澳地区、日本的联系比较多,较早受到前沿理念的影响,所以保持在比较有活力的状态。从我现在做的几个区域来看,顺德的社会基础最好。福建、江西和河南也有类似的尝试,有一个很出名的例子是河南修武的大南坡项目。
艺术家擅长发现“无用”的东西
羊城晚报:艺术家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
陈晓阳:相较那些已经在进行社会实践的公益组织,艺术家更擅长看见“无用”的部分。因为艺术是闲暇之后的产物,首先它是“无用”的,但这种“无用”却能够抚慰人的精神世界。
中产人群会自主选择用艺术的方式来抚慰或者治愈自己,比如去听一场音乐会,去看一个画展。这在乡村原本也是有的,但后来中断了。
我们在乐明村调研多年,发现它有很好的文化传统。但因为资源匮乏,有些传统随着时间流逝渐渐式微。有一次,我们团队在垃圾堆里找到了一个废弃的角柜,很有装饰主义的风格,才发现原来村里有很好的木工传统。
有些东西从当下眼光来看是无用的,是已经消失的,但艺术家很擅长发现这些东西。后来,这被策划成一场名为“角柜计划”的展览。可能文化考古更多集中在物自身,而我们关注的是人。

羊城晚报: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越来越多地应用在艺术界,为什么?
陈晓阳:这是一种思潮。当代艺术的人类学转向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二战结束之后,后现代理论流行起来,人们开始反思西方中心主义。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方法刚好可以为当代艺术提供一种进入“他者”的视角。
从那个时候开始,艺术界开始关注到非西方的、非男性的艺术家。比如1989年在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一个叫“大地魔术师”的展览,有100位艺术家,50位来自于非西方地区。这可以看做是当代艺术人类学转向的重要标志。
在上世纪90年代,西方当代艺术活动中再次关注人类学所提倡的文化多元主义和跨文化对话。这样一种方法慢慢地流传到中国。到千禧年之后,人类学在艺术界变成一种显学。
同时,在上世纪70、80年代,其实也有一些欧美的人类学家跨界艺术,他们发现艺术是很好的传播媒介。人类学家也开始讨论民族志方法如何与艺术创作的表达协调。这种交流是双向的。

羊城晚报:您怎么看待这种趋势?
陈晓阳:国内的人类学界对当代艺术的关注是从乡村建设的参与式艺术开始的,两个学科自然而然地相遇了。我们希望这样的跨界交流和融合不会削弱各自的学科,而是从中发现更多的可能性。
这几天开展的国际学术论坛也在争论这个问题。有些人担心,其他学科进来了,会不会艺术史就没有用了?其实和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甚至医学等跨学科合作不会影响艺术研究,反而提供了很多新的视角和空间。
这也是我们要带来“泛东南亚三年展”的一个原因。我觉得目前所做的还不够多,其中的类型差异和多元的探索还需要再继续推进。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吴小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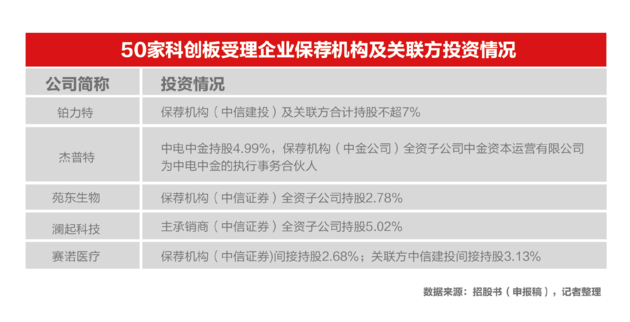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