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汉奇:一砖一瓦搭建新闻史学科大厦

方汉奇
学人小传
方汉奇,1926年生于北京,祖籍广东普宁。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1951年起先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从事中国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发起并创立了国内唯一的新闻传播学一级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其著作《中国近代报刊史》《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等影响了几代新闻传播学者;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及该委员会第四届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积极推动新闻传播学成为一级学科。
2021年11月10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举办“中国新闻史”课程与教材建设研讨会。95岁的方汉奇先生步入会议室时,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响起。掌声是对方先生的由衷敬意,更是真切祝贺。在9月26日国家教材委员会公布的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评选中,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第3版)荣获一等奖,是新闻传播类教材唯一的一等奖著作。本次研讨会的举办,正以此次获奖为契机。

《中国新闻传播史》 方汉奇/主编
《中国新闻传播史》初版于2002年,历经两次修订,为全国大多数新闻院校选用,影响了几代新闻学子,“直接嘉惠于学子,风行四海,无远弗届”。这本重量级教材,是方汉奇先生毕生的积累与心血。作为新闻史学家与新闻教育家,方汉奇筚路蓝缕、厚积薄发,为新中国新闻史学科发展筑牢根基、培育英才,以毕生之力一砖一瓦搭建起了新闻史学科大厦。
爱好集报,踏上新闻史研究之路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将中华民族逼至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平津危急!无数中国人的命运就此改变。当时方汉奇正在北京念小学,也不得不随家人开始逃难。迫于战乱,他频繁转学,全面抗战八年念了八所中学,尚且年少就已饱受流离之苦。
1944年,方汉奇转学至广东梅县的梅州中学念高二,遇到了一位过去在北京相识的长辈。这位长辈毕业于燕京大学,是方汉奇的姑姑方群凤的同班同学,本是梅州籍,当时在粤北一所小学教书。她的丈夫是北伐老四军的军长,已牺牲在抗日前线。
于战乱中得遇故旧,有其格外珍贵之处,而对方汉奇来说,更有另一番非凡意义。方汉奇到她家做客时,在藏书中发现了十来份旧报。当时的梅州,能够见到的报纸只有一两种。方汉奇在高一时曾担任班上的学习委员,负责办墙报,需要时时关注战争的信息并采访写稿。此时能看到这些出版于京沪一带的旧报,方汉奇自是爱不释手。长辈见方汉奇对旧报十分喜爱,就将这些报纸都送给了他。

《方汉奇自选集》
这是方汉奇所集的第一批报纸,这次做客也成为他集报爱好的开始。旧报上登载的人与事,虽已为陈迹,但邵飘萍、范长江等名记者的胸中丘壑、笔下风云,始终令方汉奇无比神往,他因此立志要考新闻系、做新闻记者。高中毕业时,方汉奇报考了几乎所有设立了新闻专业的大学,唯一没有报考私立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因为学费太贵。最后,方汉奇考上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念了四年的公费大学。
虽然是穷学生,方汉奇为爱好花钱却很大方。他想方设法收集各类旧报,常去旧书店“淘宝”。当时的旧书店,大多看重旧书,而不看重旧报,要搜集旧报,就得到店里的废纸堆里翻找。1947年8月,方汉奇与学长穆家珩一起逛旧书店,找到了一堆20世纪20年代的《时事新报》和《申报》。那天他们用一个烧饼的钱换来了好几种旧报,收获颇丰,倍感高兴。大学期间,方汉奇逛了三年旧书店,藏报增加到1500多种,还有不少可称为“海内孤本”的珍品。
基于如此丰富的收藏,方汉奇于1948年撰写了13600多字的论文《中国早期的小报》,在《前线日报》副刊上连载了8期。这是方汉奇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自此他走上了新闻史研究之路。
集报种类不断增加,方汉奇自有办法把它们整理得井井有条。他仿照杜威十进分类法,将报纸分类编目,一共有10大类、118小类,对于有历史价值或特殊意义的报纸,还会附上详细的说明。1948年12月,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为庆祝建校7周年,举办了一次全国报纸展览,三年级的方汉奇作为班上的学术委员,是报展的主要筹备者和展报提供者,报展采用的分类方法也来自于他。筹备三月、为期两天的报展,一共展出了1650种报纸,占用了10间教室、400张课桌,参观人数超过6000人,《申报》《报学杂志》等都对这次报展进行了报道。
方汉奇对新闻史的爱好与积累,给当时的系主任马荫良留下了深刻印象。1950年1月临毕业时,方汉奇收到了时任上海新闻图书馆馆长马荫良的一封信,这封信给他带来了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上海新闻图书馆研究馆员。
调查藏报,摸清新闻史研究家底
《上海各图书馆藏报调查录》是一本几近散架的旧书,1951年1月由上海新闻图书馆(后并入上海图书馆)编印,并附新闻学图书目录,扉页对收录范围有更细致的解释:“藏报种数在二种以下,藏报数量在一年以内者,不列入。”这本调查录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上海全市至少收藏报纸2种及时间长达一年以上的31个各类型图书馆的藏报情况,史料价值不言而喻。
70年的岁月流转,让书页变得泛黄而发脆,翻阅起来不得不小心翼翼,如同捧着一份久远而珍贵的记忆。这样一本要付出极大努力才能编纂而成的工具书,正是方汉奇的作品,那时他25岁,刚刚大学毕业。
1950年3月,方汉奇正式到上海新闻图书馆工作。这是一家报纸专业图书馆,由解放日报社、新闻日报社和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共同创办,为安置上海解放后因《申报》《新闻报》停办而退下来的老记者、老编辑。时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恽逸群为理事长,聘任原《申报》总经理马荫良为馆长,《申报》主笔冯都良为副馆长,原《新闻报》副总编辑严独鹤为主任。当时上海新闻图书馆共有23人,方汉奇是里面唯一的年轻人。
《申报》《新闻报》是上海的大报,上海新闻图书馆基于它们的资料室建立,藏有600多种报纸。方汉奇的工作主要是整理旧报资料,吃住都在馆里。老报人们大都有20多年新闻工作经验,有不少旧闻趣事可聊。方汉奇白天听老报人们讲故事,等到下午5点他们下班后,就读书看报,3年看完了已出版78年的全部27000多份《申报》,连专门研究《申报》的学者都少有做到。

2021年,方汉奇先生95岁寿辰 作者/供图
当时的上海,包括上海新闻图书馆在内,共有57家公私图书馆,星罗棋布,各具特色。方汉奇想到,把上海各图书馆的藏报情况调查清楚,正是一个以“新闻”为名的专业图书馆分内的事。于是,他向馆里提出建议,得到了马荫良和严独鹤的大力支持。
作为唯一的年轻人,到各图书馆实地调查的任务,方汉奇自是当仁不让。1950年5月开始,他每日往返于上海新闻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之间,把上海所有图书馆跑了个遍。徐家汇藏书楼给方汉奇留下了深刻印象,“那里收藏的报纸特别多”。始建于1847年的徐家汇藏书楼,是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创办的第一家图书馆,方汉奇去的时候,藏书楼里的法国神父尚未离开。
在馆里提供的500元经费支持下,方汉奇“单兵作战”8个月,不仅调查了各图书馆的藏报情况,还摸清了新闻学藏书情况,编出一本目录。严独鹤为之题写书名时,还颇感遗憾,因为刚刚毕业经验不足的方汉奇忘了写前言后语,没有为读者交代成书背景。方汉奇编辑的调查录,不仅是一份历史记录,还是一个年轻人执着努力的心血见证。
2020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为新学年举行开学典礼,满头银发的方汉奇为8000多名新生带来一堂“公开课”。他叮嘱大家,“最好的年华要去做最应该做的事”,希望大家“多读书、多坐冷板凳、多泡图书馆”。70年前,方汉奇就在他“最好的年华”里做了“最应该做的事”。
“找米下锅”,绘制新闻史知识图谱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20世纪后半叶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基本格局由此奠定。在院系调整中,中国新闻教育格局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南方的新闻教育资源都汇聚到复旦大学;在北方,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交由北京大学接办,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下的一个专业,由此形成了中国新闻教育“一南一北”的基本格局,一直持续到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成立。
1953年8月23日,方汉奇带着他的全部家当四大件行李来到北京大学,成为中文系新闻专业的一名助教。虽然只是助教,也有正式的聘书,由马寅初校长亲笔签发。从此,方汉奇结束了3年的上海新闻图书馆研究馆员生涯,正式成为一名教师,专门从事新闻学的教学研究工作。
实际上,方汉奇的从教生涯开始得更早。1951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报学系主任黄嘉德要找一位兼职讲授新闻史的教师,马荫良便推荐了方汉奇。那时方汉奇比学生大不了几岁,讲课效果却很不错,“一上讲台,四座静听”,黄嘉德当即约请方汉奇常去兼课。于是,方汉奇开始每周去上海圣约翰大学报学系讲两个小时的新闻史专题。当时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中文系的范敬宜还旁听过方汉奇的课,印象深刻,多年不忘。
方汉奇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授课,以及他在新闻史研究方面的兴趣与积累,都被他的邻居、时任《解放日报》编委和秘书室主任罗列看在眼里。有丰富新闻教育经验的罗列与方汉奇十分投契。1953年3月,罗列调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负责新设立的新闻专业。赴任之前,他邀请方汉奇到北京大学任教。因为“对教师这个职业感兴趣”,方汉奇欣然同意。罗列后来对这次“挖角”还颇有些自得,“说方汉奇是我请来的,要不是我请来,他也不会搞新闻史”。
慧眼识英的确了不起,当时在大学里教新闻史并非易事。为了建立新中国的新闻教育体系,包括课程内容在内的各方面都要进行巨大的调整和变革,但是缺少资料令当时负责中国新闻事业史教学任务的方汉奇颇感棘手。已有的新闻史研究作品,仅有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等少数几本有参考价值。但戈氏著作下限仅到1927年,其中还有不少错误。更困难的是革命报刊史部分,除了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提及的寥寥数语,再无其他现成资料。
当时在大学里讲授这门课程的,除了复旦大学的曹亨闻老先生,就只有方汉奇一人,新闻史教学与研究完全是一块待开垦的园地。方汉奇到北京大学时,离开学上课仅剩一星期,他只得一边讲课一边搜集资料备课。一开始,教学效果不够理想,收到了很多意见,方汉奇很为此感到苦恼。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方汉奇开始“找米下锅”。除了上课和教研室的例会,其他时间他都用来看书备课。寒暑假时到京沪各地图书馆、档案馆查阅和搜集报刊资料、走访老报人。得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原件,馆长向达亲自保管,不能外借,方汉奇就在向达的办公室里翻阅报纸完成备课。从1953年到1958年,方汉奇看完了2000多本书。由于长期伏案工作,他的上衣两肘总是最先磨破,为此准备了多副套袖备用。
1958年,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方汉奇随迁人大,但潜心备课积累如旧。新闻史的史料,过去不被重视,尤其是古代史部分,零散少见,而且往往深藏于各种历史文献的边边角角、隐秘之处。方汉奇以青春为代价,埋首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精心寻觅星星点点的一手史料,为新闻史教学研究一点一滴筑牢根基。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积累终有回报。自1953年起,方汉奇以研促教,陆续发表20余篇论文。至1965年,已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方汉奇编印出一本《中国近代报刊史简史讲义》,积年苦功,心血之作,初步绘制出新闻史的知识图谱。
忆来时青春年少,此时也将步入中年。一手史料的充分占有,使得方汉奇的课以旁征博引、资料丰富著称。当年听过他讲课的成美教授回忆道:“方汉奇老师讲中国报刊史,常有许多生动有趣的材料,被称为‘海内孤本’。有一次,他引用古代文献,并介绍《京报》的出版情况,绘声绘色,听得大家屏息无声,忘记了下课。”
数万卡片,垒起一座新闻史高峰
1978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方汉奇第二次从北大来到人大,从此一直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这时方汉奇已52岁,此前十年他做过不少事,下放江西“五七”干校时还在采石场打过石子、在食堂做过伙夫,但就是没能再进行新闻史教学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春回大地,中国新闻教育也重新起步恢复发展。已临近中国人民大学建校30周年,重新焕发学术青春的方汉奇找到系主任罗列,提出想要写一本《中国近代报刊史》,为建校30年献礼。

《中国近代报刊史》 方汉奇/著
写书的材料基础,来自方汉奇长期积累的几万张卡片。方汉奇上大学时从曹聚仁先生的新闻采访课上学来了做卡片积累资料的方法,从此一直坚持下来。在上海的3年,方汉奇翻阅了上千种报纸,摘录了两万多张卡片。即使在动荡年代,家当都丢了,卡片也舍不得丢。有长期积累的卡片做基础,方汉奇重新投入到紧张的教学、研究和著述时,笔下马上结出了累累硕果。
从1978年夏天开始动笔,方汉奇足足写了两年,而为此他已积累近30年,甚至为写这本书就专门做了2.5万张卡片。当时条件艰苦,家中连一张写字的书桌都没有,方汉奇就趴在书箱上写完了书——这五个宝贝大书箱,在下放江西时他也一直带在身边。由于教学工作忙碌,写书只能见缝插针利用课余时间。方汉奇一开始只打算写8万字,但写起来便一发不可收拾,最后写成了一部57万字的专著,涉及报刊超过1160种,介绍报人1500余位,纠正前人著述错误200余处。“乍暖还寒”时候,这种写法无疑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因为自1949年以来,新闻史研究几乎不谈人物,而《中国近代报刊史》光是重点展开的报人就不下百位。
1981年元旦,方汉奇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报刊史教研室为《中国近代报刊史》写下后记。中国人民大学30周年校庆已经过去,但这部凝聚了方汉奇30年心血的专著,意义远远超过一本献礼的小册子。该书一经出版就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被公认为自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之后“50年来第一部有影响的新闻史专著”,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另一座高峰”。书中大量丰富的一手史料,以及所确立的新闻史研究基本方法,对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潜心著述,夯实新闻史学科基础
20世纪80年代初,新闻教育开始恢复发展,但“新闻无学”的看法仍然十分普遍。从业界到学界,“新闻有学无学”的激烈论争遍布全国各新闻院校、新闻单位,成为热门话题。对于新闻学者而言,摘掉“无学”的帽子,成为新闻学学科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1985年,方汉奇发表文章《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引起较大影响。他强调,“新闻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属于文化史的范畴”。同时,他基于丰富的材料指出,中国新闻学研究始于新闻史研究,新闻史是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新闻学学科建设起到基石作用。
“新闻学是学”,有如“白米饭是饭”,之所以要为此撰写专文,正是因为当时泛滥的“新闻无学”错误观点,不利于新时期新闻学的健康发展。
为了筑牢学科基础,自1986年起,方汉奇和宁树藩、陈业劭等老一辈新闻史专家组织全国20多家新闻学术单位的50位学者,编写出一套260多万字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本,13年呕心沥血,终于在1999年出齐。这套通史“篇幅之巨大、内容之丰富、材料之厚实、建构之完整,都是同类著作中所未有的”,代表了当时“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最高水平”,2013年在新加坡出版了英文版十卷本,成为“新中国新闻学著作的第一个外文译本”。2000年,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三卷本出版,编纂历程跨越20年,记载的史料极为丰富、可靠,具有夯实中国新闻史学科基础的重要学术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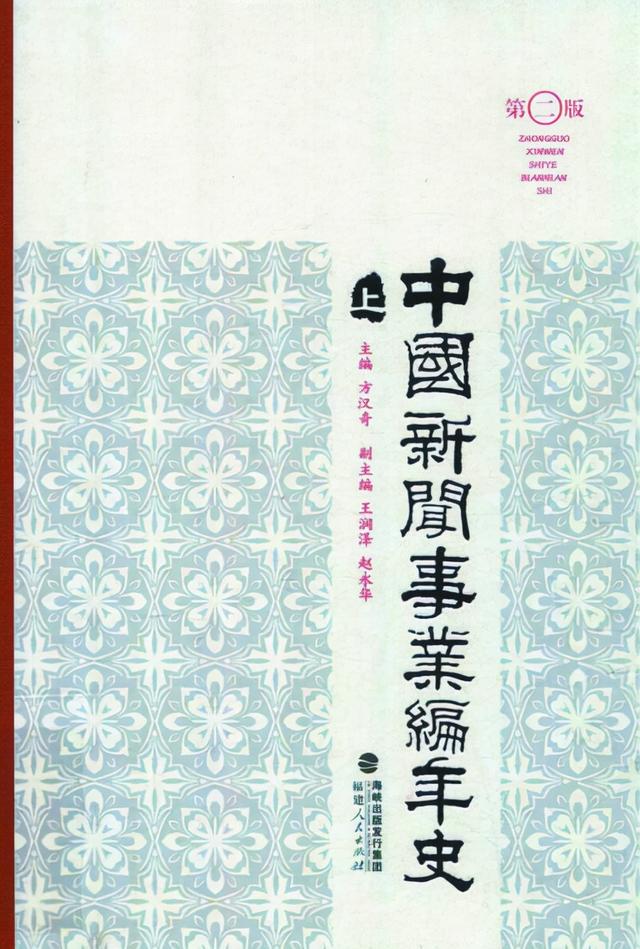
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
三千多种集报、十万余张卡片、专著、通史、编年史、教材……方汉奇一砖一瓦搭建起中国新闻史学科大厦,为中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作出巨大贡献。1981年,第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召集时,新闻学未被承认是一个学科,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被列为文学下的二级学科。时任学科评议组成员的方汉奇积极倡导将新闻学科从二级学科升为一级学科,并为之付出不懈努力。1997年,新闻传播学被评定为一级学科,有了自己单独的学科评议组,学科范围内的一切评议活动,终于可以自己作主。
2016年,在方汉奇新闻史学思想研讨会暨方汉奇从教65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杨保军教授的发言十分恳切,中国新闻学正是因为有了方先生这样的泰山北斗,这个学科才自信豪迈,才扬眉吐气,才在有学与无学的不断纠缠中成长并成为时代的显学。
桃李芬芳,守望新闻史未来发展
1978年,方汉奇开始招收硕士,1984年开始培养博士,迄今“方门”桃李已经满天下,成为中国新闻教育发展的中流砥柱。方汉奇不仅是新闻教育园地里辛勤耕耘的“园丁”,更是“园丁们”的“园丁”,为中国新闻教育事业培养人才尽心竭力。
1984年1月,新闻学专业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列为博士学位授予专业,方汉奇与王中、甘惜分三位教授成为我国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导师。那时的新闻学博士培养,生源并不多,同学们大多数更加向往业界。发现有天赋有能力从事学术研究的学生时,方汉奇总是尽最大努力鼓励他们在学术之路上继续前进。尹韵公是方汉奇培养的第一届新闻史博士,他回忆当时方汉奇先生三次去他的宿舍劝说他报考博士,“当时我住在5楼,方老师已是年过半百,可还是一趟趟亲自到我住的地方来动员我继续深造”。
从1985年招收第一届博士开始,迄今方汉奇已指导了50余名博士生,现在还在指导“关门弟子”完成博士论文。方汉奇培养学生,强调博览群书、有的放矢,且鼓励学生发挥特长,循着自己的研究志趣不断开拓,并强调在前人基础上要有所创新。清华大学陈昌凤教授还记得,方先生指导学生的论文选题时,会细细梳理一遍前人已经做过的研究,“路边的桃子已经被前人摘了,需要你再去发现、另辟蹊径了”。
“方门弟子”的研究领域不仅在时段上从古至今,覆盖唐、明、清、民国、当代等多个时期,还有对《蜜蜂华报》《述报》《上海犹太纪事报》等重要报刊及成舍我、胡政之等重要报人的深入考察。在方汉奇的指导下,“方门弟子”各有所长,毕业以后厚积薄发,在各自领域纵深开拓,不仅成为新闻史研究的中坚力量,更从多个层面拓展了新闻史研究的领域、方法与进路。从中国到外国、从报刊到新媒体、从业务到体制……作为第二代新闻史研究者,“方门弟子”在方先生等第一代新闻史学者的基础上,为新闻史研究铺设出更为广阔与精细的学科地图。
方汉奇曾说:“当教师的要有‘蜡烛’精神。燃烧自己,点亮别人。对学生必须全心全意,尽心尽力。从做人到做学问,都全力地帮助他们,关注他们,关爱他们。学生尊敬老师,老师关爱学生,我和我的学生们的关系始终是很融洽的。”每年教师节,到方汉奇家中拜访的学生络绎不绝。而不管此前在何处,每年的9月,方汉奇也一定会回到中国人民大学,在新闻学院的开学典礼上,为新生送上他的勉励与期许。
方汉奇所关注的,远不只自己的学生们,“所有的求助在方先生那里都会有下文,提携后人是方先生的一种习惯”。很多后辈学者都收到过方先生的尽心指点与鼓励,大量新闻院系在建设发展中得到方先生无私、公正与细致的建议。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李磊曾说,“为了国内新闻院系的建设,方先生不辞辛苦,可以说是走遍了祖国的千山万水”。
年逾90的方汉奇自称新闻史研究的“退役老兵”,凝聚半生心血的十万余张卡片也早已捐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但他还是在一直守望着新闻事业的发展、新闻传播活动的发展、新闻教育的发展。2017年9月,方汉奇荣获有中国人文社科领域最高奖项之称的“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奖金100万元。“这辈子得过一些奖,没得过这么大数额的奖金”,方汉奇一生勤俭节约,最大的花销是买书。得知获奖,他马上将奖金悉数捐出,用以支持全国新闻史研究、推动新闻传播学科发展。
在“中国新闻史”课程与教材建设研讨会的发言中,方汉奇再次勉励大家一起努力,促进新闻史学研究和教材编写工作进一步发展。“长江后浪逐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这是一位新闻史学家的殷切期盼与恒久守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新中国70年新闻传播史1949—2019”(19ZDA32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邓绍根 游丹怡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