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创作中应注意的的文字问题
在当下书法创作中,作品中的文字问题已引起普遍关注,特别是在展览参评的作品中,文字问题尤为严重。针对当下书法作品中的文字问题,中国书协极其重视。在十二届全国书法篆刻展评审中,特别增设了文字审读环节,以确保在入展作品中减少错别字的出现。笔者作为十二届国展学术观察员和文字审读组监审委员,参与十二届国展评审工作,对作品中出现的繁简字、俗讹字、废弃字、分化字、相似字、错别字、避讳字、偏旁混用字等等问题,谨作大概梳理分析。
中国的文字史和文明史一样源远流长,文字问题不仅在当代,在古代碑帖、墓志、典籍以及日常书写中,也存在着大量的不规范字、讹形字、俗字等,特别是民间墓志,不规范用字现象大量存在。对于书法创作者,深入研究古代文字及其流变,正确理解和取用异体字、俗字、甄别错别字等尤为重要。
本文就十二届全国书法篆刻展览参评作品的文字问题大致分为以下几类:一、繁简混用;二、相似字不分;三、俗讹字;四、错别字;五、偏旁移位;六、古代错字;七、增繁与简省。
一、繁简混用
繁体字和简体字的概念,很容易让人想到文字改革,特别是1954年以来的文字改革。其实,自文字诞生以来,繁简字就存在了。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一书中谈到:“其实中国文字既以形体为主,讹变是免不了的,由商周古文字到小篆,由小篆到隶书,由隶书到正书,新文字总是旧文字的简俗字。明以后到刻书,俗字渐少,但在词曲小说里还保存着,下层社会还曾流行着,一直到现在。”①文字的演变轨迹,始终是朝着简便实用的方向发展,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简体字,其实在古代一直是存在的,有的字还作为正字,在《干禄字书》均有体现,比如:囬——回(左俗右正)、亰——京(左通右正)、禮——礼(左右并正)、萬——万(左右并正)、乱——亂(左俗右正)等,上述字并不属于繁简混用。
像刘、张、赵、观、亲、马、孙、议论、过、这、远、迈、迁、还、虽、阴、难、离乱、双、体、穷、尽、湿、浊、权、郑、咏等等简体字,也是古已有之,并常见于明清小说,像《金瓶梅》、《列女传》、《古今杂剧》均有大量简体字出现,在《宋元以来俗字谱》里均有记载。但这些字,只是在古代民间广泛使用,很难进入官方文字系统。但因为它书写的便利性,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1964年公布的简化字总表共简化了2238个汉字。将一大批俗体简化字定位为正体,又通过减省笔画、简化偏旁、草书楷化、同音替代、改换字例、简存轮廓等进一步简化。虽说简化了,但只要字义不错,很多字还是可以在作品中运用。所以,文字改革后,这些简化字身份转正,成为我们今天的正字。我们在学习艺术的同时,也要学习规范用字。有些作者在作品中把古代的繁体字和简体字混用,或者是把当下的简化字和古代的繁化字混用,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繁简混用。比如有的作品中出现的云—雲,云为古文字,雲乃后起字,战国以后二字便分开使用;后—後,后、後本为二字,“后”的本字是毓,甲金文“后”字是“司”的异写;虽然历史上某些典籍把皇后写为皇後,不足以为凭证,皇后写为皇後是错误的;范—範,《汉庐江太守范式碑》范写为“範”,范宽写为範宽,是错误的;余——餘,作我时余写为“餘”;制——製,安禅制毒龙这首诗,作者多把制写为“製”;里——裡,墟里上孤烟,里多写为“裡”;松——鬆、斗——鬥、系——繫、征——徵,长征误为长徵;万俟—萬,万俟误为萬俟等这类字,在古代有的是后起字,有的本来就是两个字,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文字简化后,归于一个字,在书写中,我们就要甄别使用,如果不分文意,繁简混用,在某些语境下,就是错字。
二、相似字不分
相似字不分在参评作品中也多出现,有些虽说字形相似,但本义相去甚远。就参评作品中出现的误写作以举例:锺——鐘,锺繇误为鐘繇,酒锺误为酒鐘。
清邵英《说文解字群经正字》:“按,据《说文》,锺是酒器,鐘为乐器,今经典多通用锺为乐器,其误亦始自汉碑,韩勑碑云:‘锺磬瑟鼓。’校官碑云:‘锺磬具矣。…’”
但鐘磬写为锺磬,古通,鐘字产生于西周中晚期,皆用为乐器,锺产生于春秋时期,同样乐器之名,鐘锺不别,战国以后区别使用;傅——傳,傳播写为傅播;系、係、繫不分,三字在古代用法不同,“系”主要用作嫡系、派系、世系、体系等,“係”主要只用于关系、干系、确系等;“繫”主要用于拘系、羁系、维系等,擊——繋,繋马误为擊马;曆——歷不分,日曆误为日歷,庆历四年春,庆“曆”作为年号,除非避讳,一般不写为“歷”,歷,甲骨文,从止,秝声;暦由歷分化,多用作历象,日月星辰运转之象;岐——歧,歧路误为岐路;褒——褏不分,褒斜道误为褏斜道;汨——汩不分,汨罗江误为汩罗江;發——髪不分,頭髮误为頭發;游——遊,遊学误为游学;鬥——門不分,鬥写作門,門写作鬥;翼——冀不分,冀州误为翼州;岡——罔不分,罔然误为岡然;菅——管不分,虽说汉隶竹艸不分,但管理不能写为菅理,草菅人命亦不能作草管人命;修——脩,脩脯误为修脯;奕——弈不分,弈棋误为奕棋;戊——戉——戌——戍不分,戊(干名)、戉(大斧)、戌(支名)、戍(戍守),作品中常见戍边写为戌边等。还有昜——易不分,侯—候不分,末—未不分,巖——嚴不分,才——纔不分,埸——場不分,仿佛别作彷彿、髣髴,不能写为仿彿、彷髴等。
这些问题在参评作品中普遍出现,相似字易写错,字相近而意义不同,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有些相近字字义较近,不容易分辨使用,还可谅解,但有些字属于基本常识,错的很离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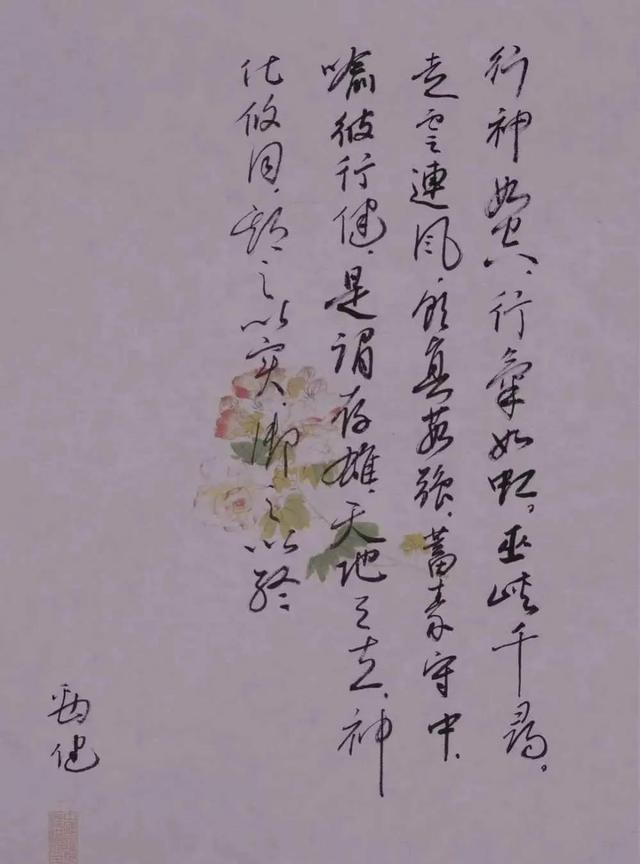
三、错别字
错字就是错字。别字,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别字”条云:“别字者,本当为此字而误为彼字也。”②是把形音义相同或相近的字拿来使用。
本届国展参评作品中错别字很多。比如,一—壹不分,一不能写为壹,“壹”战国后起文字,形声字,从壶,吉声。战国秦汉文字作 “壹”中“吉”声,隶楷文字由小篆演变而来,已失去壶形,写作“壹”,本意为专一。又由专一引申为统一、划一、一致,作副词,表示一概、一律、一样、统一,有一旦、假若、实在、的确的意义。作数量词“一”的大写为“壹”,一般用于财务数字大写。一古文字就写作一,是原始计数符号,春秋战国以后,一又可写作“弌”,如同二写作“弍”,三写作“弎”,是一种繁写法,这种繁写法均被后世废弃。比如很简单的落款用字,己亥年,己—已—巳不分,己亥写为已亥、巳亥,让人看不懂。落款传统用天干地支纪念,2019年是己亥年,已不在十干和十二支之列,巳亥二字同为十二支,是不能相配的。基本的落款,就有很多人写错,况又在显要位置,这种问题在本届国展参评作品中屡见不鲜。
还有更离谱的基本常识错误,比如历史上的人名:王羲之写为王義之,锺繇写为鐘繇,刘德昇写为刘得昇,陆游写为陆遊,庾子山写为庚子山,解缙写为谢缙,卫觊写为卫凯,汉章帝写为汉张帝,王杰写为王桀,名字要尊重作者的用字,单于写为单於,单于作为复姓,不能写为单於;更有甚者,把欧阳修的“欧”写为“殴”,看来欧阳修要挨他的板子了!对这类错字,是可忍,孰不可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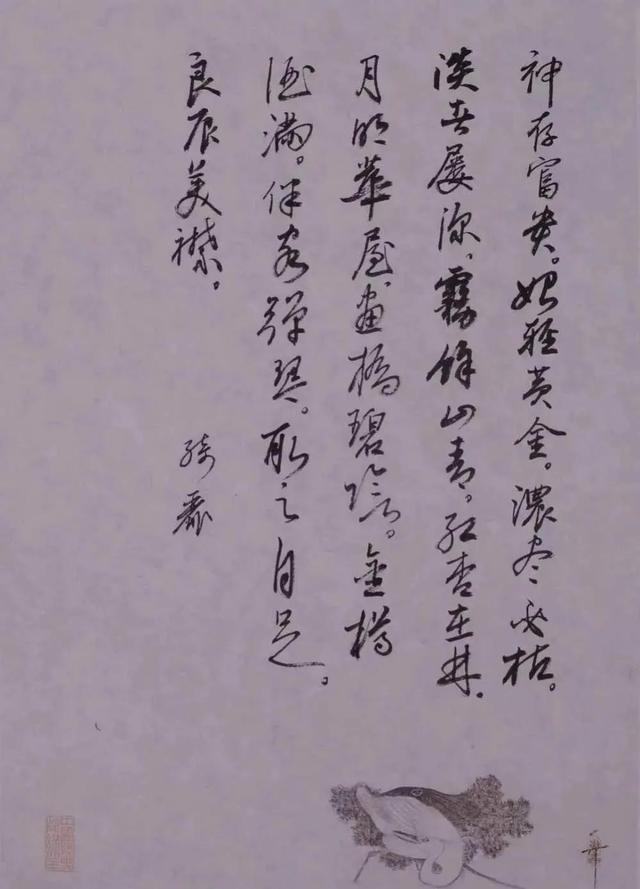
四、俗讹字
有些作者刻意选用俗讹字,生僻字,让人难以读懂、理解。对正字的坚守与推广,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一直是持之以恒的,最典型体现在科举制度对文字的要求,身言书判,书为首要。规范字始终是主流,放着规范文字不用,而故意追求冷僻字,让人难以解读,也不太可取。我国台湾俗字把嵗写为“才”,把国写为“口”,把兿写为“芸”,把轉写为“転”,把你写为“妳”等。
新加坡俗字:進写为“込”,中国写为“进”;階作“阰”,中国写为“阶”;窗作“囱”,中国写为“窓”;劃作“㓰”,中国写为“划”。
日本俗字:廰作“庁”,中国作“厅”,这两个字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字。姊作“姉”,有人认为“姉”是日本人创造的国字,其实“姉”即“姊”的隶变俗字,在居延汉简、武威汉简中已见其例。《龙龛手镜·女部》:“姉”,佛写为“仏”。“仏”字,敦煌经卷中数以万计。《正字通》:“仏”为古文“佛”。另外,处作“処”、两作“両”、齐作“斉”、龍作“竜”、縣作“県”、圆作“円”、廣作“広”、實作“実”、圖作“図”、摄作“摂”、澤作“沢”、傳作“伝”、賣作“売”、邉作“辺”等这类俗字已成为现代日语的正式用字。
五、偏旁移位
这类字在作品中常见,作者可能是为了字形美观,书写方便而随意变化结构,也可能是受古代民间文字的影响。古代汉字字形结构变换往往比较随意。
清严可均《说文校议》云:“六书大例,偏旁移动,只是一字;左右上下,随意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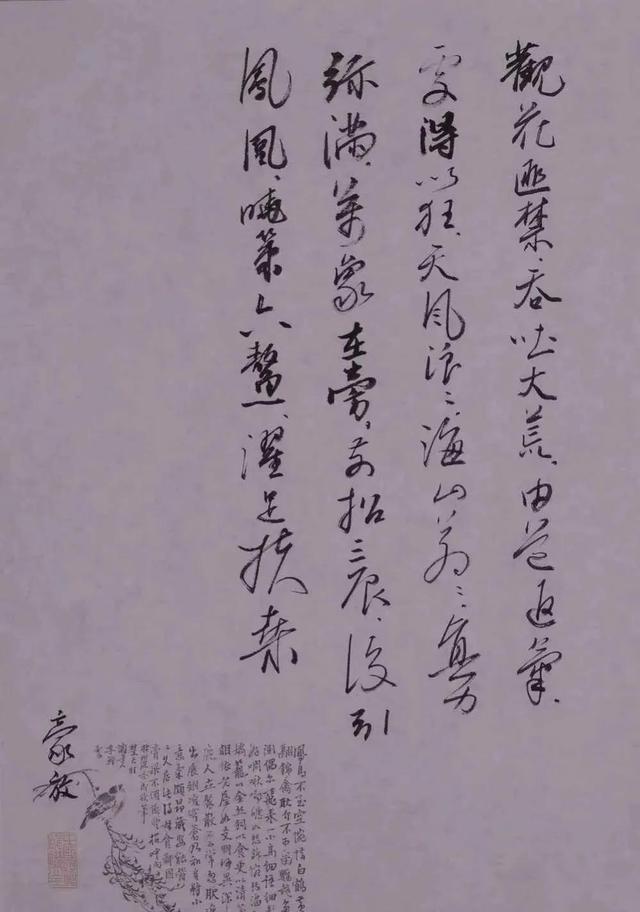
古人虽说字可变动,但也是在字义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可能是为了书写便捷而作出的合理改变。汉字经过篆隶草楷的演变,字形已趋稳定,随意更改,意味着是另一个字了。
比如,翊、翋、翌(左飞貌、古同翌,中飞翔,右明日),日在木上为“杲”,日落木下为“杳”;两朿上下为“棗”,左右为“棘”;口天为“吴”,天口为“吞”;木下口为“杏”,木上口为“呆”;日下九为“旯”,日上九为“旮”等,说明了汉字的部首不是可以任意挪位的。顾炎武曾说:“字可上下左右写者,惟鹅为然。”但张涌泉先生在他的《汉语俗字研究》一书中对“松”字进行了考证,认为“松”字有四种写法,松、枩、枀、(缺例字,编者注)。可上、下、左、右挪移,看来惟鹅为然,得作些修正了。有些作者为了追求字形的美观,不加思考,不求甚解,肆意改变字的左右结构、上下结构,所以错误也是在所难免的。
六、古代错字
中国文字在演变过程中,错、俗、讹变在所难免,历史上虽有《字样》、《匡谬正俗》、《干禄字书》等规范文字的官方字书,但受印刷、教育传播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官方的字书发挥的作用有限。所以,民间孳乳出大量不规范的文字,最明显的特点是笔画的随意简化,形体结构极为混乱,但也就是这些不规范的文字,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文字的发展。错别字在古代的碑刻、墓志、经卷、手札中大量存在,有些字因为书写者身份而影响更加深远,以讹传讹现象普遍。官方文本亦有,民间更甚,特别是民间墓志,多为乡间匠人急就书刻,目的不在于书写之精美,文辞之华丽,而是应急于丧葬之礼制,文字错漏俗讹难以避免。我们今天学习古代碑帖,一定要甄别使用,不能因为古代碑帖出现过这个字,就一定是正确的,就作为法理依据。就像我们今天作品中出现的错别字,难道百年以后就是对的了吗?后人甄别我们的字就像我们甄别古人一样,不要盲目的讲这个字古人碑帖出现过。比如《圣教序》里面的色字“(缺例字,编者注)”,明显是“包”字,《华山庙碑》“中宗”为“(缺例字,编者注)宗”,帝之庙号,不能以讹传讹。再比如,古代出现大量的避讳字,采用改字、空字、缺笔、改音等多种办法,其中避讳缺笔造成了一批不规范的汉字,不可学。在今天来看,也是不对的。如:

上述这些字,在当下书写肯定是错误的。盲目崇古、盲目继承,都是不可取的。用字还是要建立在一定的规范之内。
七、增繁与简省
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为了书写便捷,文字的简省便成了文字演变的趋向。清末学者沈学在《盛世元音》文学篇中云:“夫字,士人之利器,以愈利愈为妙。”
林辂存在《上都察院书》说:“盖字者,重要之器也,器惟求于适用。”
例如:嫂简化为“㛐”、惡简化为“悪”,亦作“恶”、權简化为“权”、觀简化为“观”、勸简化为“劝”、歡简化为“欢”、棗简化为“枣”、纔简化为“才”、變简化为“变”、懐简化为“怀”、劉简化为“刘”、羅简化为“罗”、蠺简化为“蚕”等。在简省的同时,为了使形音义更加明确,有的字又不断繁化。参评作品中,任意简省与增繁的字比比皆是。比如“逸”字少点,逸,从辵,从兔,善于奔跑之意。少了点就变成从免了,写作免,字义全无,字也就错了。茅字少写一撇成“芧”;系字少撇为“糸”,糸是细丝,世系误为世糸;耹少写一点为“聆”,地名成为聆听了;佛字简省为“仏”,“仏”字在敦煌写经中常见,古代同佛,现在少用;孃字写作“娘”,《玉篇·女部》孃为母称,娘为少女之号,本是不同的二字,唐人对此二字分用明确。有些字简省就没关系,比如草书楷化是简俗字滋生的主要来源。
还有些作者为简省笔画,上下字强行合文,各拆半边硬拉鸳鸯配,不伦不类。合文字古已有之,民国为推行文字简化,一些人曾有意识创造一些合文,当时称之为复音字、代词字、合体简字、会意新字、复音合体字、缩写字等。即使有官方的推崇,但依然不能通行。比如很典型的图书馆“圕”,依然被废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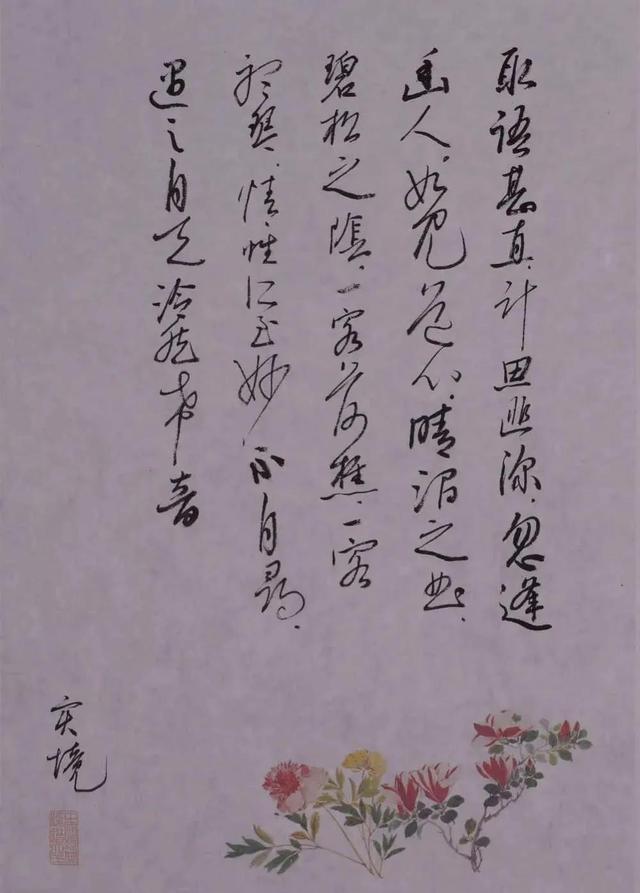
增繁字,书家创作对字的稠密度要求极高,笔画太少的字不太好写,字形也不美观,所以,繁体字书法创作总比写简体要美观得多,能加饰笔则加,以迎合人们的审美要求。随意简省易错,但增繁也容易写错。比如,或加两笔成“彧”,就是另外一个字;泉加三点水为“湶”,湶作水名,虽然古代相通,但后世作水名专用字;秋写为“龝”,地写为“埊”,人加三撇“(缺例字,编者注)”等。有些字还好,作为俗字书写,有些字是作者自己任意添加部首、任意增加笔画,让人无法理解,属于自造字。
参评作品中的文字问题不胜枚举。比如,拼凑字,这类字大部分和写大篆有关系,大篆文字较少,《说文》收大篆也就二百多字。清代民国的书家写大篆往往也是以对联为主,就十几个字,有些字没有,古人也拼凑,是用部首拼凑或假借,但前提是作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字素养。现在的大篆作品中尽是随意拼凑,拿小篆填补等,有人用大篆洋洋洒洒写个八尺整张字数过千的作品,应该是很自信自己的造字能力。通过文字审读,发现的这些问题,是值得当代书家沉思的。书法创作以文字为基础,不理解本义,一味的强调形式美、艺术性,也是没有根基的。
十二届国展评审,增加文字审读环节,可以减少问题文字。但在日常书写中,文字问题依然普遍,从影视、报刊、书籍等到题匾、题字、广告标语等,错别字充斥着街道巷尾。书法家不是写字匠,历来作为文人的形象出现,文字基础也代表着一个人的基本文化修养,但往往一个错字,便足以让人斯文扫地。
正如《字辩·补遗》字辩序所言:“六书音韵,既诉诸高阁而问津无人。讹字方言,复错杂连篇而触目皆是。”错谬问题层出不穷,作为书法家,正确使用汉字,才能更准确反映传统文化的经典内涵,使之达其情性,形其哀乐。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书法艺术的提高和发展将成为空谈,文字问题必将成为制约书法艺术发展的瓶颈。
(本文来自网络)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