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人性本恶,必须加以限制

我认为:人性本恶,必须加以限制,制止恶的一面。虽然这样说可能令人沮丧,但我仍然这样认为。
我们已经征服了太空,但我们还没有学会如何征服自身的原始本能和情绪,这些本能和情绪对于我们在石器时代的生存是有必要的,但在太空时代却没有必要。
虽然儒家思想认为人性可以改良,但我一向认为人类就像动物一样,我不确定能否改良,但我认为可以进行训练,可以进行管教……你可以让一个习惯使用左手的人用右手写字,但你无法真正地改变其与生俱来的本能。
人们认为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或者说应该是平等的……但这种想法现实吗?如果不现实,那么追求平等就会导致倒退。
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没有任何两个事物是完全平等的,没有同样小的事物,也没有同样大的事物。事物从来都不是平等的。即便对于非常相似的双胞胎而言,出生时也有先后之分,先来者优先于后到者。人类是这样,部落是这样,国家也是如此。
人类不是平等的,他们处于极其激烈的竞争中。苏联已经失败了,因为他们试图把利益均等化,这样一来,没有人会努力工作,但每个人都不想比别人得到的少。
我一开始也认为人是平等的……现在我知道这是最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因为人类已经进化了数百万年,分散到了世界各地,彼此相互隔绝,独立谋求发展,种族、民族、气候、土壤条件都不尽相同……这是我在书本上读到的东西,我自己的观察也印证了这一切。
对任何一个社会而言,在1000个新生儿中肯定有相当比例的婴儿接近于天才,有相当比例的婴儿是普通人,也有相当比例的婴儿有点儿愚笨……正是那些接近天才的人和在普通水平之上的人最终决定了未来的事情……
我们想要一个公平的社会,我们想给每一个人提供均等的机会,但在我们的思想深处,我们从来不会自欺欺人地认为存在两个在毅力、动力、敬业程度、内在禀赋等方面一模一样的人。
在这个问题上,弗雷德里希·哈耶克在其著作《致命的自负》中表达的观点非常明确,而且具有权威性,与我长期以来的想法不谋而合,但他的书没有说明一些伟大的知识分子的不明智之处,其中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些伟人往往认为人类大脑可以设计出一种更好的制度,这种制度比“历史演进”或“经济达尔文主义”在过去几个世纪带来的“社会正义”还要多。
任何一个政权、任何一个宗教、任何一种思想都无法征服世界,或者按照自己的设想重塑世界。世界的多样化特征太明显了,不同的种族、文化、宗教、语言及历史要求各国通过不同的道路实现民主和自由市场。在全球化的世界,各个社会因卫星、电视、互联网及便捷的旅行条件相联,因此各个社会就会相互影响。
在某个发展阶段,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能最好地满足一个民族的需求,是由社会达尔文主义决定的。
我会把自己描述为一个自由主义者
也许按照欧洲的标准,我是一个介于社会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的人。
我会把自己描述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一方面,我倡导机会均等,努力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最好的发展;另一方面,我还有一定的悲悯之心,希望失败的人不会在困境中越陷越深……我想让制度以最高的效率运作,但同时考虑到那些现状不佳的人,因为他们的自然条件没有提供给他们足够多的资源,或者他们本身缺乏努力奋斗的条件……
我是名副其实的自由主义者,因为我不会拘泥于某一种关于治理世界、治理社会的理论。我是务实的,我愿意直面问题,说:好吧,什么才是最佳解决之道?怎样才能为最多的人创造最大的幸福和福利?
我成长于三世同堂的家庭,这就不知不觉地使我推崇儒家思想,这种思想会潜移默化地渗透进你的大脑。儒家思想认为如果人人都争做“君子”,那么社会就能实现良性运转。理想中的君子与绅士有些类似……这意味着不要做邪恶的事,努力做善事,孝顺父母,忠于妻子,好好抚养孩子,善待朋友,这样他就是忠于皇帝的好公民……
儒家内在的哲学观念认为如果想要一个社会实现良性运作,你就必须考虑到大部分人的利益,社会利益必须优先于个人利益。这是与美国文化的主要差别所在,因为美国文化是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

在外出旅行和访问期间,我会注意观察一个社会、一个政府是如何运作的,会思考为什么它们运作得好……人的思想不只来自阅读,你可以从书本中获取,但如果你不把书本知识同自己的情况结合起来,书本知识就无用武之地。我自己经常会把读到的东西同自身情况结合起来……
同博学多才的人展开讨论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点一定不要忽略,我认为这比单纯孜孜不倦地阅读文献强得多。因为通过短暂的交流,你就能萃取对方的知识和对方的思想精华。
新加坡的模式是无法轻易复制的,我认为这是我作出的最大贡献,也是最有价值的事情。
性格、经历和思想
我的思想源自于我的性格……还有我的一些生活经历。当你的整个世界轰然坍塌时,你就会遇到一系列不可预见的、出乎意料的情况。我的人生就是这样。
如果日本军队没有在1942年发动侵略,大英帝国在东南亚的统治或许会再持续1000年,但事实上在1942年就终结了。我从来没想过日本人会征服新加坡、把英国人赶出去,但他们确实做到了,还用残暴的方式对待我们,包括我本人也遭受过日本人的虐待……
在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之前,我就深刻地知道了什么是权力。日本人表明了这一点,英国人却没有。
当时大英帝国快要走到尽头,在技术、商业和知识领域都占有主导地位,已经没有必要使用残暴的武力了。他们只是在1868年动用印度的犯人劳工们在山上修建了这座巨大的政府办公楼,以此统治人民……我从英国人那里学到了如何治理国家、如何管理人民,也见识了日本人是如何运用权力的。
日本人对新加坡的侵略给我上了一堂最深刻的政治教育课,因为在长达三年半的时间里,我看到了权力的意义,看到了权力、政治和政府是密切相关的,而且我还明白了在强权政治下陷入困局的人们为了生存会采取哪些应对之策。先是英国人在这里,他们是固有的、完全意义上的主人,而之后日本人来了,我们一直奚落日本人是矮胖、短视和斜眼。
当我和在内阁中担任高级职务的同事们回首早年治理新加坡的忙碌岁月时,我们都意识到充满磨难的学生时代使我们受益良多。我们遇到了街头恶霸,如果我们没有体验过这种磨难,那么我们就会被打倒。如果我们从未感受过忧患,就像一条狗被圈养在篱笆后面的小屋里那样安全无忧,那么当我们身处危险重重的车流中就会被碾压而亡……
我们的孩子没有经历过那种残暴侵略下的艰难岁月,较年轻的一代部长们也没有过这些经历。激烈的斗争造就了老一辈的部长们,我们中间那些身体虚弱、行动缓慢或者容易紧张的人就成为早期的牺牲品。我们这些剩下的人就是在达尔文所谓的自然选择过程中幸存下来的人,我们都有强烈的生存本能。
自1973年以来,我学到了什么呢?我学到了一些关于人类与人类社会的更加基本的、永恒的道理,学到了如何让人类和人类社会实现更好的发展,学到了倒退和崩溃的风险是永远存在的……我意识到了一个文明社会是何等脆弱……我还明白了个人成就的重要意义。
在50多岁、将近60岁时,我意识到,同知识、道德和精神上的满足相比,尘世的一切荣耀与成功都是转瞬即逝的,一切感官上的愉悦和快乐都是短暂的……我不禁开始怀疑我所拥有的东西中有多少是先天决定的,又有多少是后天培养的。如果我没有经历过艰难抗争的考验,我会与现在的自己有所不同吗?
作出了一个个生死攸关的抉择,经历了一次次重大的危机,我的眼光、雄心和辨别轻重缓急的能力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相信这种变化将对我产生深远的影响。也许所谓的“硬件”(即我的身体、精神和情绪)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我的“软件”(也就是我对上帝、荣耀或金钱的看法)已经受到了人生阅历的深刻影响。
换句话说,无论“硬件”(由先天决定)多么好,没有“软件”(靠后天培养),“硬件”也不会有多大的用武之地。
严峻的考验是成绩,而不是承诺
逻辑与推理的真理性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最终检验。
严峻的考验是成绩,而不是承诺。数百万无依无靠的亚洲人不关心也不想知道什么理论,他们只想过好一点儿的日子,他们想要一个更加平等、公正的社会。
如果我们要创造良好的经济条件,就必须找到实际的办法,解决增长与发展问题,而不是寻找这种或那种理论。这也符合理智的要求。
我的人生不是依靠某种哲学或某些理论指导的。我把事情办好,让别人从我的成功之道中总结理论或原则,我不会搞理论。相反,我会问:怎样才能做好这项工作呢?如果我在查看一系列解决方案之后发现某个方案切实可行,那么我就会努力找出这个解决方案背后的原则。
因此,我未接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人的指导,我只对在现实中行得通的事情感兴趣……如果我面对一个困难、一个重大问题或者一系列相互冲突的事情,而初步解决方案行不通,那么我就会先看看是否存在备选方案。我会选择一个成功概率比较大的方案,但如果它以失败告终,我还有其他方案,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我们不是理论家,不会搞理论崇拜。我们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问题,人们要找工作、要挣钱、要买食物、要买衣服、要买房、要抚养孩子……我们可能读到过什么理论,也许半信半疑,但我们要保持现实、务实的头脑,不要被理论束缚和限制住。如果一个方案行得通,我们就实施,这样才有了新加坡今天的经济。
面对一个理论,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它可行吗?能给人民带来利益吗?当年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理论之一就是跨国公司压榨廉价劳动力、廉价原材料,会把一个国家压榨干净……我认为,既然廉价劳动力闲置,那么如果跨国公司想利用,为什么不行呢?我们可以从跨国公司那里学习先进经验,没有它们,我们可能永远都学不到这些……发展经济学派认为这是压榨,而我们的经历就有力地反驳了这种观点。我们只是脚踏实地,绝非故意给高深的理论原则挑刺。
我认为,一个理论不会因为听起来悦耳或者看起来符合逻辑就一定具有现实可行性。一个理论最终还是要放到生活中检验,也就是要看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什么,要看能给一个社会中的人民带来什么。
我认为美国的制度不一定是理想的或者适用的。我注意到英国人一直在试图模仿美国人……盲目效仿美国制度的人认为,只要美国官员开始披露秘密,那么这种行为就应该成为一种时尚,这种行为表明你的社会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如果有任何部长或法庭压制真相,你就有义务将其捅给反对派。
这种想法是否合理呢?这还是新事物,还没有得到实践证明。如果你损害了社会基础,就会给下一代或者更下一代人造成不良影响。如果有两种制度摆在你面前,一种是得到实践检验的,另一种是尚未被检验的,而我又是保守派,我肯定会选择前者,至于后者是否可行,为什么不留给其他人、让他们证明呢?
如果一种制度能推动科技事业大繁荣、能给人民带来幸福、能解决社会问题,如果因为害怕引起争议而放弃这种制度,那就是非常愚蠢的行为……最终的证据是它能给社会带来什么。

我崇拜的领导人
戴高乐、邓小平、温斯顿·丘吉尔。
崇拜戴高乐是因为他有巨大的魄力。他的国家被占领了,他是个一星的将军,而且他代表法国……当英国人、美国人收复北非时,他前往阿尔及利亚和阿尔及尔,他在那里看到一位四星的法国将军。于是戴高乐说:“吉罗,你是一位法国将军,为什么还要让外面的美国士兵保护你?”他是一位意志坚强的人,他有勇气、有魄力。
邓小平是一个伟人,他引领贫困的中国发展成今天的模样,成为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指日可待。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有可能重走苏联的老路。
我崇拜丘吉尔是因为当时换成其他人可能就放弃了,但他说:“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田野里、在街巷里作战,我们永不投降。”在自己的军队吃了败仗的情况下能说出这种绝不向德国人投降的话是需要巨大意志力、勇气和决心的。
如果你问美国人他们崇拜谁,他们会说罗斯福。但罗斯福手中掌握着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工业实力。
不会把自己归入政治家的行列。
我不希望以政治家的身份被人铭记。首先,我不会把自己归入政治家的行列。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意志坚定、始终如一、坚持不懈的人,我脚踏实地地做事。我会坚持不懈,直至成功。没有别的了……任何一个认为自己是政治家的人都需要看心理医生。
别人会以什么方式铭记我,我认为我决定不了。生活中,我只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我从来不想搞政治。我想做律师,过上好日子,做一个好的顾问,但由于发生了一系列政治震荡,我无奈之下只有搞政治了。所以我肩负着很大的责任,我要负责让国家正常运转……
我能做的只是确保当我离开时,各种制度还是好的、健全的、清廉的、高效的,确保现有的政府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知道搜罗高素质的下届政府人选。
我并不是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但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基于高尚的目的。我必须做一些令人不悦的事情,以及把某些人未经审判就关起来。要盖棺定论,到那时你们再评价我。在闭眼之前,我可能还会做些这样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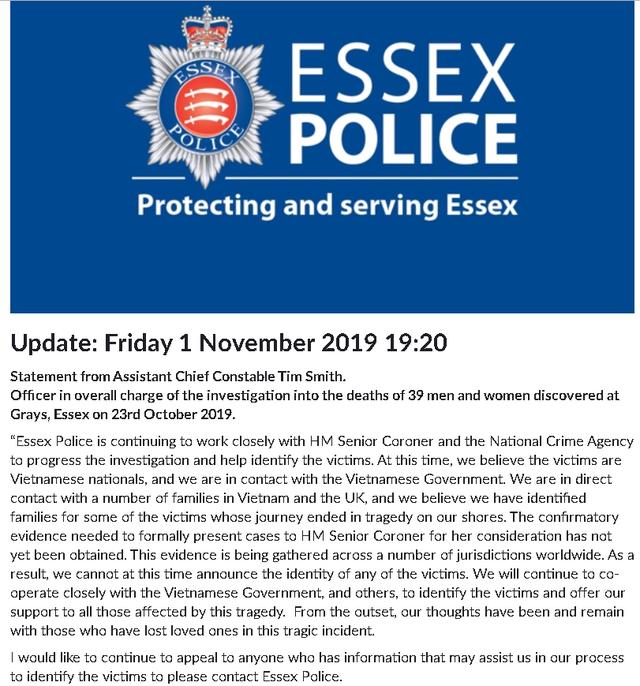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