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东方:涓滴教诲见真情——怀念余英时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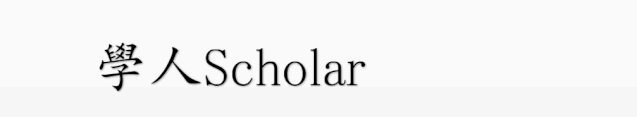

余英时(1930年1月22日-2021年8月1日)
作者简介:邵东方,现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斯坦福大学图书总馆顾问。本文原载自《汉学研究通讯》40卷4期。
一
大暑节气后的 8 月1日凌晨从梦中醒来,梦境里余英时先生为我在四条竹简上分别题写了一句诗,尽管我一再说不必为之操心费力了,他还是坚持要将这些竹简全部镶嵌起来。这个梦让我想起,距离 6 月初的两次通话,我已有近两个月没有向余先生和余太太陈淑平女士致电问安了。等到中午时分(余先生一般是晚睡晚起),我给余府拨打电话,无人接听,遂在晚间再次拨打,还是没人接听。次日及 8 月 4 日白天我又接着拨打数次,均无人接听电话。我便开始有些担心,因为两年前余府曾发生过电话不通的状况,后来向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边和教授打听才知道,当地的暴风雨造成余先生家中停电和电话中断。然而最近普林斯顿一带并无恶劣天气,莫非余先生或余太太那里发生了什麽意外?
8 月 4 日傍晚,朋友发来短信告知网上传闻:余先生于8 月 1 日早晨在睡眠中辞世。我不敢相信这则传闻是真的,因为余先生在几年前大病痊愈后,除了有些重听外,血压等指标都很正常,身体还是不错的。于是通过我过去在史丹佛大学的学生乔志健教授向边和教授查证。可是不巧边教授因近期不在普林斯顿大学校园而无法确认此消息。我便给在台北的友人、余先生的弟子王汎森博士打越洋电话询问。在电话中王兄沉痛地告诉我,余先生确实已经溘逝,根据余先生的生前遗愿,丧仪从简,因此余太太和两位女公子在余先生骨灰葬礼后,才于8 月 4 日向外公布余先生仙逝之讣。
8 月 5 日上班后,我向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中心(TheJohn W. Kluge Center)主任 John Haskell 通报了余先生逝世的噩耗,并请中心择日发布讣告。在安排好工作后,我便与朱先生在 8 月 6 日清晨开车前往普林斯顿。我们在中午之前抵达校园北边的普林斯顿陵园,是第一批前来祭拜余先生的人。在普林斯顿逗留的两天期间,我们顶着烈日酷暑,先后三次前往陵园,墓碑尚未刻镌树立,墓堂亦未告竣,我们向余先生长眠之地鞠躬祭拜、献花致哀、为余先生墓穴前的花木草地浇水。同时我也给安葬于同一陵园的友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前馆长马泰来(1945-2020)博士祭扫坟墓,敬献了鲜花。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不便进入余府打扰,只是将汽车停在宅前的车道上,下车面向余府,肃立默哀,表示敬意和悼念,并祈余太太节哀顺变,保重身体。
8 月 7 日下午,在我们即将离开普林斯顿时,突然接到余太太的电话,说知道我到了普林斯顿。我很惊讶,因为此行并未告诉她。余太太幽默地说她有“千里眼”(我后来才知道是王汎森先生告诉她的)。余太太问我是如何找到余先生的墓地的,我告诉她是在向普林斯顿墓园的一位年轻工作人员询问后,他特地开着电瓶车带我们去的。在得知我要购买鲜花省墓后,他便介绍了一家叫做 Vaseful Flowers & Gifts 的花店。余太太说墓园的工作人员都待人诚恳,认真负责,悉心尽责地照顾着墓地。她又问我是否看到洪家墓地(友人茅以森的外祖父母即洪业先生弟弟、弟媳,以及外叔公皆安葬于此),因为洪家的墓地就在余先生父母墓地的后面。
我向余太太转达了朋友们的哀悼和慰问。余太太对我说,她是从一而终的人。而她对人之生死的态度豁达开通,以为死生前定,凡事莫非缘法。她说:“余英时在睡梦里离开。他现在可以在天上与他的父母和我的父母交谈了。” 她说余先生的墓穴很深,她们在骨灰坛周围撒了许多茶叶(余先生生前喜欢喝茶,惟锺爱台北全祥茶庄特制的龙井绿茶),埋放了余先生的墨笔和稿纸(余先生毕生长于撰述,著书尤多),但忘记放进他生前使用的茶杯。我说或可在立墓碑时再放入墓穴。余太太提到,余先生去世后,她没有立即发讣,这是她和余先生生前的约定。直到余先生安葬之后她才通知了中央研究院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有关人士,连她的兄长也是从外界的新闻发布始知余先生谢世的。那几天她一直将家里的电话设置为静音,不愿意麻烦别人。余太太还很客气地说:“因为余英时的关系,我有了像你这样可信任的好朋友。”
我问余太太准备如何处理余先生的书籍及手稿。余太太说,余先生生前对这件事持很开放的态度,不想为此麻烦别人,并说有台湾学术部门有兴趣收藏。我深知余先生平生谦抑,不愿让朋友为他个人的事费心。于是向余太太建议,或可将国会图书馆作为捐赠计画的备份典藏地点,华盛顿毕竟距离普林斯顿比较近,而且国会图书馆是具有权威性的安全收藏机构,今后如想查阅余先生的书籍手稿也比较方便。
余太太还让我转告胡复先生(胡适之博士的唯一嫡孙),他寄赠的慰问花篮已收到,并提到他在余先生今年生日时也曾寄来花篮祝贺。余太太嘱咐我向胡复和他姨母曾淑兰女士表示谢意和问候,因为她目前暂时不能与大家通话道谢,只能先让我代为传话。我提到当天早上在余先生安葬处,看到傅铿夫妇献送的花束及他们留下一张有纪念文字的纸条。她说:“傅氏夫妇都很好,是上海人,傅太太常常做好吃的东西送给我们,所以余英时不缺好吃的。他们说今天是余先生的头七。我这个人可能比较西化了,所以不太清楚头七和五七之类的习俗。”我回家查询后告诉余太太,按民间习俗,头七一般指死者辞尘的第六天晚上至第七天清晨,其魂魄会回家,所以家人要为死者准备一顿餐食。
8 月 9 日 11 时许,余太太再次来电话,说今天去到墓地,看到我放在墓前的鲜花和余先生的遗照及题赞,表示存殁均感。还说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任田安(Anna Shields)教授给她打电话告知,普林斯顿大学校园从明天起降半旗三天以悼念余先生。余太太希望让我代她向所有吊死慰生的朋友转达衷心的感谢,盛情已领,容她目前不能一一回谢,至深歉仄。余太太说余英时是一个很低调和单纯的人,从来不想出风头,没料到他的去世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我答道,大家都想表达一下对余先生的悼念之情,“思由忆生,不忆故无情”,所以形成了一个悼念的高潮。她说大家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从普林斯顿回到家后,内人告诉我:她 8 月 6 日到本地邮局寄呈我们给余太太的悼唁卡片,用的是我在几星期前为准备寄给余先生的资料而事先写好地址的美国邮政优先快件(Priority Mail)信封。邮局的一位亚裔女营业员看到信封上余先生的名字后说:“He just passed away.”这偶然的一句话反映出余先生在美国亚裔中的知名度。
8 月 11 日,我收到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Association)执行编辑 Laura Ansley 的电子邮件,说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彭慕然(Kenneth Pomeranz)教授(美国历史学会前任会长)推荐我为美国历史学会官方期刊Perspectives on History(《历史的展望》)撰写纪念余先生的讣闻。美国历史学会是美国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专业历史学家团体。对我而言,能在国际主流的史学刊物上发表纪念余先生的文字,不仅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更是一种荣誉。根据刊物的要求,此类纪念文字通常偏重逝者的职业生涯,尤其要体现史学界同行对逝者的专业性评价,包括逝者对同事、机构、专业及历史学领域的贡献和影响(In Memoriam essays focus on thesubject’s professional life, but above all should be a historian’sappreciation of a fellow historian, including their influence oncolleagues, institutions, their field, and the discipline)。我连续数天重读余先生的重要著作和生平资料,尽量提取学术菁华,构思这篇英文限字 650-700 的讣闻,以简明扼要的方式,展示余先生的主要学术特点及其贡献。几天之后写完初稿,但字数远超预期,寄呈友人费乐仁(Lauren F. Pfister)教授加以删减润色,形成长短文稿各一篇,随后交上短稿,长稿则作为本文的附录一。短稿已经编委会审查通过,预定刊载于今年 11 月号的《历史的展望》。希望此篇讣闻的发表能使西方史学界再次认识余先生对中国史学研究的贡献,于我个人而言,亦可聊表对余先生的仰慕之情。
二
几天来,我和余先生三十年相识相交的往事不断地浮现在脑海中。我最初是在 1990 年 6 月通过来美国访问的冒怀辛先生介绍和余先生建立书信联络的,冒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方以智的专家,当时正在夏威夷大学讲学,并应余先生之邀访问普林斯顿大学。由于本师刘家和先生是钱穆先生在内地最后的一批学生之一、而余先生是钱先生在香港的第一批学生之一的缘故,我们的往来书信从一开始就非常自然,无拘无束。我初次见到余先生则是 1991 年 2 月 17 日在檀香山国际机场,由于航班在晚上抵达,李欧梵教授嘱咐我去机场接余先生,以便次日参加在东西方中心举行的“文化与社会: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反思”国际会议。我至今还记得当时见面的情形,余先生不顾十几个小时的旅途劳顿,到达东西方中心林肯招待所后,坚持要留我在房间里交谈一下。时隔多年,当时谈论的许多细节至今记忆犹新,记得余先生询问了我以清代学者崔述为题的博士论文的进展,并且很耐心地回答了我请教的清代学术的几个问题。余先生回忆了我的两位恩师刘家和先生和何兹全先生 1988 年到普林斯顿与他见面的情形,三人在一起交流极为融洽。他还风趣地提到了冒怀辛先生访问普林斯顿时不修边幅的趣闻。言谈之中,彼此深感投契。接下来的几天会议使得我和余先生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和交流,也开始了我们之后三十年的友谊。关于余先生和我参与此次会议的情况,可参看王元化先生的《一九九一年回忆录》。1
我和余先生比较频繁的接触开始于 2012 年 4 月我到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任职之后。我家距离余先生居住的普林斯顿只有不到四个小时的车程,因此得以每年有一到两次的机会驱车北上拜望余先生和余太太,得以面承先生之教。就我记忆所及,在这七年多的时间里,我登门访问不下十次,而平时的互通电话以及书信、传真则不计其数。
我和余先生比较频繁的接触开始于2012 年 4 月我到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任职之后。我家距离余先生居住的普林斯顿只有不到四个小时的车程,因此得以每年有一到两次的机会驱车北上拜望余先生和余太太,得以面承先生之教。就我记忆所及,在这七年多的时间里,我登门访问不下十次,而平时的互通电话以及书信、传真则不计其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推荐出版了他过去的博士生也是我在夏威夷大学的同学赵结(赵俪生之女)教授的著作Brush, Seal and Abacus: Troubled Vitality in Late Ming China’s Economic Heartland, 1500–1644。余太太也兴致浓厚地加入谈话,她特别提到他们余、陈两家与数十年中国现代历史人事世变有很大的关系。大家还一起讨论了不少美国的内政问题。我们从下午 3 点坐到 6 点多钟,余先生夫妇一定要留我们吃晚饭,我们坚持不要麻烦两位老人,遂向他们起身道别。临离开前,余先生在门口大声地叮嘱我:“你的工作很忙,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当我徐徐开出余府长长的车道时,望着暮色中余先生的身影,不由生出一种离别的伤感,两眼变得有些模糊。而我却没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和余先生见面!

作者(左一)与余英时教授伉俪合影
疫情期间,我曾多次和余先生、余太太通电话,互致问候。近几年来,余先生有些重听,有些电话是透过余太太沟通,但是重要的事情,余先生则是在余太太拨通电话後亲自説话。我们最后一次通话是 6 月 4 日,晚上 9 时 50 分余太太来电话说:“余英时要和你说话。”余先生先是答覆我前一天在传真中的问题,即记载何兆武先生到耶鲁大学访问余先生一文作者的真实姓名。那篇发表在“澎湃新闻”的文章为《何兆武因翻译〈西方哲学史〉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余先生说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喻松青女士,她当时(1982 年秋)在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研究明清两朝的宝卷。余先生请何先生到家里吃饭,喻女士作陪。余先生说自耶鲁大学别后与何兆武先生就联系不多了。在 6 月 1 日的通话中,余先生在得知何先生以百岁高龄去世后,嘱咐我向清华大学治丧委员会转达他的悼念,并说何先生是得享期颐高寿。我谈到有一年(约 2008 年)何先生托我把《上学记》的修订本带到美国转给余先生。由于初版里面何先生对冯友兰先生在西南联大的一些做法颇有微词,冯家后人表示抗议,何先生不得不删去有关部分,又出了修订版。余先生问我如何与何先生比较熟悉,我说因冒怀辛先生的缘故而早在 1985 年就认识了何先生,上世纪 90 年代末我曾邀请何先生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开会,以后休假回北京时常去看望他。余先生记得何先生曾协助侯外庐撰写中国思想史。我提到何先生还有《上班记》(即 1949 年之后的经历)的稿子,在世时不敢出版,因为怕得罪人,其中谈到侯外庐、顾颉刚、谢国祯以及历史所的领导。交谈中,我感谢余先生日前赐寄新书The Religious Ethic and Mercantile Spirit in EarlyModern China 和最近在Asian Major 发表的文章“ConfucianCulture vs. Dynastic Power in Chinese History”。承蒙余先生高擡称举,赐文上端亲笔题字:“东方兄正之 英时赠2021. 五月”,并在赠书扉页题签:“东方吾兄正之 弟英时敬赠 2021. 5 月 26 日於 Princeton”。余先生说他现在很少寄书给人了,只寄给极少数的朋友,等 9 月份他的自传英文版出版后再寄给我。我明白,余先生馈赠大作,是让我留作永恒的纪念。我提到田浩(Hoyt ClevelandTillman)对The Religious Ethic and Mercantile Spirit in EarlyModern China 英译文进行区别取舍,做了很好的整理编辑。余先生对此深表赞同。我还告诉了余先生一些友人的情况,如 P. J. Ivanhoe 最近获任乔治城(Georgetown)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任,友人庄因先生多年前为他取中文名艾文贺,而他和他的博士导师倪德卫(David S.Nivison)恰巧是同一天生日,这在师生中是罕见的。我们聊了二十多分钟,不料这竟是我和余先生的最后一次谈话。

罗原夫妇(右 1、2)访问余英时教授,左为笔者
余先生与我这样一个晚辈学人谈话时,始终是一种出于自然的对人平等的态度,他知我慎言谨行,我们的价值系统又大体相近,所以我们之间几乎无所不谈,十分投缘。余先生在学术上的深厚造诣,学界早有公论,而每相论学,他总是那样的谦和,从不居高临下,让人感到有压力,这也是余先生的人格魅力所在。《朱子语类》原序云:“晦庵朱先生所与门人问答,门人退而私窃记之。”我效法朱子门人,每次长谈后便将萦回在脑际的谈话内容记录下来。历时近十载积累的三本笔记,记载了我生平极为珍惜的一段经历。余先生关于思想学术的谈话,字字珠玑,尽管记录未必尽得余先生所言本旨,但每次翻阅都能使我不断从中得到思想和知识的滋养。笔记中还记录着余先生对我的充分信任和关心爱护,语语真挚,他亲切的音容印刻在我的谈话笔记之中。
余先生向我讲述现代学术时最精彩的部分,就是他对若干华人学者的评论,特别是他对诸位史学家学术成就和为人处事的褒贬,勾画出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质,尤其是史学的变化轨迹、发展特点及未来展望。分析之精当,令我深为叹服。希望今后在适当的时候,我能把这些记录整理成册,或许能为中国现代学术史提供一些新的资料。苏轼曰:“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借苏子之言,我认为中国史学至于余英时先生,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
三
在 2008 年的初秋,我从纽约驱车前往余英时先生府上拜访。这是我时隔九年再次见到余先生。1999 年6 月我和友人、史丹佛大学哲学系荣休教授倪德卫先生曾到普林斯顿大学与浦安迪教授(Andrew Henry Plaks)讨论《竹书纪年》的英译项目,会後余先生邀我们到他的办公室叙谈了一个下午。而 2008 年这一次我借着看望的机会,对余先生进行了一次学术采访。尽管余先生在前一段时期贵体欠安,但还是对这次访谈作了充分准备。在长达三个多小时的访谈中,余先生对自己治学的经历和经验娓娓道来,让我这个晚辈学人受益匪浅。他磨而不磷、涅而不缁的节操,令人仰慕不已。这次访谈的记录已收入我为余先生编辑的《史学研究经验谈》一书之中。2 我在此书的编后记中写道:
对于余先生的学术成就和人格风范,海内外学林早已有公论,在此不再赘述。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学术史的演变就像社会历史的发展一样,并非能简单地归纳成一种累积式的进化。余先生作为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时代意义和发生不朽魅力的学术泰斗之一,是在上个世纪某种特定的政治与文化条件下出现的。尽管近年来国内外的人文学研究在各个领域有了长足发展,“江山代有才人出”,然而产生余先生这一代“师承国学大师、遥领西方汉学”的通儒的学术环境已不可复得。所以我认为像余先生这样的会通古今、融贯中西类型的文史大家,近期内在中国学术界以至海外汉学界无能出其右者,诚如钱锺书所谓“海外当推独步矣,即在中原亦岂作第二人想乎”!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虽不能往,心向往之。记得十一年前余先生曾抄录孟子之名言及胡适之佳句,托我转赠吾友陈宁博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时髦不能动。”我想这些话也应当是对余先生行谊的最为恰当的写照。最后让我改写前人之语来作为这篇后记的结语:
今之儒者,道德文章足以楷模百世、矜式士林者,厥惟以潜山余先生英时教授为最。先生为一代儒林宗硕,通知大义。中国文化之所以倾而未颓,决而未溃,皆先生诸仁人君子心力之为。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今天,余先生已经登仙而去,他的离去使我失去了一位最敬重的良师益友。最后,我还是想用上面十一年前所写的话,作为这篇悼念余先生文字的结语。
原文附有作者所作余英时先生英文行状,此处有节略
注释:
1王元化,《一九九一年回忆录》,《九十年代日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页 50-76。
2 余英时著,邵东方编,《史学研究经验谈》(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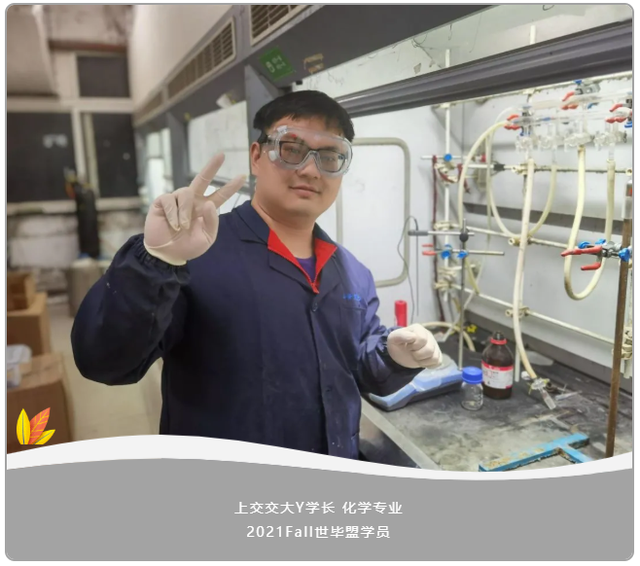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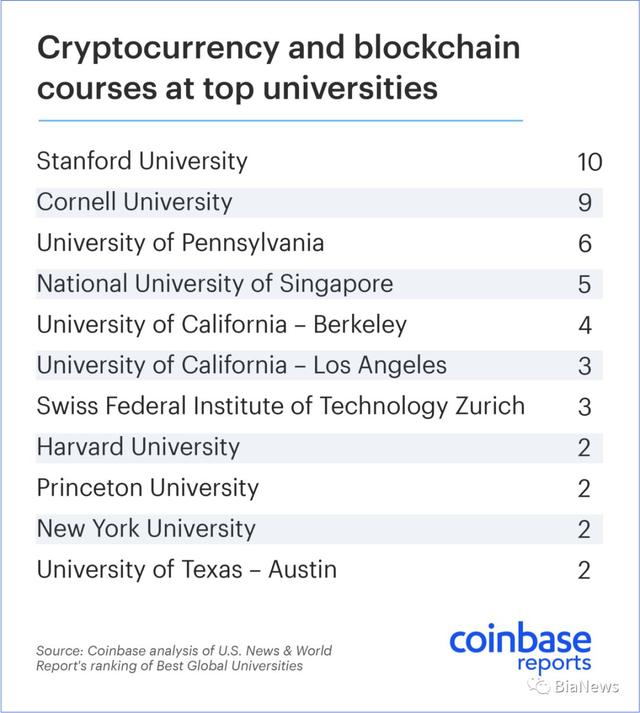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