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清,出国就像是一种本能!我们这一去,不知道啥时候可以回来

其实,与那些落后地区的居民整村出外讨生活并没有什么不一样,最大的区别或许是,我们这一去,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来。
原创:陈齐云
在我的家乡福建福清,户籍人口约135万,有接近一半的人在国外。
在老一辈福清人的眼里,出国赚钱的孩子,总要被人高看一眼。从前,当地人管从海外归来的人称为“番客”,而现在,“番客”则成了“有钱人”的代名词——不管在国外是收废品还是刷盘子,回来的都是“番客”,该盖房子的盖房子,该讨媳妇的讨媳妇。
我也算是番客。
2007年,我前往澳洲留学,第一份工作是在华人餐馆烤羊肉串,工资每小时6澳币,比当时澳洲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每小时10澳币还要低上很多。为了让我出国,家里前前后后花了20多万,父母为我借来的钱是要还的,所以我只能又找了一份给水果店理货的工作。要考雅思、要上学,加上打两份工,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两年。
2010年,我把家里的债还清了,也拿到澳洲身份,专心在一家超市工作,工资变成了一天200澳币。在我的担保下,哥哥和表妹都来了,后来旅游工作签证开放,两个表弟也辞掉工作来澳发展。
2012年,建筑行业大火,我又改了行。到2017年,工资已从一天120澳币涨到400澳币了。
这一年年底,我带着自己的全部存款10万人民币回了国——我讨厌澳洲一成不变的生活,想要完成自己儿时的梦想,当一个作家。
在家乡所有人眼里,我是属于“在金山面前临阵脱逃的”,受到非议自然是无法避免的事,也有等着看笑话的。
那时,我安慰自己:在农村,这么多钱总可以体面地活上一两年吧。可人算不如天算,今年5月,我认识了现在的女朋友田融融,想着今年就结婚。所以,这点写作基金在恋爱的开销下捉襟见肘,而且,我还必须要面对结婚的庞大花销——聘礼、酒席、房子。
我不得不重新考虑:是接受嘲讽,回澳洲继续在工地上打工,还是咬着牙坚持看不到什么希望的写作生涯。和许多人所面对的一样,理想与现实,像两匹分道扬镳的骏马,终于在我面前泾渭分明起来。
男人这辈子就两件事:起大厝,讨媳妇
那天,我和田融融从那栋5层别墅里出来的时候,福清刚下过一场大雨。
这距离她离开福建返回故乡四川,还有一天的时间。在认识我之前,她从未听过这个叫做福清的地方,在她的观念里,出国留学回来的人非富即贵。直至好久之后,她说自己都没法将那个矮小黝黑、青筋暴起的男人和这座别墅联系起来。
别墅是我姑丈2015年建好的,据说花了近100万。姑丈在市里的小区做电工,一个月能挣2000块左右,绝大部分建别墅的钱,都是他大儿子鹏成和二儿子鹏生借着留学的名义在外打工攒下来的。
在这个别墅林立的沿海村庄,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亲人在国外,他们用各种手段越过大洋,到另一个国家谋生,幸运的拿到居留证留在那里,不幸的就变成黑民,躲避警察和移民局,等到所有青春耗尽,再带着在异国出生的孩子和兑出来的人民币,回到故土。
“这哪里像一个村庄。”田融融看着狭窄的村庄小路旁一座座极不协调的别墅,“我终于理解了你当时说的那些压力了。”
我的压力,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我家那座饱含着两代人心血的别墅——它在两年前刚盖好,4层。那一年,我和哥哥将在澳洲工作的所有积蓄全部寄回国内,每人大约45万,加上父母的积蓄,最终耗资120万,盖起了这座别墅。
福清人对于在出生地建造一座别墅有一种执念,不管人在哪里生活,在家乡要是没有房子,尊严就无从谈起。按照当地人的说法,男人这辈子就两件事:起大厝,讨媳妇。“你要是没有房子,没有女人愿意嫁的”。
第一次带田融融回家的那天,也是下着雨。我妈听到车子停在门口的声音,拿着我哥哥结婚时接新娘用的红伞,在田融融的头上打开,夹在伞里的礼炮的余屑落了她一头。
事后田融融问我,这是不是风俗,我说不是。但我想,我妈等这一天,应该等了很多年。我今年33岁,她在我这个年纪,我哥已经12岁了。
田融融临走前的夜里,我妈拿了一袋子礼物上来,要她带回去给亲戚朋友,里面有澳洲的绵羊油和木瓜膏,英国的香水,新加坡和日本的药,以及阿根廷的橄榄油——绵羊油和木瓜膏是我和哥哥从澳洲寄给她的,香水是姑丈的大儿子鹏成寄回来的,新加坡和日本的药是她的朋友送的,阿根廷橄榄油是我堂姐去年给的。
田融融讶异不已。但其实,这与那些落后地区的居民整村出外讨生活并没有什么不一样,最大的区别或许是,我们这一去,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来。
回来做什么?你说你回来能做什么?
“林文镜死了。”我把水烧开,倒进茶碗,“也就是昨天的事。”
姑丈把茶盏往这头推了推,在此之前,他仔细询问了田融融的动向——她已经返回四川了,昨天从成都回到西昌,今天要赶往凉山的美姑县,她家人开了一个广告店,叫她回去帮忙。
“没有了,都没有了,这批人死得差不多了。”姑丈说的,是我爷爷那一批下南洋的人,其中的翘楚就是林绍良和林文镜。他们在晚年荣归故里,兴建公路、桥梁、学校和医院,并以各自父亲的名字命名。我就读的学校就叫元载中学,那时林绍良来学校参观,我们就穿着白色的衬衫和黑色的西裤,脸上涂上胭脂,拿着塑料假花列队欢迎。
印象中,这位前印尼首富是个满面红光的慈祥老头,步履缓慢地夹在陪同的人员里往前走,也许他不曾想过,在这些列队的孩子里,会有多少人跟在他的身后,越过大洋,到另一个陌生的国度不情愿地开始一段新的人生。
“他们那时候偷渡,真是命搏命,去日本,货轮里藏几百人,一两个月不见阳光,死的丢海里,活的继续走,到码头,缆绳一挂,一人一条白毛巾搭着滑下去。去阿根廷,去英国法国,穿过边境时,就躲着那些兵的子弹跑。现在啊,一张机票就到了。”姑丈说这些话似有所指。我知道他在提醒我,要珍惜得来不易的绿卡,别一时头脑发热,葬送了大好前程。
“巧燕高考考得怎么样?”我岔开话题,问道。
巧燕是我堂哥的孩子,我的侄女。堂哥这些年一直在做留学中介,去年7月,全市打击黑中介,被人在办公室摁住。被拖累的,还有在那里打工的姑丈的三儿子鹏强。今年6月,两个人的判决书都下来了,堂哥因伪造材料谋取利益获刑4年,鹏强作为从犯缓刑3年。宣判的时候姑丈去法院旁听,律师是从堂哥的动机为他辩护的:“出国向来是福清人民就业的一大方向。”
“听说考的不好,她要是没说,我们就不要问。”
“有没有说以后要怎么安排?”我问。
“还能怎么样?出国呗。”姑丈答道。
眼下,出国的形势似乎也不太好,特别是像巧燕这样高中毕业就出去的孩子。
阿根廷的汇率前段时间跌得太厉害,开超市的那群人叫苦连天。治安也不太好,巧燕的大姑姑、也就是我堂姐一打电话回来就抱怨:“无所事事的西人(泛指外国人)拿着枪来要钱,多多少少都要给一点……人也不好请,华人不多,西人不肯出力干活。”
至于澳大利亚,要是男孩去倒还好,工地的杂工1小时也有十几澳币,肯吃苦肯学,两三年就能成大工,工资就有35澳币左右,节俭一点还能剩不少钱。可女生的话,最多的是餐馆的服务员,工资很少有超过20澳币的,还得能吃苦、脾气好。听说前段时间有做旅游签证去澳洲的,一个人20多万,一个团60个人去,一个都没回来。澳洲政府急了,狠狠抓了好一阵子。
日本要是肯吃苦,也是找得到工作的,但就是工作时间长,经常要两班三班倒;南非没有亲人,也不敢试,有朋友回来说,洗澡很不方便,也乱。
欧洲基本没戏,朋友前段时间刚从瑞士回来,办的也是旅游签证,活儿少,工资也不算高,没收入就不敢花钱,每天老干妈就馒头;英国工资也不高,汇率也跌,鹏成到现在每月也就拿1万多人民币,上次打电话说想回来,姑丈劝他暂时不要回来——他是黑民,机票只能买单程,回来能做什么?国内工资一个月才两三千,倒不如再在那里待一阵子。可是家里的大人又担心,年龄那么大了,再不回来讨媳妇,估计以后就更难了。
“你什么时候去四川?”姑丈问我。
“7月7号,还剩3天。”
“从长乐机场过去要多久?”
“我没买机票,想试试绿皮火车,要38个小时。”
姑丈想说些什么,却明显欲言又止了,也许在老一辈眼里,我这种行为真是不可理喻。
“今年打算结婚吗?”
“打算是打算,不知道那头同意不同意。”
“礼金,酒席,聘礼,怎么说也得二三十万,不容易啊。”姑丈压低声音,“有没有后悔,从澳洲跑回国写东西?”
“没后悔。”我笑起来,给自己添满茶。
“还没后悔啊!等你要用钱的时候,估计就该后悔了。”
我不说话。
姑丈看出我脸色的变化,讪讪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做人不要后悔才好。”
他把余下的茶喝掉,站起来要走,我送他到楼下,临出门前,他又递了一根烟:“你说林文镜死了,是从哪里看到的?”
留在家乡打工,总有人说你“没本事”
不规律作息导致的失眠,在世界杯期间更为剧烈,田融融一回四川,我的生物钟就以每天延后1小时的趋势往天亮的方向推移,她总在提醒我休息。
再过一天,就要去四川了,田融融临走前交代我,一定要去医院把布满烟垢的牙齿洗洗,好给她父母留下一个好印象。
出门沿着老街,很快就经过了祖屋——这是我曾祖父下南洋的时候建的,现在早就没有人居住了。数百年前,他将整个人生砸进陌生的国土,忍受寂寞和思念,在老年时期回来,带着一条残腿和一整个包袱的金条。我的祖父、父亲都是在这里长大,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出国赚钱起大厝的想法,像扩散的白细胞一样,钻进人们的血液。
然后再往前走,就是姑丈家,按习俗,父母住一层,在英国的大儿子鹏成住第二层,在澳大利亚的二儿子鹏生住第三层,和我堂哥一起被判刑的鹏强住第四层。
这里的建筑几乎只有两种:建于一百多年前的土夯的祖屋,受徽派建筑影响,红墙青瓦;另一种则是新建的别墅式样的楼房,少则四五层,多则七八层,就孤零零地建在那里,门口坐着一对看家的老人。
镇上几乎看不到什么年轻人,在这里,留在家乡打工的人,都被认为“没本事”。而从国外回来的年轻人宁愿在外租房子,也要倾尽全力,甚至不惜借钱在老家盖一座别墅,这是面子。在这个南方小镇,面子大过一切。至于里子,谁在乎呢?
从村里穿出来,走在县道上,在镇子的环岛边上,是我同学刘斌的家。刘斌在我高中的时候辍学去法国,先坐飞机到邻国,再沿着国境线,被边境的士兵在后面开枪追着,玩命地跑。
蛇头怕这些人反抗,一天只给一个面包一瓶水,还不让他们打电话回家。一群人边走边等机会,整整奔波了一年,才终于进了法国,打电话回家报平安,她妈接到电话的那一刻,就嚎啕大哭起来——她以为自己的孩子早就没了。
据说刘斌现在黑在了法国,娶了个媳妇,跟他妈妈矛盾很深,很多年不回来了——到头来,他妈妈的孩子还是没了。
再往前走,我终于找到了那家牙医诊所,出国前,我曾来这里拔过牙,以前诊所里的老头子是四里八乡有名的牙医,现在诊所里是个小年轻,听我妈说,老头子死了,他的儿子接过诊所和仪器,就像所有的传承一样。
镊子在嘴里的时候,我心里一直想,只剩一天,我就要踏上从未踏过的旅途,那个衰老的绿皮火车会带给我什么样的风景我不得而知,但在中国的西南,有我未来的妻子——我坚信这一点。
我跟田融融是在回国后的一个写作群里的认识的,那是5月的事情。“好像一整个春天的花蕾都在那一刻绽放,又好像二十只毛茸茸的小奶猫同时瘫成一片等待抚摸。”田融融这样形容我们的相遇。
我们很快就陷入爱河。她那时候刚好辞职,我们约定在厦门见面,一起相处了8天之后,6月1日,我带她回到我福清的家。
你所厌恶的,恰好是你的救命稻草
弄完牙齿回家,我正在收拾明天要带的行李,田融融发了微信:“我跟你商量件事。”
这语气让我预感不详,放下东西,走到楼上,那头又发来:“你能不能过一阵子再来?”
我打电话过去,响了四五声,田融融才接了起来。
“怎么忽然变卦了?我都在整理行李了。”
“家里有点忙,我怕你来会影响到我的工作,还有他们也怕招呼不周……”
“他们是怕我把你带走吧?”我打断她的话——田融融给我说,她这次回美姑,着实被那里的环境吓了一跳——县城是全国贫困县,这么多年过去,还是又脏又乱,小得就像一个村庄。她想走,但亲戚苦口婆心地劝,我们之前的计划就是,先去见见她的父母,再好好跟他们说说。
“你别这样。再等一个月,好吧,就一个月。”
“这么正式的场合,怎么就改了,而且还改得这么突然?”
“你等下打给我,他们叫我了。”
田融融挂了电话,我妈就上来了,看我行李收到一半,问:“怎么不收了?”
“那边说,再等一个月。”
我妈当即就暴躁起来,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当初就说别让她回去工作,现在好了吧,他们把她栓在那里了,哪里有请不到的人啊,非要这么远请她回去。我当时就跟你讲了,肯定是先骗她回去,然后现在啊,都不知道施的什么计。”
“你别说了!”我吼起来。
妈妈叨叨着下楼了。
我点了一根烟,站在阳台的洗衣池边上。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田融融又打电话过来,听语气,像是受了很大的委屈。
我静了一下,告诉田融融:“你别怕,我可以养你,我还剩3万块钱,可能到9月10月我可以拿到两三万的稿费。如果你真的不喜欢那边,不要考虑钱的事,我可以养你的,省着点过日子,总不至于熬不出来。你也别怕没有事情做,你要是不想写也没事,我还有很多稿子,你可以帮着我看看,网上有很多投稿的地方,稿费都挺好的,你就帮我投。如果我写出来了,我们就留在成都或者福建,如果我没写出来,你要是愿意,我们就一起出国,悉尼至少比凉山环境好。”
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问:“澳洲一年能赚多少钱?”
“我们这样的,在建筑工地做弹线,或者大工,一个小时40澳币,一周大概2000左右,一年干满,差不多40万到50万吧。女生的话,一般的工作在十几块澳币肯定有,一个月一两万吧,你放心,只要你到那边,就什么都不用担心,我会为你安排好的。”
田融融似乎在考虑。
我想起她上次跟她妈视频,先是告诉她我在国内写作,她妈妈脸色一下子变了。后来又说我之前是在澳大利亚工作,每天收入人民币近2千,她妈马上就问,能不能带她的弟弟出去。
过了一会儿,田融融压低声音说:“我考虑一下,你说的出国。”
我站在窗台边,身后是整理到一半的行李,心绪久久不能平静。
田融融劝我,先把票退了,她跟那边再商量一下,看看什么时候适合我过去。我重新回想,发现田融融的确是对出国更有兴趣——这真是讽刺,起初你所厌恶的、只为活着而活着的生活,在你需要的时候,就忽然成了你的救命稻草。
眼下,绿卡就是我的救命稻草。
晚上刚过了9点,村庄就没有什么人走动了。
夏天的晚风最适合乘凉,一对一对刚过半百就早早退休的老人,在装修精致、立着石柱子的院子口摇着蒲扇,院子里幽幽的光,照着旁边数百年前古旧建筑飞檐的轮廓。
这种视觉上的违和似乎也印证着这片土地上怪相:孩子读大学,大多都是因为出国容易。他们忘掉所学的知识,从一架一架的飞机上下来,投身进入异国的工地、餐馆和小超市。而数年之后,他们因为没有合法居留被遣返的时候,那些在异国的籍籍无名,就全都变成了光宗耀祖的资本。
因为买的是绿皮火车,要去始发站拿到车票才能退,我不得不去一次福州。
到车站退了钱,只买到了晚上7点回福清的票。我坐在进站口的角落,问田融融:“我什么时候再去?”她没有回我,也许是没看到信息,也许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电话忽然响了,是巧燕的妈妈,问我一大堆澳大利亚出国的情况。
我忽然回想起姑丈那天离开我家时,又一次问我:“林文镜是不是真的死了?”我说是的,他死了。可是现在回想,林文镜哪里会死?他以另一种形式活在所有福清的孩子身上,将生的、已生的,只要你在这个地方,身上或多或少会有那个东西,它平时隐蔽起来,或者只是在你的耳边嗡嗡鸣响。
而当你走投无路或者无所事事的时候,年老的总是会说:“出国去吧。”多少年来,这句话带动着家乡的经济,多少也毁掉许多年轻人的青春。
我现在才明白,外国钱也不好赚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田融融做的第一个设计单子上,一个彝族学校需要设计校徽,校长只要结果,也不给方案,田融融设计出一个,校长就推翻一个,她感觉很受挫,也完全没法交流。
另一个原因也许更为关键,美姑县的环境确实让田融融很难适应,落后、肮脏,几乎没有什么娱乐设施,交通极其不便,包裹能送达的快递公司寥寥无几。她问了好几个朋友,大家都劝她赶快离开。
终于,这个从未忤逆过家庭的女孩决定反抗一次,过程当然并不顺利——那个地方能招到设计师的概率极低,他们自然不愿意放走这个亲戚。
田融融还是定下了离开的时间,我几乎没有犹豫地定了去成都的票——这一次,我选了4个小时就可以到的飞机,绿皮火车窗外的风景,下次吧。
7月12号,出行的前一天,我的朋友陈俊明过来看我,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赚不到钱就从国外回来的人。一年前,陈俊明和他的妻子花了12万,以旅游的名义去瑞士,合法居留只有3个月时间,他去了快一年才回来,妻子还留在那边。
我们坐在大厅泡茶来喝,陈俊明把整个后背贴在红木沙发上,全身瘫下来,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快速地解掉工作一整天的困乏——眼下,他在隔壁镇的一家玻璃厂做临时工,一天工作14个小时,170块钱。喝下一口茶,他转过头说:“我现在才晓得,你以前说的,外国钱也不好赚。”
“日子还长,赚钱也不急着一时。”我宽慰道。
陈俊明刚到瑞士时,暂住在一个远房亲戚那里,之前说好的工作试了一两天之后,就不要他再来了。他们两口子住了几天,情面上过不去,就搬到郊区的一个仅有10平方米的住屋。他的妻子先是在餐馆洗碗,没做多久就因为手慢被辞退。陈俊明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只能搬家的干两天、清洁的做两天,没有稳定收入,什么钱都不敢花。这样过了好几个月,才终于在一个饭馆里安下脚。
干了十来天,一个繁忙的周六,执码(配菜工)没有来,陈俊明临时顶上。由于没有配菜的经验,一时手忙脚乱。大厨忙不过来,大骂:“你这蠢猪怎么这么蠢!”陈俊明应了一句:“这是我第一次做执码!”
就这样,他唯一的一份稳定工作也没有了。
陈俊明佝偻着腰,端起茶送到嘴边,并没有喝:“要是我能去你那边就好了,至少不用受这份气。帮我再问问澳洲那边有什么门路吧。”
“我有两个表弟是做旅游工作签证,需要雅思和本科毕业证书。很划算,过去就花了不到2万块,但你考不了英语,也没毕业证书。做旅游的话,这段时间好像没有什么人愿意做。”我说,“刚开始去的时候,谁都是苦的。我最苦的那阵子,没比你轻松。”
“至少不用为工作发愁吧。”
“那倒是,工作的事不用太担心。”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澳洲?”
“过阵子吧,先把这边的事弄弄清楚。”
只要旧路返回,就能安全上岸
飞机是晚上8点,天空又下着雨。
田融融剪短头发去机场接我,成都也刚下过雨,天还不至于热,到酒店刚放下行李,田融融就告诉我,她的父母知道我劝她从小姨那儿离开,暴跳如雷,现在已经下了死命令——不准她再去福建,也不准我来成都。也说到了出国的事,他们觉得太远,想见也见不到,想去也去不了,受了委屈,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之前还问我弟弟能不能去那边干活,现在又忽然变卦了。”田融融埋怨道。
我理解这种担忧,从他们那个村到县上火车站要两三个小时,火车站到成都七八个小时,成都到悉尼又要十几个小时。也许数百年前,那些看着子女登上船离开家乡的福清人也有这样的担忧,那时候能交流的只有书信,一去一回,半辈子就过去了。
不像川府自古富饶,福建多丘陵、耕地少,在红薯和玉米传进中国之前,经常有人饿死——也许这就是那个年代的人不要命地往外跑的根本原因——在死亡面前,背井离乡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田融融的姐姐也在成都,在家里说话也算有分量,我们决定先见见她。那天晚上8点多,我们吃完饭,田融融去洗碗,她姐姐就问我:“我听人说,写作的收入很不稳定。”
“我只是回来试一年,如果不行,今年11月份就会重新回澳大利亚。”
“你在澳大利亚做什么?”
“做建筑。”
“你是学这个的?”
“不,我学的是工商管理。”
“那你去的话,融融可以一起去的吗?”
“如果结婚证办好了,就可以一起申请。”
姐姐似乎得到了满意的答案。在接下来的交流里,我们聊狗、聊食物、聊疫苗事件。晚上10点,姐姐打电话给田融融:“跟家里商量好了,他们不再反对了,婚礼要是可以,下半年就办了,礼金就随那边的,15万。”
在姐姐提礼金之前,我就已经给自己算过账了。我带来成都的2万块,1万给了田融融,用来支付房租和押金,1万买零零碎碎的生活用品,已经剩下不到5千。
就算也有稿费,田融融还是担忧,害怕两个人赚的钱不够维持生活的费用。我宽慰她:要是实在不行,我们可以一起去国外,赚一年回来,够花两三年了。
我很清楚,现在,去澳大利亚赚钱已经不是救命稻草了,它像一个涉水者转头就可以见到的岛屿,只要沿着旧路返回,就能安全上岸。而如今的我,又有什么立场去憎恨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呢?田融融说,从成都到越西县,需要坐绿皮火车,那里有许多山,铁路就穿山而过。现在这段时光,就是我的“绿皮火车”在穿越幽暗的隧道。
家里人时不时地打电话来,问我什么时候回澳洲。
巧燕没考上本科,她母亲希望她学一门手艺,再去澳洲;我建议她先报一个专科,等3年之后再打算出国的事,或者复读,再给自己一个机会。巧燕说,她想学习美甲,一个同学在悉尼的美甲店工作,一周800澳币;我的姨丈和阿姨前阵子拿着澳洲的探亲签证去了那里,暂时还没有找到工作,姨丈给我打电话,要我帮忙留意工作的事,挂了电话,他给我发来几张澳洲天空的照片,问我:“想不想悉尼?”
我们在机场旁边租了一处便宜的小房子,每夜都有飞机呼啸的声音。
一天夜里,田融融快睡着了,还迷迷糊糊地说:“也许这架飞机是去悉尼的。”
也许这个声音,在她的心里也是一声召唤。
(编者注:林文镜,1928年3月 - 2018年7月2日,福建融侨集团的缔造者,印尼“林氏集团”两大股东之一,该集团拥有世界最大的水泥厂和面粉厂。)
编辑:沈燕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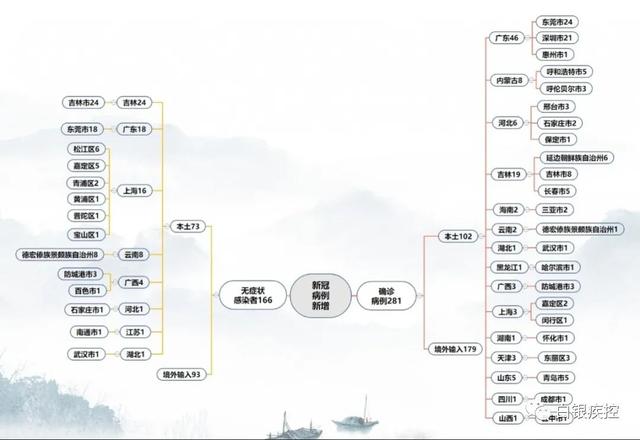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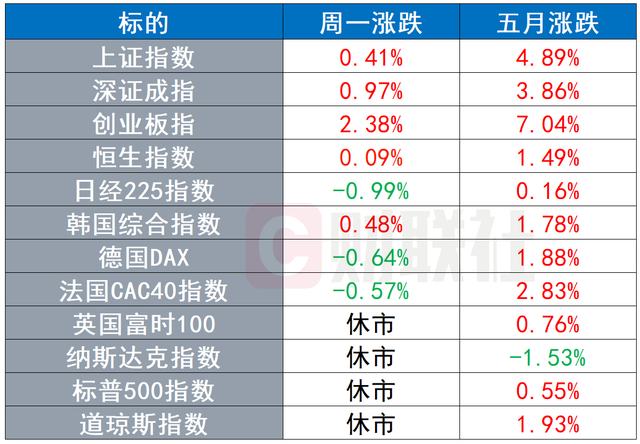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