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生长|从“龙利得案”到“布兰特伍德案”: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的突破
王生长
国际商事仲裁理事会(ICCA)的理事、顾问,法学博士
要目
一、2013年3月的“龙利得案”
二、2020年6月的“大成产业案”
三、2020年8月的“布兰特伍德案”

就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而言,“龙利得案”解决了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的仲裁协议效力问题,“大成产业案”明确了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不涉及仲裁市场开放问题,“布兰特伍德案”按照仲裁地标准为确定此类仲裁裁决的籍属和执行依据提供了指引。在中国仲裁法修订时,应当对标国际先进规则,确立处理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的一系列法律规则,营造法治化、可预期的仲裁环境,为使中国成为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而不断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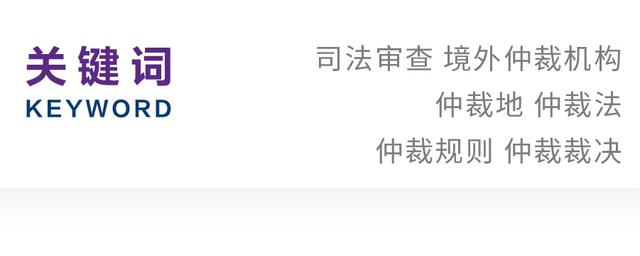
关于境外仲裁机构能否在中国内地仲裁问题,多年来意见纷纭。问题的主要结症是对我国仲裁法第16条如何理解适用,即在仲裁法第16条项下作为有效仲裁协议必备要件之一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是否可以从宽解释为包括了境内外的仲裁机构;进而言之,如果境外仲裁机构可以视作仲裁法第16条下“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在内地管理仲裁程序,那么它们在内地作出的仲裁裁决是什么性质的裁决,在中国法院依据什么法律条文申请执行。
2013年以来,通过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活动,围绕这个问题的迷局逐步明朗,司法机关的实践渐趋一致,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已经可以破冰起航,即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鉴于此,本文简要回顾在过去几年中有标志性意义的三个司法案例,并就在仲裁法修订时如何妥善处理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的一系列法律规则,营造法治化、可预期的仲裁环境提出意见建议。
一、2013年3月的“龙利得案”
案情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安徽省龙利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BP Agnati S.R.L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的请示的复函》显示:
安徽省龙利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利得公司”)与BP Agnati S.R.L及江苏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于2010年10月28日签署了一份《销售合同》。该合同第10.1款约定任何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其有关的争议应被提交国际商会仲裁院,并根据国际商会仲裁院规则由按照该等规则所指定的一位或多位仲裁员予以最终仲裁,“管辖地”应为中国上海,仲裁应以英语进行。此后,因履行合同发生争议。龙利得公司遂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合肥中院”)确认前述仲裁条款无效。
龙利得公司认为,上述仲裁条款因违反中国仲裁法的相关法律规定而无效,理由是:首先,国际商会仲裁院不是中国仲裁法项下的仲裁机构,约定将争议提交给其仲裁不构成有效仲裁条款;其次,国际商会仲裁院在中国进行仲裁违背了中国的公共利益,存在侵犯我国司法主权之嫌;其三,即便国际商会仲裁院在中国境内作出裁决,该裁决也应属于仲裁法规定的“内国裁决”,不能依据联合国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受到承认与执行。
合肥中院审查后认为:首先,该仲裁协议在约定仲裁机构为国际商会仲裁院的同时,又明确约定仲裁管辖地为中国上海,但关于国际商会仲裁院等国外仲裁机构能否在中国境内从事仲裁活动,仲裁法并未明确规定。尽管如此,当事人既然选择在中国内地进行仲裁,该仲裁从法律意义上说应当属于国内仲裁,并非纽约公约规定的“非内国裁决”。其次,根据仲裁法第10条的规定,仲裁在中国是需要经过行政机关特许才能提供的专业服务,而中国政府也未向国外开放中国的仲裁市场,故外国仲裁机构依法不能在中国境内进行仲裁。因此,合肥中院认为国际商会仲裁院并非符合仲裁法规定的仲裁机构,约定将争议提交给其仲裁的仲裁协议不是有效的仲裁条款。
合肥中院将前述意见上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审查,内部形成了两种不同意见。多数意见认为,涉案《销售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涉案仲裁条款中具有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和约定的仲裁事项,并选定了明确具体的仲裁机构,系有效的仲裁条款,合肥中院以国际商会仲裁院等国外仲裁机构不能在我国境内从事仲裁活动为由确认涉案仲裁条款无效是错误的,缺乏法律依据;少数意见赞同合肥中院的意见,认为仲裁在中国是需要经过行政机关特许才能提供的专业服务,中国政府并未向国外开放我国的仲裁市场,故国外仲裁机构依法不能在我国境内进行仲裁,因此涉案《销售合同》约定的由国际商会仲裁院进行仲裁的条款因违反仲裁法的规定,应属无效条款。
最高人民法院的答复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在给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复函中答复如下:
“本案为确认涉外仲裁协议效力案件。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因合同而发生的纠纷由国际商会仲裁院进行仲裁,同时还约定‘管辖地应为中国上海’(PLACE OF JURISDICTION SHALL BE SHANGHAI, CHINA)。从仲裁协议的上下文看,对其中‘管辖地应为中国上海’的表述应当理解为仲裁地在上海。本案中,当事人没有约定确认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的规定,应适用仲裁地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来确认仲裁协议的效力。
仲裁法第16条规定,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涉案仲裁协议有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约定了仲裁事项,并选定了明确具体的仲裁机构,应认定有效。同意你院关于仲裁协议有效的多数意见。”
简评
最高人民法院在上述“龙利得案”的答复中首次明确表示国际商会仲裁院是当事人选定的“明确具体的仲裁机构”,符合仲裁法第16条关于“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的规定,满足了中国法关于仲裁协议须选择机构仲裁的要求。这是一个有突破意义的标志性案例,它终结了此前一直存在的关于境外仲裁机构是否可被视作仲裁法第16条“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的争论,在司法实践中确认了当事人约定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的仲裁协议有效。
最高人民法院在此案中的答复也开阔了人们对于仲裁法第16条的审视角度。仲裁法第16条的主旨是希望当事人约定仲裁时选择进行机构仲裁而非临时仲裁,其中“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固然可以在狭义上理解为国内重新组建的仲裁委员会和已经存在的涉外仲裁委员会,但该条并没有明确排斥境外的仲裁委员会。最高法在答复中将仲裁法第16条“选定的仲裁委员会”从宽解释为“明确具体的仲裁机构”,是对仲裁法立法本意的补充阐释,是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法律规定的不明确之处拾遗补缺。由于当事人的仲裁意愿明确真实,法院对法律规定从宽解释以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也体现了法院支持仲裁的司法政策。
由于请示范围所限,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的答复中并不涉及国际商会仲裁院在上海仲裁后其作出的仲裁裁决属于什么性质的裁决(是外国裁决、非国内裁决还是中国裁决),以及在内地是否有执行的法律依据问题。这些问题,也只能留待后来在合适的个案中解决。
二、2020年6月的“大成产业案”
案情
2012年8月7日,大成产业气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大成株式会社”)和普莱克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莱克斯公司”)签署的《承购协议》第14.2条约定发生争议由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在上海仲裁。后大成株式会社、普莱克斯公司以及大成(广州)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成广州公司”)签署了《补充协议(一)》,大成株式会社将其在《承购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转让给大成广州公司。
2016年3月,大成株式会社、大成广州公司作为共同申请人向SIAC提出仲裁申请。在仲裁过程中,针对仲裁庭多数成员作出的仲裁地为新加坡的管辖权决定,当事人在新加坡高等法院和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兴讼,案件名称简称“BNA v BNB”。2017年8月30日,新加坡高等法院作出“BNA v BNB AND ANOTHER [2019] SGCA 84”判决,认为提交至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在上海仲裁应理解为仲裁地为新加坡,新加坡法律为仲裁协议适用法。2019年11月14日,新加坡最高院上诉庭作出“BNA v BNB & another [2019] SGHC 142”判决,认为“在上海进行仲裁”一词的自然含义就是将上海作为仲裁地。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只约定了唯一的地理位置,这应当解释为当事人对仲裁地作出了选择。因此“在上海仲裁”的文字含义即是指将上海约定为仲裁地。当事人对仲裁协议适用法律的默示选择是中国法律。但是上诉庭仅在上述的法律观点上推翻一审法院的裁决,而并未就仲裁庭是否拥有管辖权发表任何结论性意见,这意味着判定本案仲裁协议效力的管辖权落到仲裁地上海的中国法院之手。
上海一中院的裁定意见
2020年1月20日,两名申请人向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之诉。2020年6月29日,上海一中院作出《民事裁定书》,在确认仲裁地为上海、仲裁协议适用法为中国法的基础上,对本案仲裁协议效力作出了如下分析:
首先,外国仲裁机构在中国仲裁主要指外国仲裁机构适用其仲裁规则将仲裁地点设在我国的情况,由此进行的仲裁是机构仲裁,而非我国在纽约公约中声明予以保留的临时仲裁;其次,在“(2013)民四他字第13号”复函中,最高人民法院已经确认了涉外合同中约定发生争议由外国仲裁机构在国内仲裁如其约定符合仲裁法第16条的规定则为有效;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并未禁止外国仲裁机构管理仲裁地点在国内的仲裁;第四,对于具体案件,司法不能以立法不明为由拒绝裁判,尽管仲裁法在立法之初并不全面且与国际商事仲裁存在脱节,但立法与司法应系相辅相成关系,被申请人有关仲裁法在立法层面没有解决外国仲裁机构能否在中国进行仲裁的问题,并不能改变司法层面最高人民法院前述司法解释的有效意思。
综上所述,上海一中院认为应确认申请人大成产业气体株式会社、申请人大成(广州)气体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普莱克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之间依据《液态及气态产品承购协议》第14.2条、《液态及气态产品承购协议补充协议(一)》形成的仲裁协议有效,当事人为此发生争议,应提交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根据其仲裁规则在仲裁地中国上海仲裁。”
简评
中国加入纽约公约所作的“商事保留”和“互惠保留”并不包含对临时仲裁的保留,因此上海一中院的分析有其不准确之处。但除此之外,上海一中院在本裁定书中的分析值得称道,它体现了司法支持仲裁的政策导向,坚持了裁判规则前后承继有序、裁判标准统一的司法政策,并且具有顺应仲裁发展趋势的国际视野。对于外国仲裁机构能否管理仲裁地点在我国国内的仲裁这一问题,上海一中院观点鲜明,指出这个问题不涉及我国仲裁市场是否开放的问题,法律上无明文禁止规定,最高法在“龙利得案”的司法意见必须坚持,顺应国际潮流的做法应当允许。
上海一中院的裁定很好地呼应了“龙利得案”和新加坡最高法院在BNA v BNB案中的判决,再次向世人展示了中国法院支持当事人选择境外仲裁机构来华仲裁的积极态度。但由于本案的司法审查范围仅限于审查仲裁协议的效力,不涉及对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因此对于这类仲裁裁决的性质和执行依据问题,本案如同“龙利得案”一样,无法给出答案。
三、2020年8月的“布兰特伍德案”
案情
2010年4月13日,布兰特伍德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布兰特伍德公司”)与广东阀安龙机械成套设备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阀安龙公司”)、广州市正启贸易有限公司签订购买链板式刮泥机的合同,其中第16条“仲裁”约定:“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应提交国际商会仲裁委员会根据国际惯例在项目所在地进行仲裁。”根据合同约定,项目所在地为中国广州。
2011年5月9日,布兰特伍德公司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州中院”)申请确认案涉合同中的仲裁协议无效。广州中院于2012年2月22日作出(2011)穗中法仲异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确认案涉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有效。2012年8月31日,布兰特伍德公司向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提起仲裁。2014年3月17日,国际商会仲裁院独任仲裁员作出案件编号18929/CYK《终极裁决》。
2015年4月13日,布兰特伍德公司向广州中院申请承认并执行该裁决。布兰特伍德公司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意见,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可以在中国境内进行仲裁活动,约定由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在中国境内仲裁解决争议的仲裁条款合法有效。根据中国法院的司法实践,应当认定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作出的《终极裁决》是法国仲裁裁决,应按照纽约公约规定得到中国的承认与执行。如果法院认为案涉《终极裁决》是由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在我国香港的分支机构作出的,该裁决系香港仲裁裁决,也应根据《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的规定认可并执行该裁决。
阀安龙公司则认为案涉《终极裁决》不应得到承认与执行。首先,根据中国加入纽约公约时作出的互惠保留声明,由于案涉《终极裁决》系在中国广州作出,不属于“在另一缔约国领土内作出的仲裁裁决”,故应当排除适用纽约公约而被拒绝承认和执行;其次,根据中国加入纽约公约时所作的保留声明,中国并不允许外国仲裁机构在中国境内进行仲裁活动,而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并非中国仲裁法规定的仲裁机构,其在中国作出裁决,当事人无法申请由仲裁机构所在地的中国法院对其进行撤销审查,不仅剥夺了当事人的合法程序权益,也侵害了中国的司法主权;其三,尽管纽约公约在“领域标准”之外还规定了“非内国裁决(或非本国裁决)标准”,但目前中国立法对“非内国裁决(或非本国裁决)标准”没有明确规定,没有采取以仲裁程序准据法来确定仲裁裁决国籍的模式,故也不应以“非内国裁决(或非本国裁决)标准”适用纽约公约;最后,仲裁条款的效力与对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问题,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综上,尽管布兰特伍德公司主张案涉仲裁条款有效,不能当然得出案涉《终极裁决》应被承认和执行的结论。
广州中院的裁定意见
就布兰特伍德公司的申请,广州中院作出如下裁定意见:
首先,案涉合同的项目地点在中国广州市。广州中院于2012年2月22日作出的(2011)穗中法仲异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已确认上述仲裁条款有效。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根据布兰特伍德公司的申请,由独任仲裁员组成的仲裁庭在仲裁地中国广州作出案涉仲裁裁决。根据该事实,案涉仲裁裁决系外国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作出的仲裁裁决,可以视为中国涉外仲裁裁决。案涉仲裁裁决的被申请人不履行仲裁裁决的,布兰特伍德公司可参照民事诉讼法第273条的规定向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其次,布兰特伍德公司在本案中主张依据纽约公约或《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的规定申请承认及执行该仲裁裁决,其提起本案申请的法律依据显属错误,经多次释明后又拒不纠正,其应自行承担由此导致的相应法律后果。鉴此,本案不应作为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件,依法应予终结审查。本案终结审查后,布兰特伍德公司可依法另行提起执行申请。
简评
相较于“龙利得案”和“大成产业案”,本案在处理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问题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广州中院不仅在之前的民事裁定书中确认国际商会仲裁院在广州仲裁的仲裁协议有效,而且在仲裁裁决的执行阶段还进一步明确了这类裁决的国籍属性(籍属)和执行裁决的法律依据。
关于裁决的籍属,申请执行人布兰特伍德公司原本希望法院采取“仲裁机构所在地标准”,走捷径认定本案裁决为法国裁决或者香港裁决,因为本案仲裁机构总部或者受理案件的分支机构所在地分别为法国和香港。若如是,则本案裁决可以视为法国裁决或香港裁决,进而纽约公约或者内地和香港相互执行裁决安排得以适用。被申请执行人则提出本案裁决不属于纽约公约第1条第1款项下的“非内国裁决”。广州中院在本案中没有回避裁决的籍属问题。广州中院既没有按照“仲裁机构所在地标准”认定本案裁决为法国裁决或香港裁决,也没有认定本案裁决为“非内国裁决”,而是认为外国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作出的涉外性质的仲裁裁决,可以视为中国涉外仲裁裁决。广州中院的这一认定殊值称赞:首先,这是中国法院首次明确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作出裁决的性质,具有标杆意义;其次,摒弃“仲裁机构所在地标准”,以“仲裁地标准”确定仲裁裁决具有仲裁地所在国国籍,符合国际仲裁的主流观点,我国司法机关并未逆潮流行事或者置身于该潮流之外;第三,若将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作出的仲裁裁决视为“非内国裁决”,将有可能无法逾越我国加入纽约公约时所作出的“互惠保留”,于执行无助益;退而言之,即使不考虑“互惠保留”而依据纽约公约解决裁决的执行问题,纽约公约也会因其本身的局限不能解决裁决的其他司法监督问题(例如,如何确定对仲裁裁决行使撤销权的主管法院问题),因此“非内国裁决”的解决方案并不周延,容易顾此失彼。将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作出的仲裁裁决视为中国的仲裁裁决,除有执行方便外,还可以解决对该类裁决的撤销管辖问题。按照通例,仲裁地的法院对仲裁裁决的撤销有管辖权。
关于裁决的执行依据,广州中院也明确了,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作出的涉外仲裁裁决,可参照民事诉讼法第273条的规定向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民事诉讼法第273条(以及第274条)原本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裁决”,本案法院历经五年(从2015年4月13日立案至2020年8月6日作出本案裁定)提出此条文也可“参照”适用于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作出的涉外仲裁裁决,足见此一解决方案是我国法院审慎考虑后作出的务实选择,为以后同类案件的裁判和同类裁决的执行提供了明确的指引。按照本案的裁判理由进一步推理,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作出涉外仲裁裁决的撤销,将也有参照仲裁法第70条和民事诉讼法第274条进行司法监督的可能。
以上三个案例相互之间的时间跨度不到十年,其所取得的进步却意义非凡。它们都完成了同样的任务,就是面对仲裁法存在的缺漏和当事人愿意通过境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的现实需要,如何顺应国际仲裁的潮流,创造性地解决制定仲裁法时未曾明确的问题,让当事人切实感到中国是一个可信任、可预期的仲裁地。最高人民法院、安徽高院、上海一中院和广州中院在三个案例中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体现了人民法院支持仲裁、求真务实、填补缺漏、解决问题的态度。
从更加广阔的背景来看,人民法院积极支持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的态度与国务院关于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制度环境的工作总基调相吻合。2015年以来,国务院先后三次发文,就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特定地区开展业务活动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指导意见。
2015年4月8日,国务院在《进一步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中,提出要“进一步对接国际商事争议解决规则,优化自贸试验区仲裁规则,支持国际知名商事争议解决机构入驻,提高商事纠纷仲裁国际化程度。探索建立全国性的自贸试验区仲裁法律服务联盟和亚太仲裁机构交流合作机制,加快打造面向全球的亚太仲裁中心。”2019年8月7日,国务院《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进一步提出,“允许境外知名仲裁及争议解决机构经上海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登记并报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备案,在新片区内设立业务机构,就国际商事、海事、投资等领域发生的民商事争议开展仲裁业务,依法支持和保障中外当事人在仲裁前和仲裁中的财产保全、证据保全、行为保全等临时措施的申请和执行。”2020年8月28日,国务院《关于深化北京市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工作方案的批复》([2020]123号)“允许境外知名仲裁机构及争议解决机构经北京市司法行政部门登记并报司法部备案后,在北京市特定区域设立业务机构,就国际商事、投资等领域发生的民商事争议提供仲裁服务,依法支持和保障中外当事人在仲裁前和仲裁中的财产保全、证据保全、行为保全等临时措施的申请和执行。”
既然国家鼓励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设立业务机构提供仲裁服务,那么它们以内地为仲裁地受理仲裁案件、管理仲裁程序和依法作出仲裁裁决就是题中应有之义。相应地,中国法院能够执行该仲裁裁决也是合理的预期。可以想见,在外国法院看来,在中国领域内作出的仲裁裁决是中国的仲裁裁决。如果我们不认可这个现实,而是以“仲裁机构所在地不是中国”为由将此类裁决打上“外国仲裁裁决”的标签或者干脆以“没有法律依据”为由一推了之,则很容易造成认知混乱,也会让意欲在中国仲裁的当事人感到挫伤。
所幸的是,上述三个案例为解决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的相关的问题开启了绿色通道。“龙利得案”解决了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的仲裁协议效力问题,“大成产业案”明确了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不涉及仲裁市场开放问题,“布兰特伍德案”按照仲裁地标准为确定此类仲裁裁决的籍属和执行依据提供了指引。三个案例中,司法机关均本着有利于仲裁的政策去灵活地、而不是机械地理解和适用仲裁法。
当然,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在修订仲裁法时充分考虑司法实践所取得的经验,对标国际先进规则,确立处理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的一系列法律规则,营造法治化、可预期的仲裁环境,为使中国成为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而不断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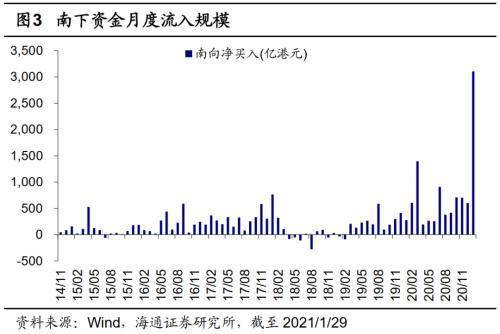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