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150年︱维舟:各地有各地的理解和记忆
今年是明治维新150周年、戊戌变法120周年,这两场变法维新运动的成败,可说决定性地影响了中日两国在近代的命运,其余波至今未息。很多国人所不知道的是,戊戌变法本身就曾深受明治维新的影响,曾著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等书的孔祥吉就明确说:“对晚清历史影响深远的百日维新,就其实质来说,是一场模仿明治维新的改革运动。”然而戊戌变法不仅比明治维新晚了三十年,并且还失败了,两国自此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或者倒不如这么说,中国变法自强是不足为怪的,因为近代试图由此摆脱殖民地命运并跻身列强的非西方国家几乎都失败了,唯一的例外就是日本。
对日本来说,在经历了太平洋战争的战败之后,明治时代的成功现代化也显得更熠熠生辉,比昭和时代更为正面积极,正如右翼作家司马辽太郎所形容的,那时的日本是“坂上之云”(顺着山坡向上爬升的云)。不过,去年、今年我两度踏足日本,从有限的见闻来看,日本人对明治维新的记忆还有着相当复杂多元的侧面,这其中不仅是对当时“开眼看世界”的欣喜,也有各地对明治维新的不同理解和记忆。
地方化的记忆
给人印象最深的一点是:日本各地对明治维新150周年的纪念活动明显热冷不均。去年春到日本,在广岛和北九州的小仓、门司都还没看到纪念明治维新的一丝痕迹,可是在山口县首府所在的山口市,已经提前一年挂出彩旗、贴出招募海报和筹备活动通知,开始大张旗鼓为明治维新150年做热身了,口号是相当自豪的“明治维新策源地”。这当然也不奇怪:山口县当年便是倒幕并主导明治维新最积极的长州藩,由此在日本政坛取得了长久的优势,虽然其人口仅占全国1%强,但出身于此的首相却是全日本第一(当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是),甚至还超过人口比它多十倍的东京都。
今年的状况也是如此:佐贺(原肥前藩)、鹿儿岛(原萨摩藩)对明治维新的纪念活动热火朝天,让人感觉那是这些地方历史上最为辉煌、也最值得记忆的一页,而在明治维新之后近百年来的历史反倒湮没无闻;四强藩中的土佐(今高知县)不在我的行程中,但想来也相差不远。在山口县的萩市博物馆内,甚至还有“平成萨长土肥联合”的标语,倡议这四县当下在这一议题上的合作。相比起来,其它地方对明治维新的纪念则冷淡得多:在我们一路经过的福冈县久留米市,都未看到值得一提的纪念活动。熊本县的八代、水俣、芦北、人吉等城市倒略涉及到了那段历史,但谈的却是西乡隆盛等人反对维新运动的西南战争遗迹。我的另一些朋友在冈山、高松、镰仓等地周游,也都没看到明治维新的纪念活动。

倒幕四强藩

萩市博物馆“平成萨长土肥联合”标语
至于去越后、青森、福岛等东北地方的,那就更是如此了,因为在那些地方的人们心目中,“明治维新”本身就是受难史。1868年1月3日,明治天皇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幕府,新政府军与幕府军爆发持续五个月的戊辰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东北奥羽越诸藩组成同盟支持幕府,在战败后被视为“朝敌”和“贼党”,在明治时代长期受到排挤、歧视,当地出身者在政坛的升迁、发迹均深受阻碍,当时甚至还有“白河以北一山百文”这一对东北地域的侮辱性称呼,意指当地人一文不值。这一记忆至今未能磨灭,因而在西南四强藩大张旗鼓纪念“明治维新150周年”之际,东北的新泻县、福岛县、宫城县等地则针锋相对纪念“戊辰战争150周年”,有些甚至提早一年就开始了——去年福岛县会津若松市就已在准备“戊辰战争150年 藩士慰灵”活动了。
对会津若松来说,明治维新带来的首先是“受难”与“恨”,他们记忆的是抗拒这一变革时的“勇气与不屈之魂”(勇気と不屈の魂)。会津藩的首代藩主松平正之是德川幕府二代将军秀总的庶子,对会津藩来说,德川将军家是祖先,是不能推翻的政权,正因此,它在戊辰战争中抗拒到底,在此地的战斗最为惨烈悲壮。战败之后,以长州藩为主的政府军禁止会津人收葬死者尸体,任其腐烂,甚至有人因埋葬死者而被收押入狱,藩士家族全部被流放到北部蛮荒之地青森。因而有一个说法:对会津若松人来说,“战争”让他们想到的并不是太平洋战争,而是戊辰战争。整场戊辰战争中,以会津战后对战败方的凌辱最为残忍,而另一支萨摩藩为主的政府军却在击败庄内藩后作出了宽大处理——尽管双方原也有旧怨,因为幕末时萨摩曾纠集浪人在江户挑起事端,试图由此获得倒幕的正当理由,当时幕府恼火之下便命令庄内藩等攻击萨摩藩邸。因而会津若松与鹿儿岛市已结为友好城市,但1986年原长州藩首府萩市认为“一百二十年都快过去了”,提议与会津若松和解时却遭到拒绝,会津若松人的答复是:“那另一个一百二十年还没过去。”
仅此大抵可见日本各地对明治维新记忆的纷繁复杂,那在很大程度上被地方化了,各地对此都有自己不同的记忆与理解——对东北的一些县市来说,甚至都不愿意提“明治维新”的字眼,会津若松市今年只在市博物馆做了戊辰战争的特展,没有“明治维新”。反过来,即便是在佐贺、鹿儿岛这样对明治维新引以为傲的地方,民众对那些纪念活动看来兴趣也不是很大,在佐贺的幕末维新博览会所吸引到的参观者远不如场外花火大会相关表演吸引的人多。更进一步说,在日本各地原本就有很多纪念物,作为地方特色来招揽游客,以至于对佐贺、鹿儿岛而言,明治维新的纪念在某种程度上只怕也是“地方特色”之一。
因此,这些纪念活动不仅是高度地方化的,甚至给人感觉是相当碎片化的,人们都是透过本地的“眼镜”来看待明治维新。例如:在鹿儿岛看到的明治维新人物,几乎全都是当地出身者(唯一的例外是曾和妻子一起来鹿儿岛旅行的坂本龙马),但凡提到明治维新时的革新进步之举,也都是就鹿儿岛本地而言;而到了佐贺又只谈本地在当年的风云人物与突出事迹,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虽号称“明治维新三杰”,但由于不是佐贺本地人,就根本看不到踪影。的确,佐贺的幕末维新馆在回顾历史时也会提到近代开国时长崎港所扮演的角色,但那恐怕是因为长崎在当时还是肥前藩的一部分,到后来才划出去成为长崎县。即便是当时的技术进步,也都大抵只谈本地的:佐贺讲自制的西式军舰凌风丸,到鹿儿岛看到的便是“日本最初洋式军舰”升平丸。

佐贺凌风丸
在这样一种自我形象认知中,“明治维新”常常变成各地将自己塑造成开放领先者的“加分项”。在山口县萩市的松阴神社内,有一块巨石,刻着“明治维新胎动之地”八字,显然自视为发祥地。佐贺县突出本地明治维新时的“七贤人”,将他们称作时代先驱的伟人,是现代国家的设计者(近代国家の設計士たち);并提出了一个口号:“当年佐贺放眼世界,如今佐贺展望未来”(その時、佐賀は世界を見ていた。そして今、佐賀は 未来を見ている),将明治维新的历史用在了激励当下。鹿儿岛市同样强调“放眼世界的萨摩”,并专门建造了一座“维新故乡馆”(維新ふるさと館),以突出鹿儿岛是“孕育出维新伟人的城市”(維新の偉人を生んだまち)。在鹿儿岛中央车站广场前,还树立着当年第一批出国留学的萨摩少年群像,显示鹿儿岛在当时领日本风气之先——但这背后真实的故事是:1865年的萨摩藩还存在着强烈的排外情绪,这批被派遣到英国学习的少年不得不使用假名秘密离国。

萩市“明治维新胎动之地”巨石

鹿儿岛明治维新150年纪念活动,其中0为萨摩岛津氏家纹
固然,在中国也会有对乡土历史的倾向,但这种“历史记忆地方化”的现象之所以在日本特别明显,当然也是因为在日本延续数百年的幕藩体制带有某种“联邦制”的特性,人们高度认同的是“本藩”而不是整个日本,战后的地方自治制度可说是它的历史延续。由于目光聚焦在地方,这些展览中即便提到明治维新对日本的意义,大体也是“我们曾在推动日本变革中起到巨大作用”这样一种视角。毫无疑问,这样的取向中不会提到明治维新对日本境外的影响——但这确实曾实实在在地影响了亚洲很多国家。不仅是戊戌变法,孙中山当年在日本避难时也曾说:“明治维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中国革命是明治维新的第二步。”《剑桥东南亚史》也曾提到,明治维新曾“鼓舞了大批东南亚的政治活动家,尤其是越南和菲律宾的政治活动家”。
说起来吊诡的是:明治维新的模式在当时之所以吸引东亚和东南亚诸多邻国的革命者,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其保守性——它借鉴西方经验保护本国传统,也就是说人们内心深处是“要现代化,但不要西化”。这种变革是在没有剧烈破坏传统的情况下实现的,研究日本近代史的学者Seymour Broadbridge甚至强调明治维新“现代部分的成功乃是由于立脚于传统部分之故”。按照中国的革命历史论述,这常会被看作是“不彻底的”,但其实倒不如说是好坏参半的:它既保证了传统与现代变革之间的连续性,避免了大规模破坏传统带来的异化,与此同时又使日本社会呈现出保守化的总体倾向。政治学者中村敏子曾说过:“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力求做到既效仿外国的社会制度,又不剧烈改变密切的人际关系。结果我们永久地拥有了这种双重社会结构。社会的外部结构是西方的,内部却是日本的。”
梅棹忠夫在其1986年所著的《何谓日本》一书中曾说:“讲到日本的近代化问题时,人们常常只强调明治维新的革命性一面,而我总是要强调它连续性的一面。”尽管这在学术上很能说得通(毕竟没有任何革新是像宇宙大爆炸那样凭空产生的),但公众看来还是对它变革的那一面印象更深。在公开的展出中,常常看到的一个叙事是:经历了锁国的日本,在长期酝酿之后,终于打破了昏沉沉的蒙昧状态,使整个国家面貌焕然一新。
这种角度很自然地不是强调明治时代与此前的共通性,而偏重近代生活如何不同。当然,这种“近代体验”的例子极多:明治时代首次开通了铁路(1872)、开放了面向民众的公园(上野动物园,1882)、建造了52米的高楼凌云塔并安装了日本首部电梯(1890),当下很多普及的事物在当时都是极为新鲜时髦的——1893年,外国进口的自行车价格相当于普通警官月薪的25倍。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在《明治维新生活史》中,对当时日本日常生活的种种变化都做了细致入微的叙述,这本身确实也是许多人所感兴趣的。长崎的明治维新150年纪念便偏重对“近代都市”新景象的描绘、当时近代工业的遗产,还将2018年的长崎与1868年的长崎作了对比,以突出长崎作为当时日本对外窗口、领风气之先的形象,以及现代化的成效;滋贺县长浜市在明治维新主题的展览中同样侧重城市生活的现代化——这也不意外,因为“近江商人”自战国时代以来便闻名全国,长浜一向商业气息浓厚,其城市建筑在日本也号称“西日本近代建筑万花筒”。因此,在这里,即便是明治时代生活的现代化,其实仍是与地方特色结合而推出的“主题策划”。
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些历史回顾中,大体上都将明治时代的现代化进程视为一件“好事”,在人们的记忆中无形中被美化了。尽管前些年经济不景气时,日本社会也曾弥漫着一种对江户时代的怀旧气氛,认为当时的日本和平安宁,还不必像黑船来航之后那样惊破太平梦,艰难革新,到世界上去讨生活;不过,在公开的展览中我的确不曾看到对明治维新的批判性反思。2015年“明治日本产业革命遗产”成功登录世界遗产名单,其中除了岩手、静冈的两处外,无一例外均位于九州和山口,主要都在倒幕强藩的辖境内。这对日本人来说意味着近代工业化的辉煌,然而其中有九处工矿设施都曾留下当年被强征的朝鲜劳工的血泪,尤其军舰岛曾有100名朝鲜劳工在此遇难,因而日本刚一申遗就遭到韩国政府的抨击。
对深受日本近代军国主义之害的东亚邻国来说,明治维新的意味很不一样:日本军国主义毫无疑问与明治时代的现代性无法脱离干系,其基础便是明治时代引入德国军事制度后奠定的,而一个对外扩张的日本也正是在此时逐渐成形的。和同时代的德国一样,日本的自强统一与对外军事胜利,产生了一个重要后果:让君主和传统统治阶层(在德国是容克地主,在日本则是武士)重获威望。如果说“在德国完成现代化的同时,现代社会中过时和经济上处于衰退的元素再次得以兴起”(《金与铁》),那么在日本也是如此。但有所不同的是,在1945年战败后,无论是东德还是西德,批判性的观点都成了社会主流,人们开始意识到正是1862-1871年间俾斯麦的胜利,或多或少地导致国家后来走向纳粹主义;然而在日本,明治维新的记忆没有指向军国主义,更未指向1945年的战败,倒仿佛是现代日本国家尚未被那些愚蠢的军国主义分子搞糟的美好童年。这或许是隐藏在看似纷繁多元的历史记忆背后的更深层记忆。
英雄,谁是英雄
在日本历史上,从黑船来航(1853)到明治维新(1868年起)的这段时间是一个风云时代,涌现出了许许多多个性鲜明、引领时代的英雄人物,这一点大概只有应仁之乱后的战国时代(1467-1585)差堪比拟。很多人在想到明治维新时,首先想到的恐怕也是这些人,他们是维新政治的道成肉身。
这些人的共同特点之一,是都很年轻:培养了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倒幕维新领导人、鼓吹“皇国史观”的吉田松阴,在被囚去世时年仅29岁;创设奇兵队的高杉晋作在明治维新前夜去世,不过28岁,比他晚半年去世的坂本龙马时年31岁;1868年明治维新正式开始,此时岩仓具视43岁、西乡隆盛40岁、大久保利通38岁、木户孝允35岁、板垣退助31岁、大隈重信/山县有朋均为30岁、伊藤博文27岁,第一个在欧美获得学位的日本人新岛襄才25岁。相比起暮气沉沉的大清帝国,当时日本的政治精英是一个相当朝气蓬勃的群体。

萩市松阴神社
这些人的另一个特质,是大多出身低微。除了大隈重信、板垣退助家的地位略高外,坂本龙马出身于土佐寒微乡士家庭,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都来自小姓与(koshō gumi)家庭,属于萨摩藩中级武士的最低一级,按幕府的政治体制,他们根本连与天皇直接交谈的资格都没有,岩仓具视虽是公卿,但在朝廷正式会议中也没有发言身份。长州藩也一样:自天保改革(1841年)之后的长州各派领袖都是收入低微的平侍:村田清风,91石;周布政之助,68石;坪井九右卫门,100石;椋梨藤太,46石。长州藩在明治维新中占据核心地位,跻身明治政府的要人中有很多人曾在吉田松阴的松下村塾中学习过,而松阴当时的一个重要理念便是“草莽崛起”,寄望来自底层的志士起来改变腐败的幕府与诸侯,建立新日本。
他们在政治上确实成功了,但是否受到后人喜爱,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伊藤博文作为明治九元老之一,曾四次组阁,不过他的故居颇为冷清,也很少看到他的形象在山口县的公共场所出现。相比起来,在明治维新前夜遇刺身亡的坂本龙马,却是日本无数书籍、动漫、影视剧乃至游戏中的超级英雄,在前些年还曾被选为日本历史上最受欢迎的人物,在“明治维新十二人组”啤酒中以他名字命名的也是最畅销的一种。这未必是他本身做出了多大业绩(他死后明治政府追赠正四位,并不算高,而西乡隆盛是正三位,大久保利通正二位),倒不如说是人们对他的形象更为偏爱。

坂本龙马
从真实的历史来看,坂本龙马的推动作用也确实有限。日本历史学家小岛毅便曾指出,即便在他去世之后的“明治维新之初,坂本龙马并不那么著名。虽然他促成了萨长同盟,应该功劳不小,但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或木户孝允皆未曾称许他的功绩。即使是他的老师胜海舟,也没有在回忆录中特别提到他。土佐藩中认识他,并且日后成为明治政府要员的人,也不太关心坂本龙马的事迹”。但这些都并不妨碍他成为日本人特别喜爱的历史人物,因为他们并不完全是根据其功过来评判历史人物,而是他的“个性”与“精神”。正如William G. Beasley在《明治维新》一书说到当时这些维新志士时所说的:“事实上,他们做出这样的决定,与其说是出于对激进政治的献身精神,倒不如说是由于年轻人的血气方刚:一种冒险的意识,一份迫不及待的冲动,一股为追求更高理想而抛弃传统道德的愿望。坂本龙马就具有所有这些品质。”
其他人物的身后之名也是如此。近些年来的一个新变化是:那些原先在明治维新中被认为所起作用不那么大的贵族上层,开始回到人们的视野中心。在山口县博物馆,幕末长州藩主毛利敬亲在群像中位居最高处;在佐贺的幕末维新博览会,当时肥前藩主锅岛直正的形象居于中心,而他的雕像也已在本丸历史馆外高高树立起来,从四周浮雕的内容看,俨然当时诸如反射炉、海军制造所、种痘等新技术都是在他主导下引进的。在鹿儿岛,三代藩主岛津氏均备受推崇,甚至十三代幕府将军正妻天璋院笃姬也进入了公共视野,其卡通形象四处可见,2010年她的雕像在黎明馆外落成,以表彰她在明治维新时让江户和平开城、在戊辰战争中为德川家族存续所作的贡献。

佐贺本丸城博物馆内肥前藩大炮制造所绘图
这恐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2008年宫崎葵主演的50集NHK大河剧《笃姬》的成功,这片极大地提升了天璋院笃姬在公众中的知名度,让人们对这位出身萨摩藩主岛津家族的公主兼幕府将军夫人大感兴趣。这也迎合了这些年来人们对当时贵族生活的兴趣,在佐贺关于明治维新的展览中,其中一项便是藩主锅岛氏侯爵家的用品及藏品展。与此同时,这些贵族在当时抵触明治维新的一面则被悄悄略过,例如萨摩藩主岛津久光虽曾参与推动维新变法,但在1871年废藩置县触及他自身利益时其实极为愤怒,久久不能饶恕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
明治维新能成功实施,大久保利通所做出的贡献恐怕比西乡隆盛大得多,西乡后来还站在不满维新政府的旧武士一边发动叛乱,思想也颇有反对现代化的保守一面(他一度认为政府建设铁路是浪费,敦促用于强化军事);然而在鹿儿岛市内,西乡隆盛这个“最后的武士”的人气明显是压倒性的,以他为名的大河剧《西乡殿》正在热播,在城山展望台下的纪念品商店里,几乎全是他的画像和纪念品,看不到别人。土居健郎在《日本人的心理结构》中认为:“日本人都非常同情像义经、楠正成、四十七义士、西乡隆盛这些失败的英雄,它反映了日本人在道德观念上有一种受虐狂意识。”这或许不无道理,但另一点也不可忽视:尽管大久保利通也鞠躬尽瘁地推进维新变法,但他的形象远不如西乡隆盛那么具有亲和力。大久保利通的雕像是一个看上去慷慨激昂的形象,而西乡隆盛的典型形象却正如东京上野公园入口处的铜像所示的,他穿着宽松的和服、木屐,牵着自己那条小狗次寅。在鹿儿岛市内,看到西乡隆盛的格言“敬天爱人”的概率可比大久保利通的座右铭“为政清明”高得多,后者一看就是让人颇有距离感的做派。
西乡隆盛在鹿儿岛的受欢迎程度异乎寻常,几乎可说是当地的代言人。日本人不仅为他建造了西乡南洲显彰馆(1977年西乡隆盛百年祭时建造),甚至还有专门的神社,这意味着他死后已经成神。这也不是近些年才如此,1942年的日本电影《南风·续》中就有这样的桥段:日本人加世田在新加坡认识了当地人辛·齐普,信奉红大教,其教祖竟是西乡隆盛与柬埔寨女人的私生子,据传西乡并未战死,而是逃到南洋创立了该教。奇妙的是,其圣堂与基督教教堂相似,圆内嵌十字的萨摩纹教徽也类似十字架,但挂在祭坛上方的圣画不是耶稣而是西乡隆盛。今年鹿儿岛的旅游手册,甚至还有一个特典“西郷どん”专门规划西乡隆盛在日本所有遗迹的行程路线,以满足那些特别崇拜他的游客需求。

西乡隆盛
中国和韩国游客对他的感受可能复杂得多,不仅因为西乡隆盛强烈主张对外扩张,也因为西乡隆盛的西南战争本身就旨在发动“二次维新”,这正是后来从三岛由纪夫到“平成维新”的日本右翼一直在使用的宣传口号。事实上,荒原朴水在《大右翼史》中就曾说:“人说右翼的源流始于西乡南洲。”对此,小岛毅也分析过日本人的心理:“在当下的舆论中,西乡与板垣被认为是站在人民这边,被视为英雄;岩仓和大久保则被认为站在体制那边,变成了令人厌恶的压迫者。但是别忘了,前者才是积极推动‘征韩论’这一侵略政策的人。其实,岩仓与大久保也没有要与朝鲜国永远保持对等的友好关系的想法,他们之所以反对‘征韩论’,只是认为当时日本不宜发动军事行动罢了。”也就是说,日本人对这些人物的评价更多是感性的,看重的是他们是否具有亲和力、是否站在民众一边,但对其政策利弊则放到一边。
当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在西方的民主政治中也常常如此,尤其是电视时代的选举,选民们常常下意识中与其说是“投票给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倒不如说是“投票给我喜欢的候选人”。但日本人的心理特点在于:他们有时还确实更喜欢那些失败的英雄、壮志未酬的人物。根据藤泽周平小说改编的电影《黄昏清兵卫》(2002)、《隐剑鬼爪》(2004)中,人物生活背景均被设置在幕末时代的海坂藩(现实中的庄内藩,即今山形县鹤冈市),属于明治维新中的失败方,黄昏清兵卫最终便在戊辰战争中死于新政府军的炮火。这些虽是虚构的故事,但它们的大红则显然是因为微妙地契合了观众的心理。历史从来就不仅仅是历史,这些长久活在人们心目中的历史人物,倒不如说一面镜子,折射出群体在不同时代的心理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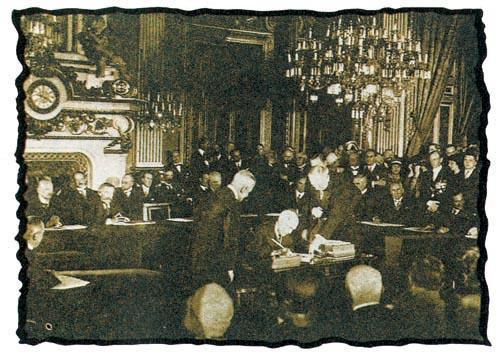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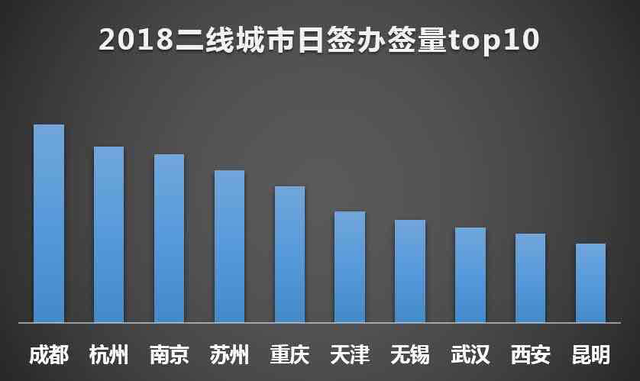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