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佣在中国:富豪趋之若鹜,黑市不择手段
新加坡眼按:在新加坡每6户家庭中就有一户雇请女佣,每月花五六百新币(约合人民币不到三千左右)请女佣帮忙做事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而在中国,找菲佣不仅贵,而且困难重重……

图/郭浩忠
Marry Car Traifclgar Lieses,48岁,她30岁的时侯从菲律宾到香港做家佣,然后每次一签两年约,约满了便回国探望家人一个月,所以这十七年来她只是回国七次。对比一般香港菲佣来说,她算是年龄比较高才来香港的。她家中有3个儿子,都在读大学,家庭全靠Mary在香港挣的钱来养活

一位菲佣在女佣中介里练习使用筷子(图/郭浩忠)
时间上,安娜应该已经到了深圳,但她居然人间蒸发了,卢云霞对此毫无心理准备。仅仅一天之前,她把这名菲佣亲自送到火车站,备足了路上的食品饮料,如以往一样关切之至。
24小时,48小时,安娜的手机一直是关闭状态,卢云霞想起当初中介的叮嘱:千万不要把菲佣的护照交到本人手里,她们完全不讲情义,随时可能跑路。但她还是轻易地就把护照还给了她。她以为全家人对安娜那么好,不会发生背叛之事。现在,她的轻率付出了真金白银的代价,安娜失踪,意味着卢云霞夫妇要蒙受接近10万元的损失。当然,对于男主人是外企高管的这个家庭而言,经济损失倒不难承受,而最大的困境在于,接下来做何选择——还敢到“黑市”雇佣菲佣吗?如果改用本土保姆,又如何适应巨大的落差?
大陆的诱惑
笔者在澳门对菲佣交易进行暗访时,和安娜有过半天的接触。当时安娜逃到深圳去了新雇主家后,新雇主通过倒卖签证的魏国,将她和其他菲佣一起,带到澳门来办理签证。
安娜逃跑时的借口是,她在中国待了多年的朋友,能办到更便宜的签证。这样就可以为主人卢云霞节省一些开销。眼看安娜半年的签证即将到期,女主人卢云霞不希望这个菲佣“黑”在自己家。卢云霞给安娜一个合法的身份,是对她的最大尊重。
4月的一个晚上,在中介的安排下,卢云霞与丈夫面试了安娜,他们是若干面试雇主中的最后一拨。
在中国大陆,菲佣像隐形人一样生活着,事实上,围绕她们已形成可观的供求市场。一位在北京从事菲佣中介(他们大多都有家政公司的幌子)的人士说,他根据行业内的一些信息估算了一下,在北京打工的菲佣,应该超过了10万。
大约2005年前后,一些高收入外籍人士来华工作的时候,习惯性地把自己的菲佣也带了进来,渐渐地,大陆的富裕阶层也对菲佣的高标准的服务有所耳闻,一个地下市场开始发育,并始终与官方的监管进行着猫鼠游戏,甚至存在着某种默契。
那次面试快结束的时候,借着中介公司工作人员如厕的机会,安娜拉住了卢云霞的手,急切地表达了马上被雇佣的意愿,并发誓自己的工作会让主人非常满意。
原本,双方是可以第二天再做决定的,男主人对安娜的资料比较满意,交了合计5万多元的所谓签证费、中介费,当晚就把安娜带回了家。
安娜今年32岁了,又矮又胖,其貌不扬,但资历确实很适合这个中国雇主。还是十几岁的小姑娘时,安娜就开始在新加坡做佣人。她聪明伶俐,很会看主人的脸色行事,加上出国前和到新加坡后都接受了比较专业的培训,她成为了非常出色的菲佣,很受雇主欢迎。在台湾工作3年的经历,让安娜学会了中国话,并烧得一手好中国菜,这为她赢得了在大陆就业的充裕资本。人还没到,很多看了简历的雇主就在家政人员那里展开对安娜的争抢。家政公司借机加价,将她的中介费瞬间提高了50%以上。
安娜听说,中国大陆的工资比新加坡、香港和台湾都高,为了赚更多的钱,明知道不合法,她还是毅然和小姨等人一起来到中国大陆。
那是一个漆黑的晚上,“蛇头”和中介公司的人为了省钱,让她们坐上了陈旧狭小的一班夜航飞机,机上不提供免费食物和饮水,身无分文的她们一路忍饥挨饿到了澳门,随后转道深圳,坐了几十个小时的火车抵达北京。安娜说,一路上她就喝了一瓶水,吃了两个包子,熬过了有些凄楚的旅程,不过,她心中也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
据安娜事后回忆,见到卢云霞一家人之后,她立即动了心,觉得这对年轻夫妇举止文雅,有教养,而且家庭状况很简单——只有一个3岁的小女孩——这让安娜很动心。
5个月的“蜜月”
在北京的生活开始了,男女主人对佣人彬彬有理,家里的食物和用具,全权由安娜负责,她工作得特别开心。
按照多年的工作习惯,她每天5点半就起了床,将一二楼的房间和庭院全部打扫干净,在8点之前做好早餐摆放在餐桌上,然后去照料3岁的小主人穿衣服、洗漱、吃饭。可爱的小主人无形中缓解了安娜对孩子的思念,因此她照顾得格外细心,孩子也特别喜欢她。
8点半,小主人准备去幼儿园,安娜为她穿上准备好的衣服和鞋子,书包里早已放好装满温水的水壶,干纸巾和湿纸巾也各放了一包。在男女主人出门前,鞋子早已擦亮,安静地摆放在门口,她还能根据女主人当天要穿的衣服,将相应的鞋子和丝巾也搭配好,女主人总会在这个时候给她一个拥抱。
将孩子送走后,安娜继续自己的清洁工作。她把别墅擦拭得窗明几净,沙发和地毯(包括柜子下面)每个星期都要清理一遍,衣柜也要定期整理。下午的空闲时间,除了打扫花园,便是熨烫衣服。这是安娜的一天,也是接受过标准化服务培训的中国菲佣的一天。
按照安娜透露的线索,笔者在北京找到了卢云霞。安娜曾经的主人住在北四环的一个高档社区里,房子是独栋别墅,面积很大,身为作家的女主人很有生活品味,几乎把每个角落都布置得别有情趣。房间内整洁温馨,花园里鲜花盛开。
在卢云霞看来,安娜是见过世面的人,在面对女主人那些昂贵衣服的时候,什么品牌、什么材质的衣服怎么洗烫,她都非常清楚,处理得体,这让最初有些嫌弃其容貌的女主人越来越喜欢她。像多数菲佣一样,安娜时刻注意摆正自己的位置,家务方面从未让卢云霞操过一点儿心,主人偶尔指出的差错,她会立即纠正,绝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安娜的尽职与专业并非特例,总体而言,菲佣确实是高素质、高标准的保姆群体,甚至可以说,菲佣是世界上最出色的保姆,代表着行业的标杆。
深圳一家菲佣中介的王先生说:主人交待过的事情,菲佣绝对不会忘记;规定的工作范畴,她们也会严格遵守,绝对不会像有些中国阿姨一样,规定干的活,今天高兴就干,明天不高兴了就不干,菲佣会始终如一。因为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她们素质相对较高,责任感很强,喜怒皆能做到含而不露。
她们安静、随和、谦恭,出国前大多经过精心的挑选和培训,大到能以接近医护人员的水准护理孩子和老人,小到熟练掌握各种材质的衣服的洗烫,更职业一些的菲佣,会根据女主人当天所穿衣服的颜色,搭配好相应的鞋子和丝巾。最重要的是,她们兢兢业业地恪守职业规范,服从是她们的天职。
女主人对工作出色的安娜超乎寻常地善待,刚替换下的手机,会送给她使用,还会把自己的许多衣服慷慨地送给她。安娜又矮又胖,很多衣服都穿不了,卢云霞便给她买新装,从头买到脚。每次出差回来,更不忘给她买个礼物。
“中国的雇主很多时候喜欢把保姆当成自己的家人,但我们很清楚,我们和他们只是工作关系,我其实不过是在工作而已,在哪里都是这样工作的。”安娜曾这样对我说。
正是因为这种文化差异,从未对主人一家投入任何感情的安娜,在北京的天气突然变冷的日子里,开始变得焦躁,在热带国家长大的她,对北京未知的冬天充满了恐惧。9月初一个微雨的早晨,对中国北方人来讲很舒适的天气,不冷不热,安娜已经开始浑身发抖了。几天后,当她的手上因为干裂出现了第一道血口子时,她烦躁不安地给她在深圳的朋友打了电话。
在外工作的菲佣很抱团,情感上相互取暖,她们没事就会打一通电话,彼此说说雇主及家庭的情况,有了烦恼更是一吐为快。她们可以省吃俭用,但在电话费上从不吝惜,这份“感情投资”甚至会占到薪水的五分之一。按她们的话讲,这是保证她们不疯掉的唯一的情绪出口。很多菲佣,为了多挣点加班费,全年都不休息,其压力可想而知,而雇主为了避免她们出去惹麻烦,也愿意多出几百块钱、息事宁人。
安娜本来是为了倾诉的一个电话,却从此改变了她的命运。朋友茱莉已经在深圳的雇主家待了5年,作为一个精明的“中国通”,她坚定地告诉安娜,北京的气候不适合她,冬天特别冷,会下很厚的雪。来中国不久的安娜当时还不知道,茱莉极力鼓动自己去深圳找个雇主,是有利益驱使的。菲佣资源短缺,有赚取暴利的空间,黑中介之间进行着不正当竞争,他们鼓励自己的菲佣,拉一个人回来给1000-2000元的提成。茱莉通过自己所属的公司,在深圳给安娜又找了个雇主,同意工资多给200元,每月5200元。
安娜虽然留恋北京的工作,但还是禁不住茱莉的鼓动,她要想办法把护照搞到手。聪明的她,在主人面前表现得更加尽心尽力。
半个月后,半年的签证快到期了,卢云霞张罗着联系倒卖签证的人,以便花高价为安娜“买”回后半年的签证——在大陆,为非法务工的外国人提供相关“服务”的地下产业链早已形成。
安娜终于等来了机会,她对卢云霞说,她的朋友可以帮忙办签证,也是出关去澳门,但可以省一半的钱,半年的签证一万多元就能搞定。
安娜并未在工作中表现出任何异常,卢云霞从未想过这个温顺的菲佣会不辞而别,于是毫无戒备地把护照交给了对方。
回不去的中国
中介公司的人用一辆破旧的面包车,载着笔者和十几个前来办签证的菲佣,七扭八拐地来到了澳门很偏僻的一条无名小巷里。这里路边都是廉价破旧的出租房,一个席子就是一个地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中介公司的人,将签证快到期的菲佣,从蛇口海关带出境,在这里住上一个星期,等新的签证办好了,再重新入境回到内地各个城市的雇主家去。
据出租屋的老板介绍,从去年初开始,生意就不怎么好了,因为签证越来越难办了,很多原来做倒卖签证生意的人,都不干了,加上鉴证费越来越高,很多菲佣雇主都不愿意折腾了,不办签证,菲佣的工资因此提高了很多,而雇主也乐意用钱买个平安顺利。所以来这里住的菲佣也就寥寥无几了。早些年的时候,这里的房子几乎供不应求。
在澳门中心街湿热的街头,安娜惊诧地获知,自己被中国大陆拒签了,她无法理解,为什么同行的人都过关了,自己却这么“倒霉”。原来,受到欺骗的卢云霞愤怒至极,通过相关部门朋友的帮助,“封杀”了安娜在大陆重获签证的可能。
安娜强忍着泪,从签证贩子魏国手里接过被拒签的护照,她用力甩甩手,发泄着对主人的怨恨,但她的怨恨无论多强烈,都显得苍白无力。
她坐在地上,憋着不哭,黝黑的面孔涨成了紫色。其他十几个一起来澳门的菲佣都顺利办好了签证,她们试图过来安慰一下,安娜有些不耐烦地说:你们过关吧,我想静静。
魏国随口骂道:“让你不安分,让你跑!现在他妈的被列入黑名单了,必须滚回菲律宾去了吧?给自己惹麻烦也给老子惹麻烦。”然后他又转头看着我说,“她的雇主对她很好,结果她为了多拿两百块钱就从雇主家跑了,菲佣特别无情,相信她们,就是相信猪能上树。”
矮小、清瘦的魏国有强势的一面,他通过非法途径为菲佣办理签证的能力,大大超出其他人,因此说话时喜欢嗓门高八度,以抬高自己的身价。他频繁地眨动眼睛,一副精明的样子。早年,这个土生土长的广东农民偷渡到香港打工,后来居然得以入籍香港。有了香港身份的他摇身一变,不但回深圳娶了个三陪小姐做老婆,还大摇大摆地做起了倒卖签证的生意,仅两年时间,就在深圳买了一套三居室,这也是他时不时拿出来显摆的资本。
外界疯传魏国的“关系”极广。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与全国各地的家政公司开展“合作”,总是能将大批的菲佣带到澳门,让她们在澳门小街上的出租屋里,打地铺住上一个星期,然后顺利地办好商务签证,再带进大陆。同时他还负责给非法来中国居住或做生意的非洲黑人办理签证,因此若谁惹他不高兴了,他不但会暴跳如雷,还会威胁说:“我找几个黑人弄死你、或奸了你!”狐假虎威这招,他做得极其到位,因此很多不明就里的人也很惧怕他。
通常,魏国一个签证对外收费8500元(另一个张姓的办签证的男子告诉笔者,现在办一个半年期的商务签证,至少要16000元了,不包括家政公司的加价),至于家政公司如何加价,向雇主怎么收费,他就不管了。在倒卖签证的“生意人”里,据说魏国是做得最好的,因此,在澳门街头那家麦当劳餐厅里(菲佣和中介公司们,一般都是在这里把护照交给魏国),他总是大声地吆喝:“收签证了!”一边喊一边骂骂咧咧,否则似乎不足以表明他的能量。
魏国也不讳言,这钱也不是全部进了他的腰包,要分给那些负责出入境管理的人,“那些警察黑着呢。”在笔者发稿前,魏国突然失去了联系,知情人说他被人举报,跑回了香港。
在麦当劳门口,比安娜还小一岁的小姨阿雅跑过来,抱着安娜大哭起来。这一对亲戚一起从菲律宾千辛万苦地来到中国,精神上和生活上互相依靠,现在安娜被拒绝入关,想到自己一个人在中国的孤单,阿雅似乎比安娜还要伤心。
“别哭了,赶紧过关。”当魏国像赶鸭子一样,将十多个菲佣赶向关口,安娜的惶恐这时爆发了,矮小的她甩掉脚上的拖鞋,像一只羚羊一样,迅速地窜过去,抓住了魏国的胳膊:“求你了,我家里有两个孩子要抚养,别让我回去,我刚出来半年还没挣到什么钱。”
她终于失声痛哭起来。魏国厌恶地甩开她的手:“神经病,他妈的前几天你的夫人还求你回去,你就是不回,活该,你要回她家吗?”安娜突然静下来,冷冷地说:“不回!”
“你就是狗。”魏国骂了一句转身就走。
二十多天以前,安娜在深圳投靠了新雇主,月薪比在北京高出200元。不过,因为她要去澳门办理新签证,新雇主告诉她,等回来之后再发工钱。被拒关外,意味着安娜连那二十多天的工钱也没拿到,现在她被列入黑名单,不得不返回菲律宾。32岁的她原本打算在中国至少再干5年,现在一切都泡了汤,在电话里,家中那个全职做家务的丈夫狠狠地骂了她一顿。
安娜从包里拿出了一本手掌大的相册,里面有她男女主人的结婚照,她看了一下,随手扔进了垃圾桶。隐隐地,她能感觉到,暗中有一只手阻挡了自己继续在中国大陆谋生,嘴上说着“我恨她们”,但懊丧的眼神表明,她心底更恨的是自己,为什么轻易就听信了“朋友”的蛊惑。
离不开的菲佣
尽管离安娜逃走已经两个多月了,但卢云霞提起此事,仍伤心不已。因为房子很大,孩子很小,需要操持的家务特别多。没有父母帮忙,她非常需要一个得力的佣人。卢云霞家里也用过本土保姆,但她把那些的日子看作噩梦——中国保姆懒散、邋遢、无知,稍微不满,她还没说什么,她们就开始撒泼打滚闹辞职了。工作没做好,少给一分钱,她们就在小区门口大哭、大骂,为了怕在邻居面前丢脸,她总是选择妥协,直到最后从心底惧怕她们,保姆也似乎每个人都敢顶撞她,和她吵架。
这样的日子,除了痛苦便是焦躁,她一直使用这样的评价语汇。有的保姆进门后连基本家用电器都不会用,更不用说专业的洗烫等工作了,而安娜带来的,是作为菲佣的标准化服务,让主人备感舒服。
在失去这个安娜的日子里,女儿终日愁眉不展,甚至哭着到处找安娜阿姨。安娜的“冷酷”离去,也让卢云霞心痛得一个星期没睡好。
卢云霞曾费了很大力气,通过社会关系找到直接的中介人,极力劝说安娜回来,并表示可以追加工资。但是,安娜表现出了极度的决绝,无论如何也不肯回去。
“菲佣是很无情的,她们把这就当一份工作,在雇主家,她们绝对听话、温和,一旦离开,不管雇主对她们多好,绝不留恋。”做了十几年菲佣家政的朱先生不满地表示:“菲佣如果有真话和真情,石头都化了。”
朱先生的评判体现了文化差异,与笔者交流时,身为菲佣的吉娜觉得,“不近人情”再正常不过:“我们和雇主就是一种雇佣关系,这种关系,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这是阶级矛盾。我们付出了劳动,换取了她们的钱,感情为什么还要给她们?没有人会喜欢一个整天对你指手画脚的雇主。哪怕她是温和的,但实际上也是盛气凌人的、高高在上的。”
无论如何,她们的职业素养和敬业精神,为她们赢得了掌声和美誉,同时也赢得了中国雇主发自内心的爱。一旦失去,雇主们难免无所适从。
在深圳生活的菲佣雇主王先生告诉笔者:家里房子大,且有两个孩子,以前她们家雇了3个中国阿姨,一个做饭、一个打扫卫生、一个看孩子。即使这样,家务还是搞得一团糟,交代的事务,有时要反复提醒,吃饭的时候,阿姨们也不分主次。此外,阿姨的脾气还不小,批评不得,一不高兴抬腿就走,这导致家里三天两头换阿姨。按他的说法,雇主每天都得给她们陪着笑脸。后来他找了菲佣,一个菲佣干3个人的活,居然还井井有条,最主要的是,感觉自己真像个主人了,出门回来有人打招呼、倒水,走的时候有人送,对主人习性了解之后,菲佣还会帮着准备出差的行李,“这些都不用说,人家就干了,不满意说几句,立即就改,绝不顶嘴,哪像中国阿姨,遇到泼妇型的,敢和主人对着吵。”王先生甚至表示,用过菲佣之后,中国阿姨白给用他都不用。
北京的赵女士也有同感,她家换过十几个中国保姆,都不满意,万般无奈之下终于找了个菲佣。“中国阿姨大多来自农村,没什么文化,因此个性也很偏执。她们不懂得尊重人,更摆不正自己的位置。说句不好听的,中国阿姨带孩子,孩子会从她们身上学到很多恶习。”她大发感慨,“用菲佣,你会觉得自己有了帮手,甚至有了管家。可以放心地把家交给她,她们比很多女主人都会打理家。菲佣大多受过至少中专以上的教育,她们有素养,懂英语,对教育孩子也是个很好的帮助。她们有服务意识,从不和雇主一起吃饭。分内的工作,你不用刻意去交代,每天该做的工作无论做到多晚、都会完成,不需要你监督。”
在中国大陆,家政公司大多缺乏规范化管理。一个刚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保姆,家政公司就可以随便推介给雇主,赚取中介费之后万事大吉,任由雇主和阿姨费劲地磨合,一旦保姆很快辞职,家政公司乐得为她们再找一个新雇主,又是一笔中介费。难怪中国的雇主们普遍抱怨,他们买不到满意的服务,倒觉得自己的家成了培训机构。而且,在快速发展的中国城市,保姆市场严重的供不应求,也使保姆们如同不愁嫁的皇帝女儿,自然不思进取。
菲佣确实体现着“训练有素”的价值,这种价值在大陆市场,经过比较而越发彰显。菲佣们出国前都经过精挑细选,受过至少3个月的专业培训。她们喜欢学习和接受新事物,初来中国的菲佣,得到一本英语版的中国菜谱后,很快就能将中国菜做得有滋有味。对于那些如卢云霞一样见识过菲佣的高素质服务的人们而言,被迫重新适应本土保姆注定是痛苦的。
不过,地下交易市场变得越来越扭曲、越来越无序,假如继续选择菲佣,雇主们要承担的风险、要付出的代价也越来越大。
“只能认了”
按目前的市场行情,一个菲佣的中介费在人民币18000至20000元之间。雇主通过家政公司提供的资料(有时还要网络视频面试),觉得满意了,立即付给家政公司10000元左右的定金;等到菲佣到岗,雇主不仅要把全部中介费付清,还要支付商务或旅游签证的签证费,其中半年期的费用为人民币18000至24000元,一年期的签证费需要28000元。同时,雇主要一次付清菲佣6至8个月的工资(一般月工资在5000至6000元之间)。
在不透明的市场里,黑中介搞出许多霸王规则,比如菲佣在国内转运的交通、食宿成本,他们一方面要求雇主承担,一方面又蒙骗菲佣,在她们的工资中扣除远远超过实际成本的款项。因为都是有求于黑中介,无论雇主还是菲佣,即使明知道被盘剥和欺诈,一般也只好忍气吞声。
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香港等地不同,在中国大陆的菲佣无需经过培训即可“上岗”,即使这样,大陆的中介机构也会扣除菲佣6至8个月的工资,直接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在大陆,因为客户都是高收入群体,加之供不应求,黑中介们习惯于狮子大开口。菲佣通关的所谓过关费只需几十元,他们敢向雇主要价几千元,由于都是地下交易,雇主无可奈何。
把一个菲佣请回家,在一天都没工作的情况下,雇主至少要一次性掏出6-10万元。有一些家政公司胃口更大,实行了所谓的年薪制,即一个类似安娜那样成熟、有经验的菲佣,要求雇主支付年薪30-60万,他们从中可以坐收更丰厚的利益。
前不久,深圳某家政公司为一个菲佣“标价”60万元,如此昂贵的一个原因是,她曾在台湾知名主持人胡瓜家里工作两年,算是“贴金”了。很快,深圳一位富豪支付了这笔高额年薪,但事实上,菲佣只是从家政公司拿到每月最多6000元的工资,其余款项都被家政公司占有。那家家政公司的员工事后感叹,中国大陆的“土豪”真是出手阔绰啊。
由于竞争日益激烈,又没有最起码的监管可言,黑中介不择手段地去挖人、抢人,类似安娜那样的跑路现象多起来。为了避免菲佣跑路给自己带来麻烦,家政公司巴结她们还嫌来不及,管理条例于是形同虚设。摸清了中国家政公司和雇主的弱点,菲佣们也变得胆子越来越大,她们往往无视约束条款,一不高兴就离开雇主家,通过无孔不入的黑中介寻找新的雇主。
广州的雇主刘珉告诉记者:今年3月,他通过中介找了个菲佣,人不但漂亮,且性情温顺。大学本科毕业,学计算机,很聪明,什么东西一教就会。因此没来几天,他的太太就多次表达了对她的喜欢,来他们家之前,这菲佣曾和中介公司的人表示,如果雇主好,就干上3年再回去。所以中介和她签了3年的合同。结果因为他太太毫无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她的喜欢,这个菲佣半个月内两次提出加薪,第一次他们答应了,第二次被他们拒绝后,她便立即提着行李回了家政公司。
家政公司的人问她是雇主不好吗?她说不是,她就不想在他们家呆了,没原因。刘先生找家政公司要人,家政公司的人说:他们不敢逼她,否则她就回去别的公司找工做了,现在菲佣到处乱跑,为了留住人,他们不敢难为。
就这样,刘珉忍气吞声地等了一个月,才等来新的菲佣。
这家家政公司的老板告诉记者:“菲佣现在越来越可恨了,也开始像中国阿姨一样不高兴就闹辞职,因为她们知道我们没办法约束他们。常常他们闹着从这个雇主家离开后,发现新雇主还不如老雇主好,因此后悔不迭。可当时怎么和她们说都不听。害得我们和雇主之间经常为此发生纷争。”
于是,付出昂贵代价的雇主们,要面对人财两空的境地。家政公司不会随便把揣进腰包的钱返还客户,他们会百般推诿,这种纷争无法获得法律保护,谁都不敢搬到明面上,所以一番鸡飞狗跳之后,吃了哑巴亏的大多是雇主。至于雇主和家政公司,都对雇用菲佣的性质心知肚明,他们也没有办法追究黑中介及菲佣的法律责任。假如雇主或家政公司亲自去抓逃跑的菲佣,菲佣们情急之下会集体跑到大使馆去告状,大使馆联系所在地派出所,派出所就会根据规定处罚雇主和家政公司,没有谁愿意承担这样的后果。
在家政公司工作的于女士说,这几年菲佣从雇主家逃走的情况司空见惯,跑掉的菲佣有的就在公司附近租房,逛街时遇到,会若无其事地走过,“谁想抓她们回去,她们就闹,她们也常常拿这个威胁家政公司和雇主。”
一位从美国回来就一直做菲佣中介的从业者,面对巨额收益,却决定洗手不干了。她说,做了十几年了,目前菲佣在中国的问题越来越多,包括吸毒、卖淫的情况也出现了,远远不如前些年单纯。其实大陆菲佣现象之乱,责任在于大陆人自身,“为什么在香港和台湾,她们就能安分守己?就能不逃跑,不偷东西?因为有法律规范和约束。”
“本来一个菲佣可以是干全部家务的,结果很多‘土豪’一次请3个,一个做饭一个看孩子一个做卫生,同样的钱,工作量却不一样,造成了菲佣现在在大陆开始挑雇主、挑工作的状况。现在菲佣在大陆的状况,也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中国人最擅长的就是破坏规矩。”做中介的刘女士说。
“如果有一天菲佣不让进来了,我们会很痛苦,现在工作节奏这么累、这么快,太需要她们这样职业的管家了。最主要的是,用她们会提高生活质量,而用中国保姆,反倒会更累。在如此需求下,政府应该寻求一个合理方式,让她们存在下来。”家里请了菲佣的王女士说。
卢云霞告诉笔者,她半年前请安娜回来的时候,一次性向家政公司交了6万多费用,还不包括给安娜的工资,结果安娜干了5个月就跑了。中介费又不给退,只能认了。
明天依旧是黑市?
中国大陆的新兴富裕阶层已经体会到菲佣的好处,虽然政府严令禁止菲佣入境,但是巨大的需求仍然使地下菲佣市场十分活跃。受访的中介机构介绍说,如今菲佣的雇主中,主体是中国人,某家政公司介绍,每10个菲佣雇主中有9个是中国人。
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陆续出现了一些菲佣中介机构。这些中介公司一般都拥有自己的网站,雇主可以上网了解到菲佣的详细资料,甚至可以通过视频挑选菲佣。由于需求旺盛而市场无序,菲佣的黑市价格不断攀升,在境外人士看来已近乎天价,即使这样,并未妨碍中国的富豪们对菲佣趋之若鹜。
一位东北籍的富豪毫不隐讳地说:生活是为了快乐,挣钱也是为了快乐地花,中国阿姨就是一个土鳖,还不听话,天天把我气得半死,我宁愿多花点钱找个舒心快乐!他觉得用过菲佣之后,中国的阿姨没法再用了,“不是一个级别的”,“人家菲佣,我不会的她还会呢,不用管。很多衣服我老婆都不知道怎么洗,以前总送干洗店,现在菲佣洗的比干洗店还好,谁不高兴啊!”
现在,中国大陆的很多大中城市都有规模不等的菲佣市场,滋生了一个暴利产业。在政策与市场的扭曲状态下,很多“有关系的人”和相关执法部门的人,腰包迅速鼓起来了。
熟悉内情的人士透露,从2005年起,菲佣们在黑中介和出入境管理人员的联合运作下,源源不断地从各个口岸入境,她们的主要通道最初是深圳、广州,此后延伸到海口、厦门、北京、海南和内蒙古,其中以北京和深圳为甚。
北京一个从事了3年黑中介的老板告诉记者,目前他旗下有两百多个菲佣,分布在全国各地,北京有一百多人。据他介绍:北京这样的中介公司起码20家,有的干了十多年的,旗下的菲佣至少上万人。
面对笔者暗访的时候,深圳某家政公司的一个工作人员表示:“你去网上查查,我们公司还被报道过呢,当然对外我们说只做中国阿姨。我们从2005年开始做,到目前菲佣至少几万人了。我们没事经常会去公安分局坐坐,每年都要给他们‘上供’,他们才不会查我们。你以为呢,如果他们查我们,就要交罚款、关门,不和他们搞好关系怎么行啊。”
她告诉笔者,目前他们手上有七八个可以选择的菲佣,她还强调自己的老板是海归,素质很高,菲佣的质量绝对有保证,此外,他们与管理部门的关系比较好,不会有任何麻烦。
3年前,笔者以找菲佣的名义认识了菲律宾人任恩。任恩早在2004年就开始往中国“倒运”菲佣,身份类似于“蛇头”。瘦弱精明的他无疑是最早尝到甜头的人,此后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他长期和北京、深圳的五六家黑中介保持联系,家政公司负责在国内找客户,他从菲律宾找菲佣。
与任恩的角色不同,无数个“魏国”把持着签证这一关,他们在这个地下市场浸淫多年,早已打通了诸多的关口和出入境管理局,大把献金之后,带给自己的也是非常丰厚的收益。
在记者截稿的前几天,一个在出入境管理局工作的人士透露,从去年开始,有关部门已经开始查处这些受贿人员,3月份某出入境机构还被抓走了几个,受贿金额都在上千万。
近两年,随着中菲之间偶有摩擦,菲律宾政府也明令禁止菲佣来中国打工。据任恩介绍,菲律宾政府这两年在出入境方面进行了严格的把控。因此,来中国的菲佣越来越少了,不是她们不想来,是没办法轻易来了。
从去年开始,黑市的签证费也越来越贵,很多中国雇主不愿再给菲佣办签证了。所有这些,都阻止不了为了淘金梦而不惜铤而走险的菲律宾女人,她们千辛万苦来到中国大陆,为了不断上涨的薪水(今年的平均水平比去年涨了10%-20%),她们认为即使“黑”下来也是值得的。
“3月份的时候,警察突击行动,我姐姐就被遣送回去了。”玛瑞的眼角有了泪光。但是,她不会被这样的震慑吓跑,“干上三五年后,钱也挣够了,再彻底离开。即便是被遣送回去,坐十几天的牢,有吃有住的,还能省个机票钱呢。出来打工什么苦没吃过?不在乎了。”
据了解,随着菲佣入境困难的加剧,很多精明的黑中介近来做起了印尼和缅甸保姆的生意。不过,印尼和缅甸的保姆大多不会英语,在京沪广深等大城市几乎没有客源,她们大多分布在二三线城市。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一位法律专家指出,对菲佣的需求,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政府要给她们一个合理合法存在的方式,同时加强对国内保姆市场的管理和规范,那么多大中专的毕业生都在待业,如果中国本土保姆也具备了相应的职业素养和操守,有自己的职业道德和标准,谁愿意花高价、不合法地找一个外国保姆呢?
从目前的趋势看,中国大陆对菲佣的限制越来越严,与巨大需求之间的矛盾也在加剧,“黑市”如若继续,乱象也难有终结。
文|佳琳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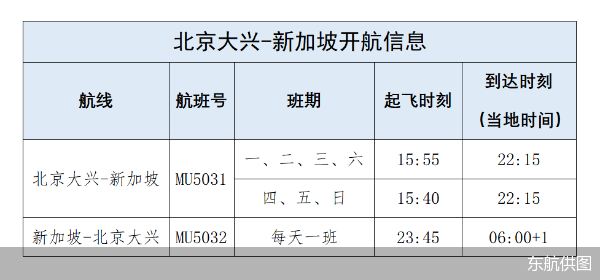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