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围棋》为例,探讨在日本电影中,以自我发现为幌子的叙事特点
Cine Qua Non还策划了迷你纪录片季“想想韩国”,其中包括遣返,A State of Mind,以及本文将讨论的下一部电影,亲爱的平壤。
该工作室的新闻副本敦促观众,通过朝鲜半岛各地三部作品的三个观点重新考虑韩国,重新考虑日本。
这些电影被定位为提供对“未知的朝鲜日常生活”的洞察,并故意反驳日本主流叙事,这些叙事涉及朝鲜绑架日本公民(其火化遗体在2000年代初被遣返)和核试验。
01
在日电影

虽然“在日电影”的概念是不确定的,许多人对指定在日电影语料库犹豫不决,但在制度定位的话语中仍然存在此类电影的建构。
正如奥利弗·露(Oliver Dew)所说,在日电影从历史上的许多角度挪用了广泛的电影实践,包括殖民政策电影、战后新闻片、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的“良心电影”以及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的黑帮节目图片。
现在,在日电影领域所包含的媒体的绝对多样性使任何一种文本或任何一种银幕实践模式“代表”在日韩国人的主张变得复杂。
在日形象的力量将继续体现在它超越代表后殖民创伤的负担的能力上,虽然这主要是与在日朝鲜人社区有关的。
但这些图像提供了一种视觉和象征性语言,通过这种语言可以询问日本帝国历史的其他元素,与本文最相关的是,在Eric Khoo的《拉面茶》中,它如何在新加坡语境中实现这种审问。

改编自金城一树的小说,幸田一雄的电影《围棋》预示着一个以前从未见过的在日主角:杉原(久保冢洋介饰),超男性化的浪漫女主角。
他的表演颠覆了在日以自我发现的青春电影为幌子的受害叙事,在这方面,它让人想起大岛渚的《绞刑之死》的实验主义。
该作品拒绝将其在日主人公R描绘成“韩国”作为“民族国家”的代表,犯罪归咎于“弱势社会地位”或“无情杀人犯”的少数人。
Go试图将杉原不成熟的自我概念建立在身体停滞和心理旅行中,杉原和他的朋友们鲁莽、不安分的行为反映了他们因公民身份而经历的空间限制。
他们被困在再日选择神身份的社会结构中,身体上无法走出日本,Go的第二个镜头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摄像机动态地捕捉了杉原和他的在日朋友在地铁站,当杉原跑过火车时,画面冻结以介绍。
杉原的冲刺通过各种快速剪辑来展示,从他的脚踩在轨道上,到跟踪镜头中的侧面轮廓,再到横跨画面的侧身奔跑。
胜利的杉原举起双臂,跑到下一站,过渡到他和他的朋友们骑着一辆滑板车试图逃离警车,他们在陷入僵局之前转向田野栅栏,这些狂热的运动和障碍的主题在整部电影中反复出现。
它们反映了流氓试图超越选择神社会的决定论结构的局限性,以及整个日本对在日人的质询。
02
精神稳定性问题

在后来的场景中,杉原和他的朋友们在田野中奔跑,反对他在朝鲜一所学校列队行进的镜头,这部电影从各个角度使用了快速剪辑。
两个看似解放的时刻恰逢:杉原与朝鲜学校的行军队伍分道扬镳,而他开始在野外飞行,杉原的叙述表明,这种限制的解除源于他在“朝鲜国民”或韩国国民之间“选择的权利”。
然而,他再次与栅栏相撞,摄像机跟踪他摆动的双腿,然后他滚到地上,杉原在空中飞行,撞上了栅栏。
幸贞回忆起三池崇史在《死或生》中对在日中国黑帮的描述,他们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国人,必须逃离警察。
杉原和他的朋友们爆发这些运动的关键是精神稳定性问题,这种不安分的表现在多大程度上是对限制性社会结构的身份主张。

与杉原希望超越其身份的决定论(无论是生物学还是人类学)一起呈现,物理限制表明实现物理回归是徒劳的,他和他的朋友们的动作是“控制在他们的小笔里”的一种方式。
然而,这种运动感——奔跑、飞翔、行进——并不一定意味着“旅行”的概念。
因此,转向Go使用照片作为跨时间和空间运动的一种方式是有启发性的,旅行的图像,代表了在其他地方寻求的快乐的短暂性。
在那里,在日身份的决定论失去了它的重量,当Sugihara的父亲观看日本旅游节目的电视广播时,引入了旅行的愿望,揭示了夏威夷海滩的场景。
“Aloha 'Oe”在下一个场景的续集中播放,杉原的父亲改变了他的公民身份,成为“在日关国神”或在日韩国人,在官僚办公室的桌子上猛击朝鲜意识形态的书籍和各种别针。

接下来是镜头穿过房子走廊的剪辑,露出了Sugihara的父母在夏威夷的鞋架上的形象,戴着花环,两侧是穿着刻板椰子壳胸罩和草裙的妇女。
一连串的跳跃剪辑将镜头直接带到了他父亲的脸上,幸福地接受了亲吻,从表面上看,照片中捕捉到的兴高采烈削弱了他们护照转换背后的意图。
选择夏威夷而不是冲绳或关岛等其他太平洋旅游目的地引发了美国种族话语的幽灵,在这种话语中,美国国籍并不拘泥于民族遗传学定义。
夏威夷是一个幻想的度假空间,是美国帝国的建构,正如卢铉(David Roh)所说,第三国家空间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一个暂时占据的地方,以重新谈判家庭自我。
这张照片象征着日本以外的世界的魅力,在这个世界里,韩国护照提供了灵活性,同时避免了返回朝鲜的可能性,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无法在家庭空间中协商这种家庭自我。
03
西班牙之旅

随着电影的进展,这张照片所站立的鞋架变成了锚点,在与杉原进行了一轮训练后,他的父亲坐在那里,对着倾盆大雨大喊大叫。
杉原不认识他的话,问道,那是什么,他的父亲回答说,西班牙语,很久以前就想成为西班牙人。
响板和弗拉门戈吉他的声音表明了西班牙之旅,场景切换到架子,平移露出他父亲穿着西装的照片,他的母亲穿着连衣裙,头发上插着玫瑰,他们的手臂像舞者一样向上伸展,背景是圣家堂。
这张照片展示了一个文化模仿的时刻,他的父母喜剧地采用了西班牙人的着装和行为,种族幻想的政治再次发挥作用,西班牙作为一个空间,他的父母不会面对他们在宰日身份的包袱。
摄影让建构的现实感挥之不去,能够抛弃这种民族包袱的记忆,Sugihara学习西班牙语的学习接住了这条线索,尽管它最终充当了仲裁者来阐明他自己无根的第三条道路。

最后一张露出的照片是杉原的父亲和叔叔,当他的父亲哀叹他哥哥泰贤的去世时,电影暂时进入了情节剧模式,忧郁的音乐播放着他父亲对贫困的回忆。
这被杉原打断,称其为“胡说八道”,声称哭泣的故事并不能弥补留给下一代在日的身份矛盾,影片切回架子,平移到杉原的父亲和叔叔小时候的照片。
无论是在朝鲜还是韩国甚至日本拍摄,都不清楚,但杉原的叔叔被透露已经“回到了 50 年代的朝鲜”。
将回归视为意识形态表明,理论上去朝鲜是杉原一家的一个选择,这幅图像与夏威夷和西班牙旅行的古怪图像形成鲜明对比。
将观众带入朝鲜半岛分裂的历史,暂时瓦解了在日过去和现在。然而,在他们回家时,他反思道。
04
法律约束

为什么入口处的愚蠢照片,为什么他们的国籍会发生变化,不是去夏威夷,这是给的,父亲试图解开腿上的镣铐。
正如Sugihara明确指出的那样,这些照片提醒观众,放弃选择神国籍是进入更广阔世界的必要第一步,而不必坚持日本的再入境许可。
这表明韩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渗透,促进了跨境旅行以及新边界内的身份认同,最终,关国人国籍是为了满足杉原“消灭边界”的愿望。
消除韩国/日本、北方/南方、日本/世界的边界,照片的承诺是扩展一个想象的空间,无根的流浪者可以扩大他的流浪范围。
然而,正如仓石一郎(Ichiro Kuraishi)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对过去的遗弃显然带有一种保守的、几乎是反动的反侨民和反种族的信息。

归根结底,无根不足以超越在日本成为在日的法律约束,日本仍然是杉原无法返回的地方,而韩国不可能比朝鲜更有意义的家园。
在围棋中,无根似乎不一定是“反侨民”,当然不是“种族盲”的一种形式,但也许是关于在日韩国身份政治的更广泛话语中的一个路点。
日本境内外旅行的主题,以及照片的建构现实在场日身份认同中坍塌时间和空间的方式,代表了杉原的身体陷阱和与身份类别的心理脱离。
与围棋相反,杨永姬的《亲爱的平壤》捕捉到了回归家园的可能性,作为一部个人纪录片,这部电影将镜头前和镜头后的非虚构景观个性化。
正如凯瑟琳·罗素(Catherine Russell)所说,摄像机相对便宜,重量轻,本质上不专业,有助于它们的“'覆盖'经济学”。
它们能够捕捉长时间的日常生活,记录身体和家庭最私密的空间,这部电影探讨了杨的父亲,在日活动家和社区领袖。

在意识形态上过度决定,于1972年将他的三个儿子,杨的哥哥“遣返”到朝鲜,他、妻子和杨留在日本,不可逆转地将家庭一分为二。
奥利弗·露(Oliver Dew)认为,这种创伤不能纳入孝道自我牺牲的人文主义框架,因为杨的父亲牺牲了他的儿子而不是他自己。
随着电影的进展,很明显,杨在电影中的视觉缺席与她缺席家庭的决定,及其集体政治意识形态是平行的。
笔者认为,她的身体形象确实出现的地方,是作为一个孩子,从1970年代和1980年代变色的照片表面向外看。

正如露所观察到的那样,她的问题和回忆贯穿始终,其特点是内省的倾向,可能会质疑屏幕上看到的图像并使其含义受到质疑。
杨对家庭内部这种身体和意识形态分裂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照片,由于她的兄弟们无法离开朝鲜,杨展示的照片是实体的,放在门口上方和橱柜上。
但也是数字的,填满了整个画面,它们让观众以生动的方式想象她的家族历史,捕捉她的家庭老龄化和他们50多年来参与朝总联活动。
来源:
- 佐藤忠雄,《遇见杀我的人》,永贺孝轮(1968年30月):第<>页。
- Ko,“代表在日”,140。
- David S. Roh,“Kaneshiro Kazuki's GO和在日韩国人的美国种族化”,Verge:全球亚洲研究2.2(2016年秋季):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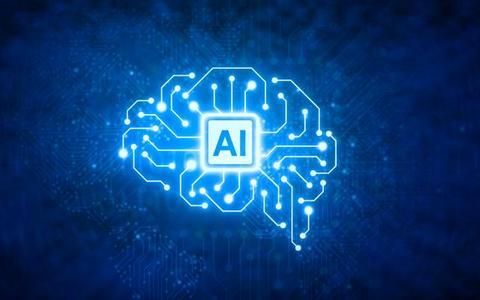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