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关系的生成:旗袍的隐喻与后西方身份的建构|国政学人

上海国际关系的生成:旗袍的隐喻与后西方身份的建构

作者:石之瑜,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新加坡联合早报特约政治评论员、知名台湾问题专家,研究专长为中国研究、政治心理学、文化研究。
来源:Shih, Cy. Engender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Shanghai: the metaphor of cheongsa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ost-Western identities. Int Polit 58, 661–678 (2021). https://doi.org/10.1057/s41311-020-00274-0
导读
旗袍是近代上海都市妇女的形象招牌,始于“旗女之袍”,建立清政权之后广布全国。1930年代的上海,女人们将旗袍穿得风华绝代、无以伦比,营造出时尚的“东方巴黎”女性形象。从晚清到民国初年,再到现今,传统旗袍在上海开放、进取、包容的大环境的影响下,慢慢演变为中西合璧式服装,呈现出女性精致玲珑、开放活泼的形象。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致力于将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与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政治语境相结合,形成具有一定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文章作者石之瑜是中国从事性别和国际关系研究的先行者之一。作者在这篇文章中重点关注了城市领导者的决策思维,以及旗袍文化意念与高调的城市精神的联系。石之瑜对后殖民女性主义的批判性创新表明,自我浪漫化、非解决方案和不一致正是用以超越由霸权话语内化的界限的合理策略[1]。
引言
文章从张艺谋执导的电影《金陵十三钗》入手,对中国上海将旗袍作为身份策略的做法进行了分析和反思,详细探究了自我浪漫化是如何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便利话语的。文章第一部分着重论述了旗袍对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批判性反思作用,并通过旗袍对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角色理论和关系理论进行了补充。第二部分简要总结了作者对中国现代性矛盾的理解,并提到了旗袍的穿着是如何为政治目的服务的。第三部分通过实际案例介绍了旗袍在增强上海人自信心的实践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第四部分探讨了旗袍作为城市的身份隐喻,以及旗袍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文章最后结合国际关系理论,探讨了自我浪漫化对角色理论、后西方理论和关系理论的影响,并对自我浪漫化如何在实践中塑造上海的城市身份进行了分析。
作者认为,旗袍流畅的曲线造型能够十分贴切地勾勒出东方女性躯体的婉柔美,体现出含蓄凝重的东方神韵。1943年2月18日,宋美龄身穿旗袍,站在美国参议院的讲台进行了20分钟的演说。她生动地宣扬了中国抗战对世界的贡献,促使美国重新思考重欧轻亚的政策,不卑不亢地争取美国朝野对中国的支援[2]。宋美龄的访问轰动全美,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围绕着宋美龄的外貌、口音以及两院对她的同情展开。无数的报道引发了读者对于旗袍所蕴含的东方女性柔性美的想象,日后在美国各地进行的援华募捐活动获得极大回响,美国国会更是决定废除当时已实施长达六十一年的《排华法案》,对国际舆论与日后争取对华援助产生了深远影响。
旗袍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
当前的国际关系研究普遍忽视非西方视角的文化和历史,为此作者分别从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角色理论和关系理论的视角提出补充尝试,并说明自我浪漫化的概念如何对以上理论进行补充和完善。
“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根据各国不同的新发展经验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塑。“后”不是摈弃、颠覆、反抗和解构,而是创新、发展、重构甚至超越,是试图共同建构一种超越西方和非西方二元对立的国际关系理论知识体系[3]。具体而言,在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可以通过将性别作为一种社会(即非地理)遗产,来弥补由地理文化遗产导致的身份策略差异。在城市层面,旗袍作为一种隐喻,可以暗指性别和社交场所,而后者作为后西方理论和实践的来源远比旗袍更为广泛和深入。
20世纪70年代,卡列维·霍尔斯蒂将“角色理论”引入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角色理论”认为国家的角色是政府总体的外交政策行为,主要受决策者国家的角色观念(地理位置、经济与技术资源、国家价值观、教义信条或意识形态等)、国内需求及外部环境中的关键时刻和趋势的影响。作者认为,在“国家角色理论”的研究中,可以将性别作为一种角色,并且关注这一角色对其他角色产生的影响。旗袍,代表一种自我浪漫主义的精神状态。旗袍的穿戴者并不是被观赏的对象,相反,他们提炼和利用旁观者的喜好,在自我欣赏、自我满足的同时,通过改变旁观者的态度来展现其自身价值。
从“关系理论”的视角来看,每一个国家在采取行动的时候,都必然表达出国家的身份认知,而其中深刻地包含了在该国历史、地缘关系脉络里早已形成的与周边其他行为者及地缘生态之间的“关系”,这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在身份中已然具备的“关系性”,因为在自我与他人之间建立了一种大家都拥有的“共同性”,可以促成彼此接受,从而确保国际秩序[4]。正如宋美龄的演讲在美国掀起风暴一般,自我浪漫化是一种即兴创造关系的特殊方式。关系理论可以通过对旗袍隐喻的临时关系而受益,这种对性别化的思考意味着男性和女性在国家的战略规划过程中,具有同样的自我浪漫化和中性化生理性别的能力。
“诱惑”与现代性之间的矛盾
与旗袍相伴相随的“解放”和“诱惑”,都体现了个体对自我意识的追求。在遵守父权制亲属规则的社会中,“诱惑”被认为是不道德和不传统的。然而在现代社会,性的选择权再次回到女性手中,不论“诱惑”与否,都要由女性根据自己的选择来决定。旗袍“从根本上与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关键时期对女性身体的重新定义有关”,它的设计风格展示出了现代性,象征着女性的进步,标志着女性在身体上的解放,引申开来,也标志着当时在政治和社会上的解放;但它同时也可以是具有挑衅意味的服装,比如被上海的广告商用以暗示性的可能性。这种矛盾的心理不仅展示了男性权力和女性依赖之间隐含的等级关系,同时也表明女性是有能力和意愿去选择奖励和分散男权权力的。
作者认为,在中国兴起的旗袍热潮很难说是“自我东方化(self-orientalizing)”的表现,因为对旗袍的怀念,只对那些能够接触到民国女性形象的中国人才有意义。相反,旗袍在海外从未失去自己的市场,因为它会给不熟悉的观众带来充满诱惑和感染力的身份,这些观众更大程度上属于“西方”的范畴。因此,作者采用“自我浪漫化(self-romanticizing)”的概念来描述那些穿着或使用旗袍隐喻的人的身份策略。“自我浪漫化”指的是行为体在自我欣赏的过程中,散发出积极主动的情绪,从而使旁观者不自觉地被吸引到浪漫的氛围中,进而改变旁观者的态度。“自我浪漫化”与“自我东方化”的不同之处在于,“自我浪漫化”的情感是自给自足的,它不需要依靠预先存在的西方旁观者的想象来确认这种积极的感觉。这种不依靠旁观者的做法,重新确立了自我浪漫者和旁观者之间在认识论上的平等,使得旁观者的看法对自我浪漫者的感觉或信心并不重要。对于那些将旗袍隐喻作为身份策略的人而言,自我浪漫化可以使旁观者(包括中国人和西方人)更自然地接受这种(隐喻的)行为和关系,减少对抗的气氛,让人们在面对看似不可调和的问题时表现出耐心。
旗袍对上海的身份塑造作用
除了上海,没有哪个城市能如此直观地将旗袍与自己的城市形象联系在一起。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在旗袍成为时尚甚至是城市生活的必需品之后,旗袍女郎的形象开始频繁出现在广告、酒吧和咖啡店中。随着它们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渐渐无法起到任何商业功能。相反,这些旗袍女郎的图像似乎成为了所有者或销售者所选择的身份声明,当然这些所有者或销售者可能是男性。在文化大革命后,这些曾经作为政治主要参与者的男性,更容易将旗袍或旗袍的隐喻(不关心政治、解放思想、文化重组)与他们的城市联系起来。他们在文化上乐于重新组合一切可获得的东西,尤其是旗袍制作这种有关剪裁的精致艺术。
在21世纪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旗袍发展成为一种身份表述的趋势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它既有官方的一面,也有民间的一面。在官方层面,2010年,海派旗袍作为上海女性代表的典型穿着风格在上海世博会首次亮相,并相继走进米兰世博会、联合国维也纳总部等万人瞩目的舞台;2011年5月,旗袍手工制作工艺成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2014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第22届APEC会议上,中国政府选择旗袍作为与会各国领导人夫人的服装。在民间层面,旗袍穿着者希望通过自己的穿着获得观众的喜爱,当然这绝不是为了满足观众的需求,而是为了自我满足。进一步而言,旗袍穿戴者希望将这种自我形象投射到旁观者的眼中,进而给观众带来乐趣。
旗袍有助于塑造穿着者积极的自我形象。从风格来看,旗袍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可以将穿着者与世界上的任何人群和场合联系起来。更为重要的是,旗袍是确保穿着者在自我形象方面与众不同的精确元素。一方面,旗袍加深了旁观者和穿着者之间的区别,能够在没有任何对抗的状态下增强穿着者的自信;另一方面,通过对双方获得的文化元素的提炼和重组,旗袍会营造一种相互认同的愉快氛围,并将浪漫化的旁观者和自我浪漫化的穿着者联系起来。由于双方在对旗袍的喜爱上产生了相似之处,旗袍有助于促进人际关系,重新构建旁观者的形象。
旗袍:属于上海的百年芳华
上海旗袍并不是一种能够使用清晰的语言描述相出来的身份。它揭示了一种认识论的身份,而不是本体论的身份。这种认识论特征反映了一种关系文化,它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看待世界,以及如何与不同的世界联系起来。简而言之,这是一种能够承担角色同化与重组的身份。旗袍的形象表明,旗袍的穿着者灵活应变、随时准备好享受文化重组,这与官方的宣传,即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上海城市精神不谋而合。这是一种承诺,即在上海,所有问题都可以有实际的解决方案,所有的极端情况都可以成为实际生活的一部分。这种“开明睿智”是自我浪漫化的开放和适应的准备,这种氛围吸引着那些希望做出改变的人们来到上海,因为在那里,有些人总能巧妙地做出预期的改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近代史上,政治领导人总是前往上海发动变革。因为如果他们的政治举措能够首先在上海实施,那么接下来的政治转向总是显得更有道理。
旗袍是一种不张扬但独具特色的服装,它是东方和西方、传统和现代、功能和目的的混合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旗袍的吸引力不仅仅局限于性感,更在于它所拥有的不断重组的能力。旗袍可以通过重组的文化特征带来灵感,使旁观者与穿着者感到舒适。当然,对于绝大部分佩戴者来说,这种自我浪漫化不以接受他人淫欲的目光为前提。在后西方学派对当前国际研究的批判中,提出要通过不同的场所来重建国际关系的不同身份实践和话语。不过虽然性别话语和关系无疑是场所和国际关系的基础,但后西方国际关系研究未能将性别本身视为场所。事实上,旗袍以其非地域的特点体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地缘文化轨迹,可以作为一种隐喻,暗指无处不在的女性化场所。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自我浪漫化
庶民和后殖民主义研究关注的是那些被霸权话语压制的行为体。后殖民主义研究从已经受到殖民主义知识与体制所制约的行为体出发,探究上述行为体在无法完全摆脱殖民主义影响的基础上,如何保持自己与殖民主义的不同。相关研究坚决反对自我东方主义,并且对后殖民主义能否重新利用霸权价值观、角色和制度,来实现脱离这些制度预期的目的持有矛盾态度。然而,自我浪漫化并不等同于自我东方化。自我浪漫化的观点是,重组的文化只有在能够吸引进行文化重组的主体的前提下,才能为其旁观者服务。重组的文化所提供的服务和享受对旁观者来说既不是预期的,也不是熟悉的,尽管这些服务对他们来说也不可能完全陌生。在自我浪漫化的过程中,积极的感受并不完全来自于旁观者的反馈,更多的是发自内部,并且强烈到足以影响文化的旁观者。
结论
旗袍的广泛穿戴,体现并强化了上海市民自觉的身份认同策略,这种身份认同策略不再强调差异性,更多的是对文化的适应和重组。随着越来越多的上海女性在各种社交场合穿着旗袍,旗袍愈发成为一种特殊的、充满活力的社交场所,尽管它同时传递了一种随时准备好为来到上海的国际游客们提供即兴服务的讯息。穿着旗袍增强了穿着者群体的吸引力,对于市民们来说(不论男女),它更像一种自我浪漫的表现。自我浪漫化表明了城市乃至整个国家对穿着者的支持,他们可以对穿着(隐喻的)旗袍感到自信和自豪,同样地,他们也可以以一种不张扬但自我满足的方式将不同的价值观和制度结合和重组起来。
词汇积累
产生
engender
旗袍
cheongsam
隐喻
metaphor
自我牺牲
self-sacrifce
注释
[1]李英桃,石之瑜.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北京、台湾两位国际关系学者的对话[J].国际观察,2022(02):128-156.
[2]1943年2月18日,宋美龄一身旗袍在国外演讲,二十分钟激昂发言[EB/OL].档案纪实TV,https://haokan.baidu.com/v?pd=wisenatural&vid=13079389441217166728,2022.
[3]尉建文,李培林.后西方社会学与当代中国社会学[J].社会科学文摘,2018(05).
[4]石之瑜.国际关系中的“关系”理论与“后华性”实践[J].东南亚研究,2020(03).
译者:信思涵,国政学人编译员,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兴趣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公共外交。
校对 | 杨影淇 周震 张鸿儒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张誉璇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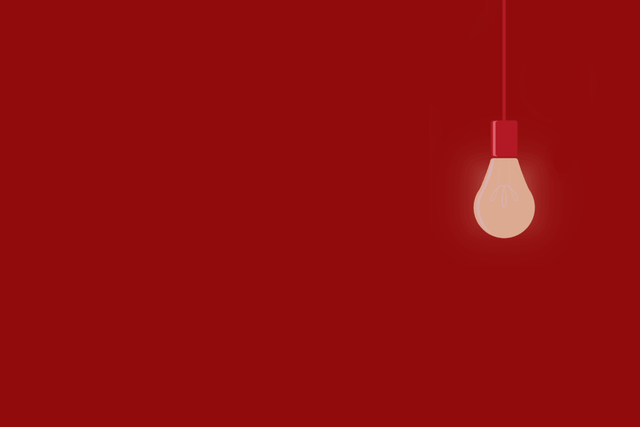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