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头,他为何被一张照片破灭了回国的梦想?
春节前的一天下午,印尼泗水一位朋友突然发来的微信:
噩耗!王钦辉先生于今日(2022年1月12日)上午9:30分不幸逝世,享年74岁。
“痛哉!痛哉!钦辉先生半个月前他还打电话给我,要我去福清侨乡博物馆,把馆内陈列的他们父子事迹的橱窗拍照寄给他,当时声音洪亮,一如往常,完全没有说起他生病的事情。怎么一下子说走就走了?真是太意外了……”
惊愕之下,我赶紧询问那位朋友。
朋友告诉我,王钦辉并非中标新冠疫情去世,而是因为身体太胖,多年患有糖尿病、冠心病,还有肺气肿,引发了肺积水,在泗水的医院救治了一个星期,结果药石罔效,撒手人寰。

印尼华人三教庙宇联合会总主席王钦辉(右)与其父——印尼三教会创始人王基财(大幅照片和事迹简介,2021年被正式陈列于福清侨乡博物馆。
王钦辉是印尼东爪哇知名企业家之一、佳雅纸业集团(PT.JAYA KERTAS)老板;他同时也是一位华人宗教领袖,担任“全印尼三教(儒释道)庙宇联合会”总主席四十余年。
因为写传记的缘故,我与钦辉先生相识多年,并在泗水和他朝夕相处了几个月,每天带我驱车在市区转来转去,差不多把整个泗水的中餐馆吃了个遍。我在雅加达北区PluitCBD 的住所,也是王先生购置的公寓,免费提供给我,对我颇有些知遇之恩。
突然听到他逝世的消息,我很难过。整个虎年春节期间,我不时会想起钦辉先生,脑海里经常浮现出他给我讲述的从前的往事。
我曾整理过四五篇有关王氏家族历史和其本人经历的文章,发表在本号,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翻看一下。
这位华侨大资本家的儿子,其实在学生时代,因为接受了左派华校的红色教育,曾经一心要回国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命运使然,未能如愿,后来便成为企业家老板和笃信佛道的宗教大佬。
那么,当年作为印尼进步华校的学生,王钦辉都有哪些难忘而奇特的经历呢?

2017 年 10 月 26 日,佐科威总统出席在雅加达举行的印尼佛教协会 (WALUBI) 全国工作会议。王钦辉作为印尼佛教总会第一副主席,在此次大会上陪同佐科威总统接见与会代表。
新华中学及那个年代的教育
王钦辉这一代华侨子弟接受中小学教育的时期,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而那个时代无论对中国,还是印尼,乃至对整个世界而言都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革命年代。这一时期,与特定的文化政治形态相关,大量来自新中国的当代红色经典文艺作品进入印尼华人社会,充满中国大陆意识形态的爱国主义的教育体系,也被完整地复制到印尼华校,尤其对华侨青少年学生产生了难以磨灭的重大影响。
1960年的年底,王钦辉和同学们集合在泗华小学礼堂,大家合唱了一首几十年前流行的中国抗战风味老歌:“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一曲唱罢,热血沸腾,这群十二三岁的孩子就从这里毕业了。
那一年,钦辉考上了位于加巴沙里街的泗水新华中学,在该校读了6年,一直到1966年新中关闭时刚好高中毕业。当年在泗水有几所较大规模的华侨中学,除了新中,还有中华中学和联合中学,此外还有一所全印尼唯一的女子学校——中国女学。这其中,要数新华中学办学历史最长,创办于1930年,前身为励志中学,后与泗水侨中合并,改名为泗水新华中学。
早在1940年代,印尼各地华文学校,便因大陆国共两党内战而出现了政治分化,分为左右两派,左派被称为“爱国进步”学校,右派则被视为“落后反动”学校。特别在新中国成立后,亲大陆和亲台湾的两派华社和华校矛盾愈发尖锐,相互抨击诋毁,几乎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
尽管双方时常争斗,针锋相对,剑拔弩张,但两派华校在办学宗旨、教学内容等方面,实际上仍然都是以向华侨后裔传播中国历史和语言文化、培养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反对华侨后裔数典忘祖为根本目的。两派学校也始终高举忠于祖国和热爱中华民族的旗帜,而只是在政治观点和政权效忠上存在分歧而已。平心而论,两派华校培养的学生都有很多精英人才,他们在经历过种种挫折和磨难之后,都在不同领域为印尼或中国的发展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泗水也是如此,比如王钦辉考上的新华中学,就是一所左派学校,其教学贯彻新中国教育方针,采用中国版教科书,学生们受到的都是社会主义的红色教育。另一所联合中学则属于偏右的国民党学校,高初中课程均依照中国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课程规定,参照当地政府文教部门法令加以编排。偏重于商业知识及基本技能的学习,重视教授中外优良文化。在两派之间,还有一所中华中学,提出“中中至上”原则,政治上要求思想自由,保持独立自主,不愿受任何政治派别的控制。

泗水唐人街墙壁斑驳的老建筑,充满了年代感的怀旧气息。
有趣的是,钦辉进了左派新华中学,二姐月娇读的却是右派联合中学。父亲系当地华人庙宇“凤德轩”敬神社主席,作为宗教领袖,老先生并不喜欢卷入政治,但是他两派都不得罪,还应邀担任了联合中学、新华中学的校董,慷慨解囊资助办学。所以他就让自己的儿女分别上了这两所学校。后来到1958年,联中被政府关闭,二姐随后于1960年回国深造,考入北京师范学院。
在新中上学期间,王钦辉阅读了大量来自当代中国的所谓的“红色经典”小说,比如《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乘风破浪》等等。半个世纪之后,他对上述书中许多人物的名字仍是如数家珍,林道静、卢嘉川、杨子荣、少剑波、许云峰、江姐、金环、银环、杨晓冬……甚至在小说里占的篇幅很小的一些反面人物,他也记得清清楚楚。

1960年王家二姐王月娇(后排中)订婚时全家合影。后排右四是父亲王基财,中排左二抱着小弟弟的那个小孩便是当时才12岁的王钦辉。
有一次和一个中国朋友谈起《林海雪原》,那人也是一个小说迷,两人回忆起这本书的种种情节,朋友记得《林海雪原》里面有个土匪冒充解放军侦查员,名字很特别,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绰号,但就是想不起来了。王钦辉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哦——你说的是那个‘一撮毛’吧?”朋友惊叹一声:“哎呀!就是叫‘一撮毛’啊!王先生你可真不简单!一个印尼华侨,比我们国内的人都记得清楚。”
五六十年代,泗水专门放映华语片的电影院有两家——一是“南京戏院”,二是“新华戏院”,钦辉每个星期都去光顾,差不多把那时新中国拍摄的故事片和纪录片都看过了,印象较深的诸如《上甘岭》、《五朵金花》、《刘三姐》、《小兵张嘎》、《洪湖赤卫队》、《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等。

泗水新华戏院旧址。
在王钦辉记忆中,泗水南区也有放映美国好莱坞影片的戏院,但观众似乎没有看华语电影的人多。“在当时充满革命热情的氛围下,所谓进步华校的老师和学生如果想看西方电影,都要悄悄地不敢声张,生怕被本校的同事或同学看到,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
那个年代,对华侨青年影响很深的文艺形式还有革命歌曲。新中广播喇叭里天天播放《我的祖国》、《南泥湾》、《祖国颂》、《洪湖水浪打浪》、《大海航行靠舵手》、《社员都是向阳花》《毛主席,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三八作风歌》等等。
钦辉和几个男同学喜欢唱那首《我复员回到了故乡》。
“到现在,我还是可以一字不落地唱下来。”王钦辉在汽车里和笔者说着,便张开喉咙唱了一段:“我复员回到了故乡,故乡全都变了样;万亩土地连起来,村连着村庄连着庄。我们亲爱的故乡,到处是一片新气象。”
说来惭愧,笔者在国内长大,但是从来没有听过这首歌,看这位印尼华人王钦辉唱得兴致勃勃,却无法同他应和。
话说回来,五六十年代的印尼华人社会,不管受到中国左倾思潮的影响多大,但毕竟不同于全民狂热,扫除一切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的国内,大家文娱生活中依然保留了不少旧时代柔软抒情的所谓“靡靡之音”,同样受到人们追捧。当时流行于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华人圈子的国语歌曲有《香格里拉》、《夜来香》、《夜上海》、《秋水伊人》、《玫瑰玫瑰我爱你》、《东山一把青》、《四季歌》等,而在歌坛经久不衰歌星以龚秋霞、周璇、姚莉、李香兰、白光、吴莺音、张露等人最为著名。
钦辉上小学时,经常和两个姐姐在家里唱歌。大姐爱唱雄壮有力的革命歌曲,二姐喜欢唱温柔婉转的抒情歌曲。大姐唱了一首声调高亢的“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古树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二姐就唱一首哀婉缠绵的《秋水伊人》:“望穿秋水,不见伊人的倩影。更残漏尽,孤雁两三声。往日的温情,只换得眼前的凄清;梦魂无所寄,空有泪满襟。”
钦辉小小年纪,什么歌都喜欢,喜欢听,也喜欢唱。。
有时候,家里的收音机总是不断地播放那首美国女歌星多丽斯·戴演唱的好莱坞电影《擒凶记》插曲Que Sera Sera。
每当此时,钦辉就会看到二姐跟着收音机,一起轻轻地唱道: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当我还是个小女孩)
I asked my mother,(我问妈妈)
What will I be? ( 将来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Will I be pretty? Will I be rich? (我是否会变得美丽、富有?)
Here's what she said to me(她对我说:)
Que sera, sera(世事不可强求)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顺其自然吧。)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我们不能预见未来。)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顺其自然吧。)
When I grew up and fell in love.(当我长大并恋爱了,)
I asked my sweetheart,(我问我的心上人,)
What lies ahead?(我们将来会怎么样呢?)
Will we have rainbows day after day?(生活每天都会美好吗?)
Here's what my sweetheart said:(我的爱人对我说:)
Que sera, sera(世事不可强求)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顺其自然吧。)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我们不能预见未来。)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顺其自然吧。)
……
这两个姐姐,都比钦辉大十多岁,已经长成青春靓丽的大姑娘了,自然有了向往爱情的心事。
1960年,二姐月娇同无数热爱祖国的华侨学生一道,踏上了北归回国深造的轮船。她去了北京,考入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后即结婚成家,并在北京一所中学教书。
二姐结婚没过几年,丈夫就因病去世,她就一个人带着年幼的儿子在北京生活。1973年,二姐和她的孩子去了香港,随后娘儿俩又回到印尼泗水定居,与大家庭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团聚。
岁月无情,人生苦短。前几年,在印尼成家的大姐和丈夫也已经过世。
如今只有年迈的二姐住在泗水,她的儿子和媳妇则在新加坡定居。
弟弟钦辉经常和二姐打电话聊天。有时候钦辉在外面看到二姐喜欢吃的东西,就特意买了派人送去。他也时常派公司的女职员和自己的女护士,去二姐家里探望照顾。姐弟情深,每次见面总有说不完的话。

2017年,王钦辉夫妇与二姐王月娇在泗水。
一张照片破灭了回国梦想
1966年4月,王钦辉的母校泗水新中与全国几百所华校一样,先后被当局关闭。此时,成绩优异且读完了高三课程的他,还没来得参加毕业典礼,大家也没有机会再合唱一遍那首《新中校歌》:“大好时光,正当青春,求学乐无穷。世运维新,学术演进,文化日昌隆。崇尚科学,讲求实用,礼义廉耻重。愿同学兮,爱护新华,发扬我校风。”
当局一声令下,他们不得不告别学校了。
王钦辉在班里有两个“铁哥们”,一位叫关文华,客家人,他的爸爸也是泗水富商。另一位叫严复,来自外岛,不晓得祖籍是哪里的。这两人与王钦辉彼此投缘,结成“死党”。三个小伙伴天天在学校,上课一起听讲,下课一同玩耍,好到形影不离。
封校那天,在军警虎视眈眈监视下,几千名新中学生带着恐惧、无奈、彷徨,噙着眼泪,背着书包,默默地离开了校园。
悲愤之中,王钦辉与关文华、严复等三位好友萌发了强烈的回国念头。回国需要中国领事馆签证,但是那时候中印关系极度紧张,中国驻泗水总领馆不堪每天受到示威骚扰,已迁回雅加达中国大使馆工作。三个年轻人决定去雅加达直接向大使馆申请签证,他们从泗水坐夜班火车来到椰城,下了车便直奔雅加达唐人区班芝兰附近草埔街(Gelodok),很快找到了设在一座古香古色中国式的大宅院里的大使馆。
钦辉他们不知道,这段时间中国大使馆也处在风雨飘摇的危险关头,印尼当局对使馆采取断水断粮等措施,并且多次派人冲击,已是朝夕难保。在这种形势下,中国驻印尼大使姚仲明便应召回国,留下副大使姚登山担任临时代办。姚登山军人出身,战争年代当过解放军独立团团长。他率领使馆工作人员不辱使命,斗争坚决,其本人也因此被称为“红色外交家”。
那天上午,王钦辉、关文华、严复一走进中国大使馆庭院,正在二楼喝茶的姚登山临时代办就看到他们了,立刻吩咐工作人员把这三个小伙子带上来。姚登山身材魁梧,高大壮实,操着一口山西味的国语和钦辉他们聊了一会儿。他说,你们这三个华侨小鬼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现在印尼形势复杂,反动分子气焰嚣张,但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我们国内正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开展文化大革命,你们如果下定决心回国,我可以特别批准给你们签证。
满怀爱国热情的三个年轻人,连忙用在学校期间接受的红色教育的豪言壮语向姚大使表示了回国的决心。
姚大使点点头,亲切地与钦辉他们一一握手,便把他们送到楼下。临走时还特别关照他们不要从大门出去,要走后面的小门。“你们出了门注意看看后面有没有‘尾巴’盯梢,现在是非常时期,一定要注意安全。”
大使告诉他们回泗水等候,签证做好使馆会按地址用快件寄到泗水。果然,钦辉他们回家不到两个星期,大使馆就把签好的护照寄过来了。
签证到手,接下来就要准备动身,钦辉的父亲基财老先生出面阻止了。一方面,他当然舍不得自己最看重的长子离开这个家;另外一方面作为过来人,父亲对国内异常艰苦的生活条件有过切肤之感。他也隐约听说,目前国内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到处搞批斗运动,许多归国的华侨学生都被分配去了农场种地,吃苦受累小事情,如被卷入无情的政治运动丢了身家性命也说不定。

中学时代的王钦辉(后排中)。
但是儿子似乎去意已定,态度坚决,非走不可,父子俩谁也说服不了谁。“争论到后来,毕竟姜还是老的辣,爸爸对付我这个毛头小伙子还是很有经验。他也没有硬摆出父亲的权威压我,而是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让我不得不暂时接受,于是问题就得到缓冲,事情就发生了改变。”
王钦辉说着,思绪又回到了那个时代。
我爸爸对我说,人各有志,你如果一定要回国,我不能逼迫你留下来。不过可不可以不要太急,你们三个好朋友不必一起走,或者先让一个人回去探探情形,若无大的问题,剩下两个再一起走不迟。
我看爸爸说得有道理,就同意了。经过商量,关文华第一个回国了。他临走时同我和严复约定:回国后如果看到形势大好,就拍一张站着的相片寄来,如果情况不大好,就拍一张坐着的相片寄来。为什么不能写信说明,而要用拍照片这种方式加以暗示呢?因为我们认为当时从国内寄信给国外,一定会给国内的干部打开检查,如果信上写国内不好,一个是怕寄不出来,再者也担心写信的人会遇到麻烦。
可是关文华一去三个月,既没有写信也没有寄照片,音讯全无,不知何故。
我们不甘愿就这样呆在不走了,也不放心关文华。于是,严复又第二个义无反顾地回国了。哎!严复不要忘记,到时千万寄照片来啊!我和他还是同样的约定,爸爸也在等着结果。
又等了两三个月,严复终于寄来了照片,信是从广州寄来的。我迫不及待打开信封一看,马上傻了——只见严复在广州越秀公园五羊塑像下拍的这张照片,既不是站着,也不是坐着,而是脱掉上衣光着膀子,耷拉着脑袋,趴在一条石凳上,两只胳膊也垂向地面,半死不活,好像一头任人宰杀的绵羊。不言而喻,看来严复回国之后,处境不是不好,而是极其恶劣。哇嘟!看了这张照片,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天作声不得。
我老爸看了照片,心情也很沉重,他为我的同学好友难过。但是,他也为我幡然醒悟,并因此打消了回国的念头暗暗高兴。从此,严复也和我失去了联系。后来有了关文华的消息,他在香港定居,但是一直没有露面。可能是因为他当初回国没有给我们写信,导致严复不明真相又第二个回国,并不幸失踪,文华感到内疚或者别的什么原因,他从此不愿意再和同学相见。
半个世纪过去,我想过很多办法,都没有打听到严复的消息,或许在那个年代的滚滚洪流之中淹没了……国内当时有红卫兵串联,到处搞武斗,我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情况。可以说,如果没有同学这张照片,我肯定回国了,至于会遭遇怎样的困境就可想而知。也可以说,是严复使我免去了一场苦难。
本书主人公王钦辉先生青春时代的上述经历,实际上是他那一辈华侨青年人生悲欢离合的一个缩影。回望当年,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发生的种种离奇故事,匪夷所思,亦真亦幻。
怀着对父亲先见之明的钦佩,还有对同学挚友的思念,以及庆幸自己还好没有贸然回国的复杂心情。年轻的王钦辉慢慢坚定了信念,他要像父亲那样踏踏实实,在印尼这片生息地上干出一番事业,开花结果,落地生根。
如果不是同学寄来了那张“半死不活”的照片,王钦辉当年不顾一切回国了,他的人生又会是怎样一番经历呢?
其结果恐怕谁也不好预测。
最后,借用一段带有禅意和宿命色彩的格言,来结束这篇文章:
我们今生所有遇到的人和事,前世已注定 ;我们来世所有遇到的人和事,今生已注定。轮回路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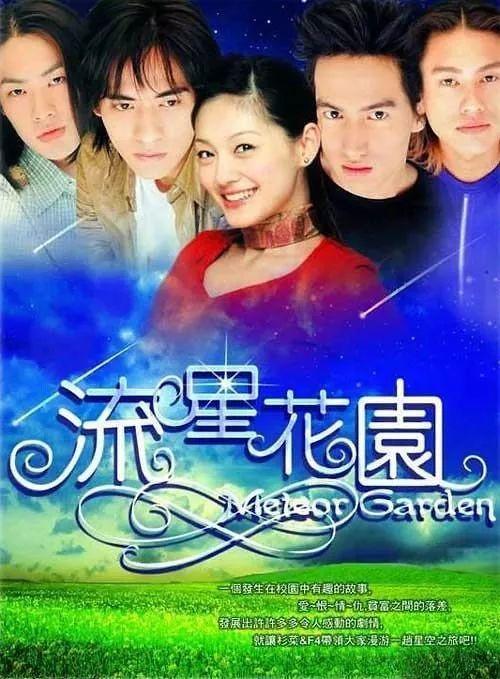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