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戛尔尼使华日志看中英两国当时的知识差距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9月,英国派出的特使马戛尔尼到达热河(承德)行宫,拜见了乾隆皇帝。(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8月2日《南方周末》)
如果以谢清高的《海录》与当时英国对于远东的知识相比,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差距。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当时的中国并不是不能获得外部知识,当时的中国有着许许多多个“谢清高”,但在世界全球化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外部知识,在中国却不为朝廷所重,也不为当时读书人所重。在“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么一个庞大的建构之中,竟然找不到这类知识可以搁置的位置。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9月,英国派出的特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到达热河(承德)行宫,拜见了乾隆皇帝。马戛尔尼此行的表面目的是祝贺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真实目的是要求与清朝扩大通商并获得割让小岛等权利。马戛尔尼使华的主要目的失败了,当时在清朝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反响;后来的历史却说明,这是中国历史上头一等的大事。
马戛尔尼使华前,英国政府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其中包括了关于航行和中国的“知识”准备。1792年9月,马戛尔尼使团从英国出发,沿着大西洋一路南下,经过马德拉岛(Madeira,葡萄牙)、特内里费岛(Tenerife,西班牙)、佛得角群岛(Cabo Verde,葡萄牙)、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葡萄牙),到达大西洋南部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Tristan da Cunha,后归英国);随后顺着洋流横向往东,越过非洲的南端,一直航行到印度洋南部的阿姆斯特丹岛,然后再顺着季风和洋流,到达爪哇岛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由此经昆仑岛、土伦港(今岘港),于1793年6月到达中国广东海面。从马戛尔尼使团的航行来看,他们对大西洋、印度洋以及东南亚各海域的气候、风向、洋流,已经有了比较好的把握。这是海洋与航海知识的运用与加强。
马戛尔尼使团对于沿途各地有着详细的记录,到了中国之后,更是有着各种各样的记录。这可见之于使团的官方文献,还可以见之于使团的许多私人记录(其中一部分也译成了中文,例如使团副使斯当东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英国由此可以获得许多外部的和内部的情报。这使得英国对于沿途和中国的知识有了很大的增加——可以说,这也是使团的目的之一。最近,何高济教授翻译了《马戛尔尼勋爵私人日志》(与使团医生巴罗的记录一并收入《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一书,下引书未注出处的,均指本书),让我看到了马戛尔尼的中国印象,或者说是他的中国知识。

《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何高济、何毓宁译,商务印书馆,2013(资料图/图)
马戛尔尼的中国知识
《马戛尔尼勋爵私人日志》篇幅不大,分成风俗与品性、宗教、政府、司法、财产、人口、赋税、文武官员的等级和制度、商业和贸易、技艺和科学、水利、航行、中国语言和结论等章节。作为两百多年前的“老外”,第一次来到中国,不懂中文,但对中国的观察和了解却相当深入。这是他们的知识需求所致。我在这里引用马戛尔尼的几段话,测一下他关于中国知识的水准。关于宗教,马戛尔尼称:
我现在来谈谈中国流行的宗教。就我所见,其中没有一个对信徒的行为产生多大的影响。教义可以不同,伦理几乎一样,都要支持和履行同样的社会义务。但人的品德并不总是以他们的宗教观而定,所以我相信,某一教派的犯罪分子很难比另一教派少。中国没有正式的国教,没有拥有垄断特权的教派,也不排斥某教派的信徒担任官职。国家的工作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不管他们是在庙里还是在浮屠里作祈祷。皇帝派来护送我们的使团中,鞑靼使节(徵瑞)信喇嘛教,王(文雄)是佛教信徒,乔(人杰)是孔教,他们三人做的是同样的工作。(第18页)
在当时的西方,宗教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有时具有超政治、超经济的强势地位。马戛尔尼也同样关注于中国的宗教生活及其政治地位。他提到的三个人都是乾隆皇帝比较信任的官员。徵瑞(1734-1815),满洲正白旗人,富察氏,时任长芦盐运使,后长期任职于内务府,他的宗教信仰很可能是仿效乾隆帝。王文雄(1749-1800)是武夫出身,贵州玉屏人,曾从征缅甸、金川,时任通州协副将,后官至固原提督,自称是佛教徒,很可能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烧香拜佛。乔人杰(1740-1804)是举人出身,山西徐沟(今清徐)人,时任天津道员,后官至湖北按察使,自称其信奉孔夫子是很自然的事。马戛尔尼对此不能详加区别,甚至将儒学也当作了宗教,即孔教。他可能不知道,徵瑞、王文雄也会同样地信服孔夫子的学说。然而,他对中国没有国教、宗教不占政治生活主导地位的判断是正确的。
关于财产,马戛尔尼写道:
在中国,皇帝的利益始终是头等重要的事,违反他的旨令,任何人的财产都是不安全的。例如犯罪,财产必定被没收。没有长子继承权,一个人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处理他个人的财产……一个留下遗嘱的人往往将他的财产传给他的妻子,特别在子女还幼小的时候。但如果他死时未留遗嘱,他的土地和财产就在他的儿子中均分,保留一份给寡妇作抚恤金……女儿得不到什么,但由她的兄弟供养直到出嫁……合法的利息是12%,但一般增加到18%,有时甚至到36%。法律惩治高利贷,但和别的大多数国家一样,很少处罚。(第31-32页)
这一段描写,表明当时在英国极其重视财产关系,马戛尔尼在中国也有相应的观察:私人财产在政治罪名下得不到保护,遗产的平均分配,女儿不分遗产和高利贷的普遍性。他的观察是大体准确的。
关于政府,马戛尔尼写道:
……以学识和德行闻名的中国教师被派去教导年轻的鞑靼王子,从中将产生未来的君主。汉语被保留为国语,古代的制度和法律极受尊重,原有的职官和庞大的官僚机构保留下来,被征服者的风俗习惯为征服者采用。这些措施最初施用于百姓,让他们很多人适应新政府。由此产生一个普遍错误的看法:鞑靼人不加区别地和认真地采用中国原有的一切风俗习惯,这两个民族现在完全融合为一。就服装和头饰而言,他们的穿着肯定是相同的,但不是鞑靼人习惯穿中国人的服装,而是中国人不得不模仿鞑靼人。各自的特点和性格仍无改变,任何伪装都不能掩盖他们不同的处境与心情。一方作为征服者而振奋,另一方则感受到压抑。我们许多书籍把他们混为一谈,把他们说成是好像仅仅是一个总名叫做中国的民族;但不管从外表得出怎么样的结论,帝王从未忘记其间真正的差别。他貌似十分公正,内心却保持民族习性,一刻也不忘记他权力的来源。
这段描写,说明马戛尔尼的观察十分深入。儒学是清代皇子们的主要教材,朝廷有着大量的汉官,以儒学为核心的制度与文化保留下来了,并有所发扬;但满汉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相合的、融洽的。他指出,汉官穿的是满服,在满服之下跳动着压抑的心。最为精彩的是对乾隆皇帝内心世界的描写,即貌似公正,内心中却努力要让满族官员和士兵保持“国语”“骑射”的传统精神。由此,马戛尔尼又写道:
中国人现正从他们遭受的沉重打击下恢复,正从遭受鞑靼政治蒙蔽下觉醒,开始意识到要重振他们的民族精神。微小的摩擦可以诱发火花,将造反的火焰燃遍全中国。事实上帝国已发展到不堪重负,失去平衡,不管它多么强大有力,单靠一只手已不易掌控局势。(第24、27页)
此时正值清朝的全盛期,马戛尔尼却看出了“不堪重负”的内相。他所预料的全国性的反叛,虽然没有立即发生(一直到五十多年后,才发生“太平天国”叛乱),但清朝政治局势有着很大的不安全性,却是真实存在的。乾隆皇帝对此一直有着内心的警惕。
关于风俗与品性,马戛尔尼写道:
根据中国人的观念,一户家庭只有一致的利益,其他的想法都是非自然的和不道德的。不孝之子是中国不生产的怪物;儿子即便在婚后仍大多继续住在父亲家;家庭的劳动都是在父亲的安排下共同进行,父亲死后长子往往保持同样的权威,继续与他的年幼兄弟维持同样的关系。
即使上层的百姓,尽管喜欢衣着,一天总要换上几件,但他们的身子和习惯仍邋遢肮脏。他们外面的新袍用不同色彩的丝美饰(最高层的衣袍绣有金色的龙),而普通的衣服则用素丝,或者细黑呢;但他们的汗裤和内衣(根据季节他们一般穿几种)并不时时更换。他们不穿纺织的袜子,而用粗棉布裹足,经常穿上一双没有后跟的黑缎子靴,但靴底将近一英寸厚。在夏季,人人一把扇子在手,不停挥扇。他们很少穿亚麻或白布衣,他们穿的极其粗糙,洗得不干净,从不用肥皂。他们难得使用手帕,而是任意在室内吐痰,用手指擤鼻涕,拿衣袖或任何身边的东西擦手。这种习惯是普遍的,尤其恶心的是,有天我看见一个鞑靼显贵叫他的仆人在他的脖子上捉骚扰他的虱子。(第8-9页)
对于此类风俗与品性的观察,每个人都有可能得出相同、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来。此中最为重要的是,马戛尔尼将此作为他观察的重点和起点,是他私人日志的开篇。他对此留有大量的记载,有些他认为是好的,有些他认为是不好的。
马戛尔尼使华是一次重大的事件,对此的研究仍未到达“止于至善”的地步。牛津大学的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教授正在重新研究这段历史,也发表了论文。她去年(2017)秋天到华东师范大学访问,我们有着愉快的交谈。她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关于马戛尔尼使华,清朝的官员是否留下了私人的记载?我一下子被问住了。脑中快速搜索一下,感觉是没有。于是我开玩笑说,当时的官员,喜欢写诗,大约都会出版他们的诗集,而不太会出版或保存他们的书信和日记之类的私人文件。
关于马戛尔尼使华,清朝档案中有着非常详细记录,当时的奏折和上谕是完整的;但负责接待的官员,对此似乎皆无私人的记录。我需要特别提到两位高官:一位是和珅(时任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诗写得不错,还真的出版了他的诗集;另一位是松筠(时任军机大臣、户部侍郎),曾任伊犁将军,也有一些西北史地与治理方面的著作,但却没有留下此次接待的记录,尽管他是陪同马戛尔尼从北京一路到广东出境的官员。
马戛尔尼到达时,清朝正值“康乾盛世”的顶点,平定了准噶尔,打退了廓尔喀,兵锋直入缅甸。乾隆皇帝有着“十大武功”,疆域扩至最大。他的怀柔政策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热河分别为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修建了普陀宗乘之庙和须弥福寿之庙,并用了万两黄金做了金顶,尽管八世达赖喇嘛未到。在此文治武功之下,乾隆皇帝张扬着豪情,显示出壮怀,君臣上下似乎没有将英国放在眼里。关于马戛尔尼使华的中文资料和档案是相当多的,但其中基本上没有关于海洋和英国的知识——清朝人不了解马戛尔尼是怎么来的,也不想了解马戛尔尼所在的国家——他们没有兴趣,而最为关注者,是“下跪”。

《海录校释》,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安京校释,商务印书馆·中国旅游出版社,2016(资料图/图)
谢清高与《海录》
最能代表这一时期中国对于外部世界知识的,当推谢清高的《海录》。这本书的产生就是一个故事。
谢清高(1765-1821),广东嘉应州(今梅州)人,可能识字,也有一定知识。早年随商人到海南岛等处从事贸易,18岁时遇风覆舟,被外国人救起。于是随外国商船航行于东南亚、南亚以至于欧洲等地。据其自述,十四年之后才回到广东,此后住在澳门,为铺户。但亦有资料说明,他于1793年前已双目失明,生计困难。这样的话,他的海上生涯可能不到十四年。1793年,正是马戛尔尼到华的那一年。时光又过了27年,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举人杨炳南到澳门,遇到了这位同乡,将其见闻记录下来。
《海录》大约19000字,共记录93个国家和地区,涉及亚、非、欧、美、澳五大洲,没有地图。
最初读到《海录》时,还是我在读研究生时,关心的是其中的欧洲和美洲国家,共计17个:大西洋国(葡萄牙)、大吕宋国(西班牙)、佛朗机国(法国)、荷兰国、伊宣国(比利时?)、盈兰尼是国(瑞士?)、亚哩披华国(汉诺威?)、淫跛辇国(神圣罗马帝国?)、祋古国(土耳其)、单鹰国(普鲁士?)、双鹰国(奥地利)、埔理写国(普鲁士?)、英吉利国、绥亦咕国(瑞典)、盈黎吗禄咖国(丹麦)、咩哩干国(美国)、亚咩哩隔国(巴西?)。许多国家现已无法对应,很可能是葡萄牙语+英语+粤语+客家话,多次转音之后,无法对全。其中描述比较详细的,是两个国家:一个是葡萄牙,另一个是英国。谢清高所上的外国商船,很可能是葡萄牙船,又长期住在澳门,对其熟悉自在情理之中;而对于英国,是其国力与财富给谢清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海录》中英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由此看看马戛尔尼所来的“英吉利国”,《海录》的记载为:
英吉利国即红毛番,在佛郎机(法国)西南对海,由散爹哩(Saint Helena,圣赫勒拿岛)向北稍西行,经西洋(葡萄牙)、吕宋(西班牙)、佛郎机各境,约二月方到。海中独峙,周围数千里。人民稀少而多豪富,房屋皆重楼叠阁。急功尚利,以海舶商贾为生涯。海中有利之区,咸欲争之。贸易者遍海内,以明呀喇(孟加拉)、曼哒喇萨(马德拉斯)、孟买为外府。民十五以上则供役于王,六十以上始止。又养外国人以为卒伍,故国虽小,而强兵十余万,海外诸国多惧之。
海口埔头名懒伦,因口入,舟行百余里,地名论伦,国中一大市镇也。楼阁连绵,林森葱郁,居人富庶,匹于国都,有大吏镇之。水极清甘,河有三桥,谓之三花桥。桥各为法轮,激水上行,以大锡管接注通流,藏于街巷道路之旁。人家用水无烦挑运,各以小铜管接于道旁锡管,藏于墙间。别用小法轮激之,使注于器。王则计户口而收其水税。三桥分主三方,每日转运一方,令人遍巡其方居民,命各取水。人家则各转其铜管小法轮,水至自注于器,足三日用则塞其管。一方遍则止其轮,水立涸。次日转别一方,三日而遍,周而复始。
其禁令甚严,无敢盗取者,亦海外奇观也。国多娼妓,虽奸生子必长育之,无敢残害。男妇俱穿白衣,凶服亦用黑,武官俱穿红。女人所穿衣,其长曳地,上窄下宽,腰间以带紧束之,欲其纤也。带头以金为扣,名博咕鲁士。两肩以丝带络成花样,缝于衣上。有吉庆,延客饮燕,则令女人年轻而美丽者盛服跳舞,歌乐以和之,宛转轻捷,谓之跳戏。富贵家女人无不幼而习之,以俗之所喜也。军法亦以五人为伍,伍各有长。二十人则为一队,号令严肃,无敢退缩。然惟以连环枪为主,无他技能也。其海艘出海贸易,遇覆舟必放三板拯救。得人则供其饮食,资以盘费,俾得各返其国。否则有罚,此其善政也。其余风俗大略与西洋(葡萄牙)同。土产金、银、铜、锡、铅、铁、白铁、哆啰绒、哔叽、羽纱、钟表、玻璃、呀兰米酒,而无虎豹糜(麋)鹿。(第258-259页)
虽说《海录》对于英国的记载已是最为详细者,但总字数不足八百,故全录之。段落是我分的。第一段讲地理位置与国家特点,第二段讲伦敦,第三段讲习俗、军队与出产等项。以我们今天的英国知识,可以对证出许多内容,甚至可以查明“三花桥”的桥名;看到英国“急功尚利”品性、富家女子幼年习舞的风俗,自可会心一笑;但对十五至六十岁人民“供役”制度、伦敦三天一循环的“取水”规定,无法准确了解;而英国司法制度致使“无敢盗取者”,军队“以连环枪为主,无他技能”,应属错误知识;所言英国“土产”,只是说明了英国可以提供的商品,许多种类并不产于英国。至于那条“由散爹哩(Saint Helena,圣赫勒拿岛)向北稍西行,经西洋(葡萄牙)、吕宋(西班牙)、佛郎机各境,约二月方到”的航线,对照马戛尔尼使团的回程,从圣赫勒拿岛到朴茨茅斯,确实是要两个月(1894年7月1日至9月6日);所称“西洋”(葡萄牙)和吕宋(西班牙)很可能指他们的殖民地。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仅凭这二十余字是无法将船开到英国的。同样,对于当时一个完全没有外部知识的中国人来说,以此不足八百字的短文,还是无法了解英国的。
至于其他国家,《海录》的介绍就更短了。如“埔鲁写国”,其文为:
埔鲁写国又名吗西噶比,在单鹰之北。疆域稍大,风俗与回回同。自亚哩披华(汉诺威?)至此,天气益寒,男女俱穿皮衣,仿佛与中国所披雪衣,夜则以当被。自此以北,则不知其所极矣。(第252页)
“埔鲁写”从读音来看,指普鲁士,《海录》中的“单鹰国”,亦指普鲁士,此处似指普鲁士的北部地区或东普鲁士。这位广东人对该国的唯一感受就是冷。至于“风俗与回回同”一句,也是很难让人理解的。
这几年,我比较注意《海录》中关于东南亚国家的记录,比如今天的马来西亚,《海录》中记录了8个国家和地区:吉兰丹国(吉兰丹)、丁咖啰国(登嘉楼)、邦项(彭亨)、旧柔佛(新山)、麻六呷(马六甲)、沙喇我国(雪兰莪)、新埠(槟榔屿)、吉德国(吉打)。关于“新埠”(槟榔屿),其文曰:
新埠,海中岛屿也。一名布路槟榔,又名槟榔士,英吉利于乾隆年间开辟者。在沙喇我(雪兰莪)西北大海中,一山独峙,周围约百余里。由红毛浅顺东南风约三日可到,西南风亦可行。土番甚稀,本无来由(马来)种类。英吉利召集商贾,遂渐富庶。衣服、饮食、房屋俱极华丽,出入悉用马车。有英吉利驻防番二三百,又有叙跛兵千余。闽、粤到此种胡椒者万余人。每岁酿酒、贩鸦片及开赌场者,榷税银十余万两。然地无别产,恐难持久。凡无来由所居地有果二种:一名流连子,形似波罗密而多刺,肉极香酣;一名茫姑生,又名茫栗,形如柿而有壳,味亦清酣。”(第81页)
槟榔屿是当时英国在远东最重要的殖民地,随着远东航线的扩展,这个港口城市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在英国人到达之前,华人先已到达,英国人大量招引华人以发展经济。大约在谢清高到达时,当地的华人数量很可能达到万人,但主要不是种胡椒,很可能从事以胡椒为主的香料贸易行业。谢清高称其“地无别产”,属实,但判断“恐难持久”,则是完全相反,他完全不了解处于国际航线上港口城市的特殊性。槟榔屿在整个19世纪一直有着非常强劲的增长,直到后来新加坡取代了它的地位。不久前,我曾访问该地,仍能感受到历史脉博之跳动。而该地给谢清高留下深刻印象的,又是两种水果,榴莲与芒果,分别称其“香酣”与“清酣”。
如果以谢清高的《海录》与当时英国对于远东的知识相比,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差距。问题又出在什么地方?
当时的中国并不是不能获得外部知识。传教士的东来,曾将大量的地理学知识传入,最为著名的是明末的《坤舆万国全图》(1602年,明万历三十年)和《职方外纪》(1623年,明天启三年),清初亦有南怀仁的《坤舆全图》(1674,清康熙十三年)。清朝雍正年间禁教之后,北京还留着一个俄国东正教教士团,清朝若想通过这一渠道了解外部知识,也还是可以的。
至于民间的知识,今天更是难以想象其巨量。从明代开始,福建人大量下南洋,遍布各地的妈祖庙,说明了他们的行踪。到了清代,在东南亚的许多地方,华人建立起贸易的网络,从事着农业、商业、服务业等行业。马戛尔尼使华时,在巴达维亚(雅加达)、马尼拉都看到了华人,大量的中国商船航行于马尼拉、邦加(Bangka)和巴达维亚等众多港口之间。然而,这些牵涉到数十万、数百万人生计的“本事”,并没有上升到国家的“知识”体系之中。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有着许许多多个“谢清高”,他们的头脑中有着许多外部知识,但官家与学人没有(或很少)去了解或想去了解。当谢清高向杨炳南讲完他的故事,第二年便死去了。
在世界全球化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外部知识——当时英国等国最为看重的知识——在中国却不为朝廷所重,也不为当时读书人所重。在当时甚至此后的中国最重要的知识机构(官方的、半官方的或民间的)——如北京的翰林院、天津的问津书院、广州的学海堂等等——看不到“夷人夷事”的学习与研究,也不闻马戛尔尼之使命。在“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么一个庞大的建构之中,竟然找不到这类知识可以搁置的位置。《海录》所能提供的外部知识虽然是有限的、不准确的,却是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其出版也没有引起很大的关注,很可能只是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到了鸦片战争时期,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东发现了这本书,并向道光皇帝报告道:
当查《海录》一书,系嘉庆二十五年(1820)在粤刊刻,所载外国事颇为精审。其英吉利条下云:‘周围数千里,人民稀少,虽娼妓奸生子,必长育之,无敢残害’等语……”(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林则徐集·奏稿》,中华书局,1965年,中册,第680页。林则徐的目的是向道光皇帝报告是否有“夷人”在广东、福建收买“内地年未及岁之幼孩”,林对此报告称“访查实无此事”。)
对于这本如此简要的著作,做出“颇为精审”的评价,可见林则徐的无奈——找不到更好的记录。此后,魏源编著《海国图志》,依然需要参考《海录》的记载。在这样的知识基础上,在马戛尔尼使华四十七年之后,1840年(道光二十年),清朝因鸦片的非法输入而与英国展开的外交和兵战,只能是失败。
历史向下走了过去,清朝的出使大臣(公使)也到达英国,先后有郭嵩焘(1875-1879在任)、曾纪泽(1879-1886在任)、刘瑞芬(1886-1890在任)、薛福成(1890-1894在任)等人。根据总理衙门的要求,他们都有着相应的关于航海和英国等国政情的记录。(可参见郭嵩焘:《使西纪程》;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刘瑞芬:《西轺纪略》;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这些记录,尤其是最初郭嵩焘的记录,引起了国人的愤怒、惊异、暗羡,由此而求知,开始了国人“走向世界”的历程。然而,这些记录与马戛尔尼的《私人日志》相比,在知识的水准上又是如何?——尤其是薛福成的记录,任期恰与马戛尔尼相差一百年——两相比对,不由感慨良多。
1793年马戛尔尼来华时,清朝与英国之间的贸易量已达到相当高的数量,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双方的主要差距在于知识。此后清朝虽然过了近半个世纪比较太平的日子,但知识的差距越拉越大。再往后清朝在军事上败于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在外交上败于英国、俄国、法国、日本和德国,牺牲了许多生命,损失了重大权益,付出了巨额赔款,割让了大片土地。如果细究其中多次失败原因,最主要的因素之一是知识的差距。这些都是血肉、利益、金钱、疆域换来的教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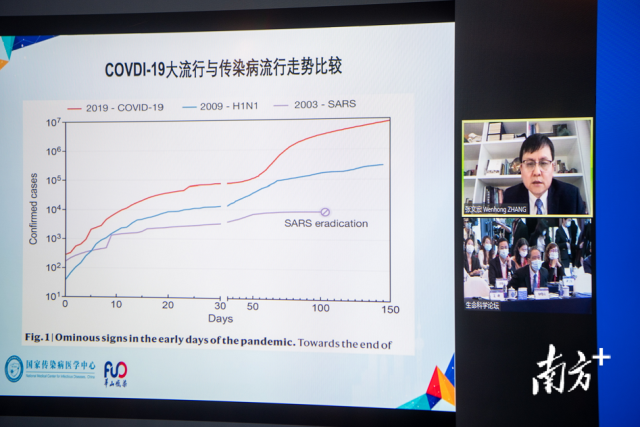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