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殡葬师:我5岁起清洗人骨,长大后帮父亲的遗体化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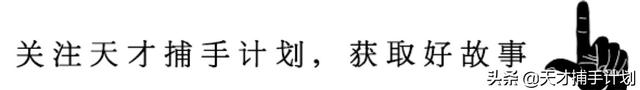
大家好,我是陈拙。
你会不会原谅一个整天叫你去死的人?
这是网上的一个问题,下面总共有一百多人回答,其中有条评论让人印象深刻——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怎么活是自己的事儿,就算再落魄,怎么死也绝对不容他人干涉。
可据我了解,有个职业就是整天教导人怎么去死。
他们是临终关怀义工,帮助那些生命走到尽头的人,尽可能的接受死亡,体面的离开。
我有一个朋友叫谢八楼,他就是干这个的,经常被帮助对象感谢。他却告诉我,有个女人比他更懂死亡:这个女人出身在坟场,五岁开始就被爷爷带到井边清洗人骨。
三十岁之后她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和活人说说话。

今年4月底,我来到了“死亡咖啡馆”。
那是闹市的一处天台,有很多大伞和白色桌椅,能看见周围明媚的天空。
其实,“死亡咖啡馆”不是一个场所的称呼,而是活动的名称,一个属于我们临终关怀义工的活动,每个月一次,专门分享死亡话题。
我们这种义工,帮人缓解死亡的痛苦,见过了太多人死的过程,难免对死亡不断有想法,不分享出来会憋出病的。
4月底的那次,“死亡咖啡馆”被哀伤的氛围笼罩,一共来了14人,仿佛真的沉浸在生死离别中。
这时,我们被要求围坐一张桌子,闭上双眼。有人扮做死神,要随机带走在座的某个人。
我听见脚步声从桌子那头响起,慢慢向我靠近,又走远,突然停住。我睁开眼睛,发现被选中的是我正对面的一位大哥。

“死神”居然哭了,对大哥说,自己很愧疚,但不得不这么做。大哥却笑了,安慰“死神”,你选的对,我这辈子很圆满,没有遗憾了。
他声音低沉,看起来大约四十来岁,留着寸头,有些发福,穿浅色T恤和牛仔裤。
我想起来,我们之前一起做过服务,他似乎对死亡早已习惯,无论怎么样惨烈的场面,永远是最平静的一个。
活动结束后,我特意去打听大哥,小伙伴却疑惑地问我,“大哥?没有这个人啊!”
我真是汗毛都立起来了,难道见鬼了?
反复确认了几次,我才知道,这根本不是什么大哥,而是一位大姐,大家都叫她菲姐。
菲姐是一位殡葬师,这行里女人属于凤毛麟角。
没有哪个女人比她更懂死亡,从四五岁开始,她就认识了太多尸体,除了同行,很多外人都有些忌讳她。
她说,现在之所以来做临终关怀,是想和活人多说说话。
(以下内容来自菲姐口述)

我离死亡最近的一次,是在24岁。
那天我躺在医院,感觉有很多人围着我,还有叮叮当当,金属碰撞的声音,然后我就失去了意识。
没过多久,我醒了,感觉身体特别轻松,走下床,就像飘起来一样。
我走到了诊室,爸爸妈妈也在这里。他们和医生好像在争论什么,我模模糊糊听见了几句。
医生告诉妈妈,我病危了,要签一下知情同意书。妈妈就坐在那里哭,爸爸在旁边催着妈妈,回家做饭。
“我们回家吃饭就行了,她不会死的。”
这时我才发现,怎么没有人注意到我。
事实上,当时的我仍然躺在病房里。我也说不清楚这种感觉是不是幻觉。
有一种生理现象叫“既视感”,简单来说,就是在现实中碰到自己虚构过的场景时,自身就算没有经历过,也会感觉好像曾经发生过。
我的爷爷奶奶都是天主教徒,我从小就耳闻目染各种灵魂出窍的说法。我只能这样和别人去解释。
我当时得了肝病,禁食了快一个月,瘦得只剩70斤,差点死了。后来因为转院,才被救活。
这一次濒死的感觉让我记了很久,虽然不舒服,但也有直接的好处——我不再惧怕死亡了。所以,后来我成为一名殡葬师,也没有什么害怕的。
在这一行,不害怕只是最基本的门槛,还要不怕苦不怕穷。
我们这里一天差不多有200人去世,不同的人要准备不同的寿衣、骨灰盒、花圈等等。
要和别人抢单子,一来活儿,不论几点都得抓紧时间跑来跑去。这么累,收入也只比其他行业略高一点点。
再加上我听人说,很多主家对女孩子来做殡葬,多少有些避讳,因为女性属阴,不吉利。
但我没有碰到过,很多时候,葬礼都快办完了,主家才发现我是女性。按八字来说,我有七字属阳。
就我认识的同行,起初还有三分之一的女性,但很多两三年就不干了,现在我都遇不到女性同行。
我却一干就是16年。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死亡,处理死人是我们家的传统手艺。

我的爷爷是新加坡人,奶奶是马来西亚人。当年为了躲避战争,搬到广州一个叫做淘金坑的地方。
淘金坑在今天是市中心,离火车站不远。据说曾有一所孤儿院,院后是一个专供弃置死婴的“死仔井”,大约有四万名婴孩埋葬在这里。
除了孤儿院,著名的黄花岗烈士陵园、十九路军陵园都在附近,总之当年就是城郊的坟地。
爷爷是神父,从我出生开始,一大家子都住在教会分给爷爷的大院里。
那是一个足足有400平米的院子,过了门厅,两侧依次排开大小屋子。
再往里走,是一座小花园,正中打了一口井,井口比寻常的大出一倍。水井旁边,有一道通向院外的水渠,平时总能看见家里人蹲在这里洗衣服。
我1972年出生,还不到5岁的时候,就常常在这个水渠里清洗死人的骨头。
附近山丘上埋着修女和部分教职人员,就被教徒说成圣山。如有需要,爷爷会去山上收拣灵骨,并帮忙清洗收放好,以便家属把他们带走。
广州的春天非常潮湿,有一些骨头会起菌斑,长出白白的长毛,我负责清洗这些菌斑和长毛。
我半蹲在水渠旁边,一手拿着把一尺来长的长柄软毛刷,另一手握住一块泛白的骨头。抬起一端,浇上一些水,轻轻地从上往下刷。

骨头埋得久了,难免比较脆。所以在洗完之后,需要放入大笸篮里。大笸篮由竹篾编制,很浅。再找一处太阳不能直接照射的半阴地,把笸篮放好,晾晒骨头。
我并不害怕这些人骨。我们家里很穷,我一直都惦记洗完骨头后,教友为了感谢爷爷,请我们一家子吃好吃的。
直到5岁,村里一位91岁的老婆婆去世,让我第一次见到了不是骨头的死人。
婆婆盖着被子,躺在殡仪馆里,我盯着她的脸,脊背有些发凉。
她的肤色太白了,涂着腮红,面无表情,不像睡着的人,显得诡异。七十年代,化妆的女性都很少,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张脸,那种恐惧一直伴随我上中学。
上中学后,我开始越来越像男孩,总是和人约架,地点就在十九路军陵园。
我也在黄花岗和别人“打擂台”,谁赢了谁就是大哥。这些年,很多时候都是我当大哥。
上高中后,我听说有人在打架中被捅了一刀,意外身亡。
5岁时在殡仪馆看到的那张脸,又出现在了眼前。在那种莫名的恐惧下,我下定决心,再也不打架了。
那时候,淘金坑的老宅也被拆掉。我们搬了家之后,老宅那边盖起了殡仪馆。之前很多熟悉的叔叔伯伯们,都去了殡仪馆工作。
现在想来,我一路成长都和死亡走得太近了,似乎是命中注定要做殡葬。

在那个年代,一个女人选择殡葬行业,多少不是个循规蹈矩的女人,我从小就和别的女孩不一样。
我们家有严格的家规,由于是村里唯一一家外姓人,小时候爷爷在屋外画了一条“三八线”,家里的孩子只能在线里活动,放假的时候也不能出去找朋友们玩。
越界了就会被打手心。
但我有办法,我会利用上下学路上的时间,带着表弟和朋友们翻到旁边别墅的院子里,摘果子吃。
那时候的我,带着一顶草帽,也不穿上衣,斜挎一个灰色的单肩布包。
后来老师看不下去了,把我叫去,“阿菲,他们几个是男生打赤膊,你女孩子怎么也跟着学?”
到了四五年级,我不再留长发,转而剪成寸头,此后四十多年就再也没留回去。
再长大点,我发现我不仅仅是性格很像男孩,也像男孩一样喜欢女孩。
于是我找了一个女朋友。父母知道以后非常生气,毕竟我们家很传统,加上信教的原因,我简直是离经叛道。
况且,在那年代,同性恋还在精神病诊断中,外人看我的眼神,都是“这孩子脑子有毛病”。
我还不懂什么是同性恋,但我知道我脑子没有问题。既然这样,只要我去和男孩子谈恋爱,就可以让他们认可我了。
我找了个男朋友,没想到没多久,怀孕了。得知这件事情,男友跑得没了踪影。
我本来想去打掉孩子,可晚上突然做了个梦,梦里一个陌生面孔的孩子蹲在地上大哭,我想走近看看,却怎么也接近不了。
我感觉,这可能是我的孩子。我心软了,“放心吧,我不会不要你的。”
起初,未婚先孕的事被家里知道后,爸爸就很生气,这会儿听说我又要把孩子生下来,他把我从家里撵了出去,还在亲戚间放了狠话。
“我要和她断绝关系,看你们谁敢管她。”
1992年,我的大儿子出生了,可母子却没地方安家。我没有办法,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只能厚着脸皮,带着孩子流浪在各个亲戚家。
亲戚也不是很待见我,很多时候外出回来,就能看见自己晾晒的衣服跌在地上。开始我还以为是大风吹落的,捡起来,重新晾了回去。
可没几天,更多的衣服都掉在了地上,还有一些原本是放在房间里的衣服。我这才明白,这是变相地赶我走。
有一次,我在姨妈家住,突然接到电话,是父亲的声音,开口便是质问,为什么要勾引姐夫?
父亲说,姨妈找他告状了,因为姐夫在家的时候,我洗澡不关门。
我感到了莫大的委屈,去和奶奶诉苦。奶奶一听就不干了。“可以把你赶出来,但怎么可以这样子侮辱人?”
奶奶带着我去讨要说法,可她是亲家的长辈,姨妈那边根本不理会。见奶奶来敲门,隔着门说,自己今天不方便,没空招待她。
转了好几家,竟然一家门都没进去。奶奶后来叹了口气,对我说:“你就在我这里吧,不要到别处去了。”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奶奶离死亡也不远了。

和奶奶一起住的时候,我自己出去打工,成了一名采购员。
因为业务发展得好,短短一个多月间,我的职务连升三级,从普通文员成了采购主任。
奶奶没多久生病去世了。同一年,我遇到了张先生。他是个务实又善良的人,父亲是钢铁厂厂长,家境优越。起初我们只有业务上的往来,慢慢的,他开始追求我。
亲戚们知道了都很高兴,还有人私下提醒我,不要轻易把带孩子的事情透露给对方,这么好条件的对象,能找到不容易。
但是我没听,很快就把自己是未婚妈妈,以及还带着孩子的事实,告诉给了对方。我觉得,瞒得了初一瞒不过十五,不如早做打算。
没想到,张先生没有被吓跑,反而接受了这个事实,一定要和我在一起。我也渴望有一个温暖的家,就同意了。
我们的婚礼在一家五星级酒店举办,十分热闹。新郎和长辈们都很开心,只有我,真的进入婚姻后,除了疲惫,居然没有任何感觉。
有一张婚礼的照片,新郎和长辈们都在望向镜头,我这个新娘却心不在焉,眼望另一边。
那天的嘉宾们很少人知道,我肩上那蓬松浓密的长发是一顶假发,假发之下,是留了足足十八年的寸头。
婚后,我做起了全职太太,丈夫上班赚钱养家。小儿子出生后,我的生活重心全部放在带孩子上。
每天,我先是送大儿子上幼儿园,又时时刻刻看着小儿子。等他睡着了,再急忙出门,买菜做饭。
我没有了社交,每天的交流就是和孩子、丈夫。我感觉自己像一只轮子,围着孩子围着厨房围着家转动,可我从来没有绕着自己转。
最多,也就是下楼打打麻将,仅此而已。
我经常会问自己,这一天快乐吗?本该是快乐的。因为在别人口中,有爱你的丈夫,富裕的家庭,健康的孩子,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吗?
而且,这也是我之前在流浪时,梦寐以求的安稳生活。
我说不上来缺少了什么。
有天晚上,我和丈夫久违地亲热了一下,正在兴头上,突然听见丈夫问我:“这个月水电费交了吗?”
我突然兴致全无,好像被冷水从头浇到脚。我停了下来,没说话,翻了个身。
就在这一刻,我决定离开。

丈夫没有同意离婚,他说,我可以搬出去,两人分居,我想什么时候回来,都可以。
出乎意料,这次爸妈也没有反对。也许在他们看来,我已经结婚生子,尽到了一个女人的义务。
我离开家后,首先要面临的问题,就是找工作养活自己。
这一年是2005年,婚后的第5年。也是从这年开始,国家允许私人资本进入殡葬行业,当时,整个广州只有寥寥几家和殡葬相关的单位机构。
冥冥之中,这就像是为我准备好的。这些年来,我经历了太多活人之间的纠缠,和死人打交道反而自在,我打算就干这个。
我来到了一家丧葬公司,从销售开始做起,每天都根据公司的要求出门跑业务。
死亡是不会挑时间的,只要电话一响,我就得迅速抖擞起精神,因为收到的信息很可能不是独一家。
这个城市一天会有多少人去世,在行业内都不是秘密。我要用最快的时间去和别人抢生意,才能拿到相对高一点的工资。
很快,我就积累下来很多经验和人脉。我给领导提建议,与其把殡葬店开在殡仪馆,不如开在医院旁边,更接近市场。
但领导觉得维持现状就好,我那样太冒险。
我想来想去,决定自己单干。
在一家三甲医院前,我看到一家童装店正在转租。老板说,也不知道为什么,前些年店里生意还可以,今年一下子就不行了,这才想找人接手。
我告诉他,斜对面200米就是太平间,这生意能好吗?
盘下店铺后,我又和医院的运尸工夫妇商定,夜里两点到五点离世的病人信息,优先发给我,“只要你们把信息只给我一个人,别人给你们100元,我给200元。”
过了段时间,我的店铺装修好了,虽然只有十来平,东西可不少。
一进门,正中间摆一张方桌,供奉地藏王菩萨。上面是一副对联,法事师父提的,白纸黑字。

两侧是架子,左侧是成套的寿衣,红色挂在最外面,新潮一点的放里面。因为越是高龄,款式越朴素,只不过是颜色会鲜艳一些。
右侧的架子,从下到上是大小不同的骨灰盒,最下面最精致,最上面最普通的。
我的店里有两种套餐,普通的4990,豪华的7990。从人去世后,到联系殡仪馆、化妆、布置灵堂、法事超度、骨灰装殓、烧纸这些,我都可以管。
一般人不太会计较价钱,很少有还价的,但我也碰见过,火化完家属不给钱的。
那是唯一一次,我只能打电话和他们说,骨灰现在在我手上,你们觉得我会怎么做呢?这样,我才收到钱。
我还接到过和小时候洗骨头一样的委托。
以前,很多装骨灰的都是瓦罐,埋得久了容易破损,有家人委托我,帮他们换个骨灰罐。
我拿了铁锹去坟地,刚下几铲子,就发现情况不妙。
骨灰罐早破了,泥土里混着骨灰,还有细碎的骨头。我拿着小灯,蹲在坟里,捡了几个小时,连带着泥土,挖了一大袋带回家处理。
就这样,连带着医院的信息源,我每个月收入稳定,日子又好了。紧接着,我遇见了心爱的女人。

那天晚上,我下班后,去了一家清吧放松。
店里很冷清,我数了数,就三张桌子有人,一共六个。于是我组织大家,凑在一起喝。
我们六个直到现在都是好朋友,其中一个女生,不在意我的工作,也不在意我的过往,成为了我的女朋友。
我们感情很好,只不过,我在广州,她在重庆,于是我关了小店,一起去了重庆。
准备走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有天凌晨四五点,我被手机惊醒。有信息说,医院有病人走了,家属们都还在现场,要我去处理一下。
中途,我经过一处低矮的民房,听到屋里有人在嚎啕大哭,声音悲愤委屈,难以形容。我也没空去看,匆匆赶到医院,见到了对方的家属,但没谈拢,又回来了。
那时候,民房已经围了一圈人,警察也来了,有人猝死在这里。
我挤到了人群之中,看到了死者的亲属,凑过去递了一张名片,让他有需求,可以找我,随喊随到。
几个小时后,死者的哥哥来了,是一个满脸愁苦的中年人。
见到我,他就开始倒苦水,说死者是家里最宠的孩子,现在喝酒喝死了,不敢通知父母。
我也没多想,帮他办了后事。但诸事办妥后,当哥哥的却消失了。我捧着逝者的骨灰盒,不知道该怎么办。

当哥哥的换手机号前,回了最后一条信息,“老师行个方便,随便找个什么地方埋了干净,我自己一摊子鸡毛蒜皮,还不知道怎么跟爸妈说。”
我哭笑不得,只能悄悄把骨灰盒埋在白云山,身份证、火化证都放盒子里头了。事后,我去了重庆,这些年都不敢换电话号码,就怕哪天死者会打电话寻回骨灰。
在重庆这些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候,我和女朋友住在一栋别墅里,一年只有一半时间工作,经常宴请朋友,或是外出游玩。
我和她都分别见了家长,我的孩子们也知道我是同性恋,却都坦然接受了。
我从没有想过,这种快乐终有结束的一天。
2016年1月,女朋友要去趟美国出差,需要从白云机场转机,我就陪她回了广州。
在机场的时候,女朋友依依不舍,要再陪我一会儿。我却和她说,来日方长。
没想到,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那年春节前,广州百年难遇,下了一场雪。当天,我收到了一条跨洋来短信:“我们分手吧”。
11年的感情,就在短短几个字中结束了,甚至连一通电话都不愿意给我打。
我有些喘不上气,只感觉冷,就像外面的雪一样冷。

转眼到了五月,一位老朋友来看我,她说我气色太差了。能不差吗,我这几个月一直很消沉,天天在家念经。
她推荐了一个读书会给我,劝我去调整放松一下。
说来也巧,除了我,其他五个都是有心理咨询从业者。就这样,读书会变成了我的心理陪伴会,都在开导我。
从2016年5月到2018年10月,我在这些朋友陪伴下,开始回顾自己的人生。
我从小离经叛道,后来的工作也不被多数人待见,是一条少有人走的人生道路。但我好像从没有感觉到,自己被边缘化。
我最先想到的是感谢公公婆婆。我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外表完全男性化,就算走进男厕也不会有人发现。但公公婆婆都没有嫌弃我,他们从没说过什么。
他们还常带着我一起,去亲戚家拜年。按照广州的风俗,已婚的要给未婚的发红包,但我却收到了很多红包,因为我总被人当做是他们未婚的小儿子。
我也不好解释,公公婆婆也很尴尬,但出了门,就像没发生过一样。
再往前,人生的第一道难关,奶奶帮我度过了,后来是丈夫、儿子、女友的陪伴,我一直想要什么有什么。
我此刻才察觉到,这么多年来,我是多么幸运,他们像接力一样,用爱把我环抱。
我也快50岁了,余下的生命里,我应该再做一些什么。
我一辈子都和死亡打交道,给主家办丧事的时候,常常看见他们痛哭流涕,想帮他们却无能为力。
后来我遇见了临终关怀的义工,原来在死亡之前,还有很多事可以做,可以帮助人。
于是,我加入了他们,去开导那些还活着的人,也用自己这么多年的经验,让临终的人不再恐惧死亡。
可是义工有义工的规则,我还没做到资深义工,不能完整跟下来一个案例,每次只能随机探访。
我找到几个小伙伴,一起成立了自己的小组,可以完整跟踪一个案例。
2021年2月,我们正在医院的阳光房里开会,突然一个焦急的身影跑了进来。
他推开门,边喘气边说,自己是社工,但是:“我快撑不下去了,案主的情况很差,救救我们。”
这就是我们小组第一个案子,一个难度超出想象的案子。

跟着社工,我们来到了一个城中村,脚下的土路,像极了小时候我住的地方。
“呼——呼——呼——”,远处突兀地传来一阵声音,像是除草机。走近才发现,竟然是从房间里传出来的。
有三台一米多高的工业电扇,开足了马力,向着屋外吹风。
我正疑惑这家人在干什么名堂,鼻子一吸,闻到了我最熟悉的味道——在尸体上才会出现的腐臭。
我吃了一惊,病人不会已经去世了吧,赶紧进了房间。
只见病人躺在床上,是个老太太,左胸前有一团黑肉,溃烂得厉害,黑色的肉芽遍布伤口崩裂的地方,已经看不出半点原来的轮廓。
因为挨近心脏,黑肉受心跳的牵动,一直在跳。
味道就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
社工告诉我,病人是乳腺癌晚期,因为家人经济情况不太好,没有钱住在医院,这才搬回家住。
家里人都很嫌弃她,唯一的诉求是让她赶紧出去。我的小伙伴们也离得远远的,不敢上前。
我心里一动,当年我也是这样被家人赶出门的,何况这是我们小组第一个案子,我一定要接下来。
我了解到,这些年负责照顾病人的,主要是她的母亲,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家,腰背驼着,有严重的腰间盘突出。
现在,老母亲视力也不太好了,有时探访过程中,她会望向女儿身侧,疑惑地瞧着那团跳动的黑肉,然后对我说:“怎么有一只老鼠在我女儿身上?”
我们决定,每周来探访一次,又联系社工找来一些止痛药,发动身边的热心人士,提供数千元的物资乃至现金。
感受到物质上的援手后,一家人坐在一起的次数也变得越来越多。
最令我欣慰的是,6月多的时候,这一家的老中青少四代人,拍了家里唯一一张全家福。
7月,病人的状况更糟了,溃烂的创口有时毫无遮挡地出现在我的面前,冲鼻的气味,发黑且夸张的腐肉,都在提醒我,她的时间不多了。
我得知,她本人的意愿,是想在家里走掉。然而按照习俗,外嫁的女子,如果死在本家很不吉利。
我想了个办法,找到了一家愿意接收她的老人院。老人院还具备一定的医疗功能,有临终病房供人入住。
这一别,她和妈妈就再没见过面,只有时通过我的手机,看看对方的相片和视频。
我听养老院护工说,有一天夜里,她突然创口大出血,鲜血如冬天崩裂水管的水,飚到床单、墙壁和医护人员身上,在场的人都吓坏了。
过了几天,我看见她的背上穿了一个肉洞,不停冒着脓血。她已经是弥留之际了。
一床之隔,她对我轻轻地点了头,已经不能像从前那样和我打招呼说,“阿菲,你来啦。”
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里她是我的邻居,有着高挺的鼻梁,皮肤的白皙,用大大的眼睛看着我。过了会儿,她问我,有没有手机?
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突然听到一阵铃声,抓过手机一看,她儿子说,就在一个多小时之前,她离开了。

就在我做临终关怀之后,我的父亲去世了。
那天晚上,我正陪他聊天。他盘腿坐着,把两只手上下叠在一起,抬起右手,在左手心上打了一下。转过头来,深深看了我一眼。
他没有说话,但我懂,这是佛教里禅定的手势,意味着平静。他是一个天主教徒,我是信佛教的,显然他是让我平静。
我再一转头,发现父亲已经不动了。他静悄悄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在殡仪馆里,我亲手给他做了遗体妆容。
很早以前我就明白,干殡葬的一定要比家属淡定。如果我有任何一份情绪在,对家属的影响都会很大。
多年养成的习惯,让我在入殓父亲的时候也是一样,非常平静。
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猛然真的意识到,父亲真的不在了。
我本来是一个对死亡没有感觉的人。我这一辈子,经历了太多死亡。对于我来说,我可以接受任何形式的死亡。
可就在父亲走后,我有些羡慕他。他跳过了从衰老走向枯萎的过程,没有老态龙钟的样子,也没有病入膏肓。
我突然知道,今后的人生要干什么了。
我一直都陪着死亡一起生活,往后大概也会是这样。如果我能活到70岁,在剩下的20多年里,我会坚持做临终关怀,然后,像父亲一样,体面地离开。
我这辈子都没学会属于女孩的温柔,但我想,如果我能以这种方式离开,不给任何人添麻烦,这就是我最后的温柔了。

谢八楼很早就想写菲姐了,但他一直不知道怎么下笔,因为即便是在临终关怀的群体里,菲姐对死亡的理解也显得独特。
我鼓励他写下来,又让他介绍菲姐和我认识。与菲姐沟通后,我和谢八楼都决定,要用菲姐的第一人称口述这个故事。
谈论死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与其让我们去理解菲姐的意思,不如让她亲口对你们说说,她作为一个最懂死亡的女人,是如何看待死亡的。
我想让你们感觉,是和她面对面聊天。如果你对死亡有什么问题,问问她,听听她,就好了。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海东青 马修
插图:娃娃鱼 六耳 花椒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