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有个迟子建

迟子建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唯一不满意的是,今年哈尔滨只下了一场小雪,也没那么冷,「这还叫东北吗?」
不管是在文学世界还是现实世界,迟子建一直笃信万物有灵,不知道是不是听见了迟子建的抱怨,哈尔滨的冬天很快有了表示,采访结束回北京的次日,迟子建发来信息,「哈尔滨下雪了,还不小呢!」
文|卢美慧
编辑|柏栎
摄影|黎晓亮
先声夺人
迟子建对世界始终是好奇的。
起先,她非常干脆地拒绝了当面采访的请求。发邮件可以,有问必答,这是多年以来迟子建对待大多数媒体采访的习惯,邮件省事,你也省得跑一趟,而且像钱钟书先生说的:「干嘛非要看看下蛋鸡呢?」
后来答应见面是《人物》记者无意中说了大学时学的是物理,迟子建好奇心上来了。最终见面的地点在哈尔滨一家东北菜馆,不知是不是永远保持好奇心的缘故,迟子建的眼睛远比一般人清亮,周围的客人陆陆续续落座,隔着一屋子的喧嚣和热菜上桌时飘散开来的水气,迟子建的眼睛放着亮亮的光,「物理?我就一下子很好奇,一个关心文学的姑娘,学物理,她是什么样的。」
这位54岁的女作家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那个非洲猪瘟控制住了没,今年哈尔滨怎么不冷呢,以至包括一个学物理的记者可能是什么样子。
真的见了面,迟子建有东北女人天然的爽利亲切,叫上几个她认为最有特点的东北菜,招呼服务员上了两瓶啤酒,「你来哈尔滨,一定要尝尝这儿的啤酒。」菜陆陆续续上桌,每一道她都能说出门道,她说你一定得尝尝东北的大米,东北的大米好啊,又说你得多吃我们东北的豆腐和鱼,「跟其他地方的,那绝对不一样。」
声音也亮,直冲冲的干脆,又很爱笑,作家阿来形容迟子建的笑声,一群作家扎在一起,「她给我的印象总是未见其人,而先闻其声。听见她在某一处和人交谈,但你总是会先于其他人的声音而听到她的。更多的时候,人还没有出现,就听见她爽朗的笑声,预告她的出现。」
就像苏童评价迟子建的故乡漠河,迟子建本人也自带一份「先声夺人」的气势,其实迟子建是圆圆的小脸,笑起来还带浅浅的酒窝,但生在北国一片苍茫之中,小家碧玉似的娇柔那肯定没有。迟子建性子里沉淀着北国的风雪,忸忸怩怩不要,羞羞答答不要,要干脆、要直接、要快刀斩乱麻,大兴安岭走出来的女人,当头的是个「大」字。
迟子建自己说,如果不当作家,她大概会是个好的农妇。写了三十几年,文坛热闹过也冷清过,迟子建倒还真像个守着时令的农妇,春种秋收,不疾不徐地维持自己的节奏。
许多年前,苏童写他眼中的迟子建,「大约没有一个作家会像迟子建一样历经二十多年的创作而容颜不改,始终保持着一种均匀的创作节奏,一种稳定的美学追求,一种晶莹明亮的文字品格。每年春天,我们听不见遥远的黑龙江上冰雪融化的声音,但我们总是能准时听见迟子建的脚步。」
2018年5月,果然是春天,迟子建出版新书《候鸟的勇敢》,这个伴着松花江上的黄昏写成的故事,讲述了在东北一座小城栖息停留的候鸟和保护它们、扑杀它们的人类之间的种种纠葛,一如既往的迟子建。
除此之外,2018年,迟子建还收获了三个语种的翻译书,分别是瑞典语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英文版的《晚安玫瑰》,还有泰文版的与莫言的一个合集。
对于自己今年的「收成」,迟子建很淡然。新书《候鸟的勇敢》除了参加了首发式,其余推广活动都推掉了,海外译本也是,出版商希望她能参加一些活动,都被谢绝了。
对外界的热闹,迟子建有本能的抗拒。饭桌上一口菜一口啤酒的间隙,迟子建说「海外翻译这一块,我觉得作家应该还是把它看得淡一点更好,别觉得多了几个语种,好像自己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作家,这个东西很容易就变成一种烟花,绚丽一时,立刻就寂然无声。对吧?吃菜吃菜,这个鱼要多吃。这个豆豉鸭也很好吃。」
不在潮流之中
30多年的写作,迟子建用超过600万字的体量建立起一个美丽与苍凉并存的文学王国,这个王国别有一番风景,于是我们在她的笔下总能看到,北国满世界的大雪,冰冻或奔涌的河流,自由自在的鱼,生生不息的树,飞鸟与野兽,鲜花或云朵,风的声音,星空的低语,清凛的月色,虽然人在烟火和红尘之中,但迟子建的笔下,「自然」一直作为永恒的背景承载着一切,注视着一切,当然也抚慰着一切。
在这面巨大的幕布之上,人间的一切,生与死,爱和恨,新生或老去,都不是孤零零存在,人生短短几十年,在自然面前不过一瞬,这是迟子建端详世界的方式。
作家梁鸿一直非常喜欢迟子建的作品,她认为迟子建最了不起的是,「她的作品具有独有的『风景』,这个风景要打引号。」梁鸿解释,「风景」是文学研究里面的一个专业术语。指的是一个内部的景观,是你如何看待这个世界,「我觉得她并不是说只是为了写异域的风景而写风景,那就没什么意思了。迟子建的书写解决了客观风景和人的生存场景之间的关系,风景要和人之间形成一种互动,形成一体化的存在,风景也是人,人也是风景,对吧,它们俩互为存在,互相彰显对方。」
出生于同样辽阔壮美的四川阿坝藏地,阿来珍视迟子建笔下的自然,「我喜欢迟子建的小说,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她的小说里面有自然,中国不少小说里只有人跟人的关系,看不到自然界。」
2015年,迟子建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的驻校作家。后来,莫言和苏童主持了一场迟子建作品研讨会。
迟子建一直不怎么喜欢研讨会的形式,「一开始我拒绝,我不喜欢研讨会,但我无法取消,因为它是规定动作,每一个驻校作家,苏童、余华、贾平凹、格非,他们都有一场研讨会在北师大,我去我也要必须(参加)。」于是这个研讨会,成为了迟子建步入文坛30年后,第一个作品研讨会。
在那个研讨会上,苏童说起迟子建作品的与众不同,「大多数中国文学的作品在看待现实时采取批判、尖锐、狠毒的方式,我们都知道这种作品容易引起注意和阐述。迟子建最不容易的是一直用美好的、温情的眼光看待人、事、物、世界。」
作家李洱和诗人欧阳江河都认为现代主义文学是在处理恶、反讽和批判的问题,北师大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张柠将之总结为「斥妄」,实质上是对人类现代文明的不满。欧阳江河说迟子建正是从这一层面努力超越,尝试从更大层面对现代文明做出评价。「美可以跟很多东西构成复义关系」,欧阳江河强调,迟子建的美跟一般的美不一样,「她把美推到极善的程度,把人性缩小,从而得以从终极意义来考虑问题。」
几年后,在哈尔滨的饭桌上,迟子建说外界的声音其实很难影响到她,当《人物》记者向她复述其中的某些观点,迟子建忽闪着那双亮亮的、黑白尤其分明的眼睛,「有吗?是不是我当时溜号儿,我怎么不记得了?」说完把筷子探向她爱吃的鱼,很是专注地享用她的晚餐。
写了三十几年,用迟子建自己的话说,「我从1983年开始写作,期间经历了新时期文学种种的潮流。我不是任何一个『主义』下的人,也不是任何潮流中的人,这种不入流,恰恰给了我自由,给了我广阔的生长空间。」
对世事人情,迟子建向来开阔,她是个喜欢独来独往的人,「不爱扎堆,人越多我可能感觉越孤独。这与我成长的环境有关吧。在一个地广人稀的地方长大,从一开始就觉得人是渺小的。世界的大潮流在我眼里是壮丽的自然界,人只是其中的涟漪。所以作为作家的我,难以入流,极其自然。」

残酷之后呢
至少在人们认定的一个渐行渐远的文学黄金时代里,中文写作的当务之急都是凝视和回望时代的伤痕,这当然是必要的,所以评论界一直有的一个声音是,迟子建的温情和暖意,会不会成为她的妨碍,阻挡她走向文学的更深处?
梁鸿觉得这是人们对文学的一个非常大的误解,「仿佛只有写残酷人生才是好的东西,这肯定是不对的。」梁鸿认为温暖这个词不应该成为文学的对立面,或是所谓的「更好的文学」的对立面。「因为温暖是人性的一个至深的东西,真正的温暖,它是人性里面最深刻的一种存在。」迟子建正是长久地凝视、书写着这种存在,「她能够在一个复杂的人性场景里面去体现某种温暖的一种可贵,和某种温暖的深刻,这非常不容易。」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郭力是迟子建长期的读者和研究者,她认为一路写下来,迟子建的写作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北中国的冰雪给予她的韧性和开阔,「在这个高寒的纬度之上,有作家对于生命的独特的体验,就是说雪国这样的一个,就是北方的洁白的这样一个雪乡,使她瞬间地在这个天地间的广阔,这种洁净,广阔的这种美,使她笔下的景物是独特的,不仅带有生命的这种悲悯,同时也带着北方的那种生命的韧性。」
大概是管中窥豹看到的那个斑点,郭力觉得温情的标签是对迟子建实在的误解和不公平。郭力认为,迟子建一直试图回答「残酷之后」的命题,这是她文学的底色。作为国内研究萧红的资深学者,郭力厌倦透了学术界反复拿迟子建和萧红作比,「其实都是在标签化一个作家,而忽略他们各自的特色。这个也是我们学术研究当中学术资源话语贫乏,这种贫乏之后,集中暴露出的这样一个窘态,学术研究的窘态,这个一定要给我放进去。」
郭力认为,其实迟子建的作品里,残酷之处比比皆是。她写《额尔古纳河右岸》,写被现代文明挤迫和围堵的鄂温克民族,写他们风雨雷电之下百年民族悲歌,日寇的铁蹄,「文革」的阴云,时代风云之下人必须要承受的残酷命运,迟子建在小说中描写了大量的死亡,死亡之密集常常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但与此同时,「残酷之后呢?」她一定把笔触延宕出去,写他们的顽强,写他们在命运面前的坦然。
「不是说迟子建她回避残酷,她不回避,生命的悲哀这些,那种大的悲痛,人性的龃龉之处,她都没有回避。」但即便生活这个样子,人间这个样子,迟子建还是爱着脚下的土地,郭力觉得这是土地、故乡和书写者关系的迷人之处,那迟子建就不可能是太过缠绵的,或是沉溺在一种情绪里,她一定能走出来,清风明月,莽莽丛林,人还是得继续过日子,「这个特别诗意,这是迟子建。」
郭力觉得文学的价值或魅力正在于此,一方面它是虚构的,一方面它又最大限度地再造了某种真实。从这一点上,莫言之于高密东北乡,余华之于浙江嘉兴,刘震云之于河南商洛,苏童、毕飞宇之于江苏水乡,迟子建之于东北雪国,「每一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
郭力说,这不是孰优孰劣,或者这个和那个为什么不一样的问题,美感恰恰在于差别和不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再一百年过去,我们回头看,怎么看一个时代的转折,我们怎么看一个几千年的传统农耕社会去结束、转型、再造和新生。这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都会是为我们留下、为后代子孙留下了中国当下的正在发生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历史记录。」
站在此时此刻,作为文学研究者,郭力内心有些描摹不清的愁绪,「因为我们真的是跨入了一个中国迅猛的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几千年的来自于农耕社会的,依托于土地的,文化的记忆,生命的感知,慢慢与我们今天现代人远去了,它是一个背影,它是一个余音。那么当文学记录这一切的时候它就呈现了文学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意义。」
故乡与童年
虽然不怎么热络地去附和外界对她的评价,但关于自己在写作中的取舍选择,迟子建在一篇文章的一段记录或许可以作为自身心迹的旁证。
迟子建的手边一定要有书,常常也要翻着书才能睡去,有天夜里她在书架上翻开前辈友人王观泉先生的赠书《欧洲美术中的神话和传说》。一幅幅画作延展出遥远的希腊神话和圣经故事,迟子建为艺术久远的生命力感动。在那篇文章中,迟子建特地摘抄了王观泉写给她和爱人的一段赠言:
此书起笔于1953年,时为23岁当大兵时。但虽戎装在身,心中想的是保卫和平,使中国乃至世界宁静。忽忽近半个世纪流逝,这才发现世界其实一点儿也不太平。书虽然漂亮,2002年垂暮之年的我已经对世道不感兴趣了,只是愿意比我年轻的你及你相似的中青年们,能如我在起笔写此书时一样好心情,赏析美。
对美最初的认知,当然来自她的家乡。迟子建写过太多关于故乡的片段,其中有一则是,「当我童年在故乡北极村生活的时候,因为不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我认定世界就北极村那么大。当我成年以后到过了许多地方,见到了更多的人和更绚丽的风景之后,我回过头来一想,世界其实还是那么大,它只是一个小小的北极村。」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常常要受制于命运。但人与自然的关系,存在某种永恒。虽然已经做了快30年「城里人」,但每年迟子建要回家乡,她需要那份滋养。
除此之外,如果我们试图解答「迟子建为什么是迟子建」命题,还是要将目光投向她的童年。除了壮美的自然教予的那些道理,迟子建是个在爱中长大的孩子。
迟子建的父亲爱喝酒,爱写字,会拉小提琴和手风琴,是一位豁达又浪漫的小学校长,她的名字是父亲取的,在1964年,大多数国人争着给孩子起名「卫红」、「卫东」、「志国」的年月,因为很喜欢曹子建的《洛神赋》,父亲给自己的二女儿取了「子建」的名字。母亲则「坚韧又慈悲」,大兴安岭半年时间都是冰雪,雪特别大的时候,母亲在房间里看着外面的鸟儿发愁,雪把世界盖住,那鸟不都饿死了么。她就隔着窗子给鸟儿撒米吃,鸟们受够了人类的捕杀,开始不愿意落脚,后来一只两只陆陆续续过来,母亲高兴得不行。
父母的诗意和善良或许能解答迟子建笔下的温润究竟从何而来,他们和北极村轮回的四季一起,给了迟子建最初的生命教育,「从小我就知道,跌倒了得爬起来继续走,所以不怕坎坷。再加上那里长达半年的冬天,冷风刺骨,你抵御大自然的寒流的能力强了,抵御人生寒流的能力自然也强了。东北话讲叫『皮实』。」
经历极寒的人会对生命中真实的温暖格外敏感,而什么该在意,什么当一笑了之,迟子建也十分清楚。
对于世俗世界给予的荣誉热闹,迟子建一直看得淡泊。她是中国文坛唯一一位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家,并且获得过一次茅盾文学奖,一次冰心散文奖,一次庄重文文学奖,一次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凭借《额尔古纳河右岸》摘下茅盾文学奖的那年,回到哈尔滨下飞机后被家乡的记者围住谈感受,迟子建脱口而出最希望的是采访赶紧结束,自己能马上回到原来的生活。
倒是2011年在北京参加活动时一份特别的礼物,她每次都愿意特别骄傲地跟外界分享,因为「迎灯」的乳名,她的读者们自称「灯迷」。2010年,来自不同城市的60位灯迷,给迟子建送上了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是本墨绿色封面的厚厚的大书,60位读者用手写的方式把20万字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抄了一遍,有心的读者还在空白处画上小说中出现的驯鹿、树木和溪流,这让迟子建喜欢得不行,她把这部独一无二的手抄本摆在书柜上,正对写字台,写得疲惫的时候,抬头就能看见。
这是迟子建写作生涯中最珍贵的礼物,其中有写作者和读者之间,最真挚的情分。
年过五十之后,常有人追着问,担不担心自己会面临创作的枯竭。迟子建真的不担心,她十分明白自己的生命的源头来自何处,又十分明白,不管是北国的风光,还是生命中收获的那些温暖和爱,都会滋养着她,支撑着她,去迎上前去,面对命运给予的一切。

自我
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日子,迟子建有时会有些自己的小顽固。迟子建至今仍不用智能手机,一个四周已经磨掉烤漆的老款三星手机已经用了十几年,「能接发短信,能联系朋友,不就够了吗?」她有微博,但也只在电脑上用,一直没有微信,对一个小小的软件营造的天涯若比邻的幻象着实没有兴趣,「生活够喧嚣的了,作家对于这个世界,既要倾情拥抱,又要有所保留,因为艺术是需要距离的。既要多听,又要少听,有意识地屏蔽一些东西,保持心灵的自由和独立。」
在科技越来越将人类大一统的当下,这样的自我常常制造一些小插曲。前年去西班牙参加文学论坛,在飞机上苏童笑她,「你等着吧,都智能时代了,你下了地面肯定没信号。」结果到了西班牙,「有信号呀。」迟子建很雀跃地描述当时的情景,可是今年到了新加坡,她的老款手机就失灵了。
前阵子迟子建去哈尔滨当地一家俄罗斯面包店买面包,一共二十几块钱,付钱的时候,俄罗斯小伙儿说,他们不收现金,只能支付宝或微信,迟子建轴劲儿上来了,跟小伙儿理论起来,「你还担心钱是假的吗?二十几块钱的面包,我至于去骗你吗?」
这很像2015年的那次研讨会上莫言对迟子建的描述,1987年,迟子建和莫言、余华、刘震云等一起进入北师大与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研究生班学习,说起来是实打实的同门师兄妹。莫言说「当年在北师大研究生班的时候,迟子建是我们小师妹,年龄很小、很高傲、脾气也很大,惹不好她会动手『打人』。」
采访中聊到这一段儿的时候,迟子建来了精神,搭配着标志性的笑声,「他那是调侃,我怎么会打人,哈哈。」迟子建接着说起属于这群作家的80年代,那时候大家凑到一起,真的会认真聊文学,不是说非要开个会讨论什么的,就碰到一起了,大家就会聊。那时莫言和余华一个宿舍,「嗯,他们的房间很有灵性,出了两位大作家。」
迟子建的室友是女诗人海男,诗写得很漂亮,她口吃,但挡不住对文学的热情,每每写完了就给迟子建朗读,「那个时代这点是值得人怀念的,文学还是生活里重要的东西。」
对80年代的怀念是文坛的一股流行风潮,失落了的理想国和乌托邦,根植在一代人的内心深处,是心口的朱砂痣,摸不得碰不得,但反复端详,始终是美的。
作为80年代走出的女作家,迟子建对群体性的抒情倒是没多大兴趣,「那就是文学的青春,无论怀念还是遗忘,它不会与我们重逢了。30年代有位歌手叫白光,她有首歌叫《魂萦旧梦》,其中有句歌词『青春一去,永不重逢』,我很喜欢。」
时值改革开放40周年,官方纪念活动中,似乎少见文学的踪影。问迟子建她对这40年中文写作的评价,干脆利落地八个大字,「大河奔流,泥沙俱下」,除此之外,也不愿多言。
过去了就过去了,没有了就没有了,日子还是要过下去,她还是要写下去。大约是骨子里沉寂的风雪发生着作用,迟子建对一切突然的热闹都抱有一份怀疑,「80年代的文学热当然不可复制,留下了一些代表性作品,当然也产生了一些泡沫,这是不可避免的。我觉得80年代我们在文学准备上并不很充分,也就是说在80年代的文学大合唱中,歌唱票友多,而真正具备歌唱家素质的不很多,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作家会歌声渐淡,后劲乏力。」
这很像经历了一场高烧,退烧之后,大体能检验出人们对文学的忠诚。
迟子建当然是忠诚的那个。在大众领域,或许那个属于文学的美好时代已然远去,但30多年下来,文学在时代的广场上热闹或是冷清,迟子建始终在那儿,「如果一开始写作,有人告诉我你会写三五十年,我会吓一跳,觉得那会是一种苦役。可是写作伴我走过30多年的时光后,我陡然发现,没有写作,我在人生的一些关隘上可能会倒下。」

图源视觉中国
「勃勃的生气」
写作是迟子建抵御人生荒寒的武器,也给了她应对命运时必须的顽强。
王安忆也说起过迟子建的笑,「我最先是从照片上认得她,那时还没看她小说呢。看照片就觉得她很会笑,她笑得那么明朗,她也不是疯笑,也不是媚笑。就是一种非常开心的笑,我觉得这个女孩长得很好看,我就觉得这个人可以写出好东西,然后我看到了她的小说。我不是说她小说写得如何完美,我就觉得她有生气,这真是叫勃勃的生气。」
但命运似乎瞅准了这个有着勃勃生气的东北女人,一定要伺机给她来那么致命的一下。迟子建刚过20岁就失去了自己深爱的父亲,挚亲的过早离场,让迟子建早早就意识到人生的苍凉。
2002年5月,迟子建经历了人生中最黑暗和残酷的一个春天,结婚不满四年的丈夫因为一场意外车祸身故,在人生中最甜美的时刻,命运一下子把迟子建推进又一场暴风雪中。
黑龙江省作家协会的办公室副主任罗纯睿在那一年前后进入作协工作,那之前,她是迟子建的读者,但在此前并未谋面。回忆第一次见面,罗纯睿记得当时在作协的一楼,迟子建穿一件墨绿色的长裙,很美,「就是眼神很忧郁的样子,但还是很美。」罗纯睿当时并不知道迟子建家中的事,几年之后,她在家里读迟子建的中篇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当时我怀孕,我看那本书,我哭的啊,那本书我是一宿看完的。」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写于丈夫去世之后,开篇第一句,迟子建写,「我想把脸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见我的哀伤。」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位悲痛难抑、感觉被命运遗弃的妻子,她的丈夫是一位魔术师,因为车祸离开人世,带着悲痛,她决定前往曾经与丈夫相约要一起去的三山湖。一路上,这个一度以为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见证了世间的种种苦难、悲哀和死亡,其中的主角蒋百嫂,甚至连大声哭一哭的机会也不曾有。若是按照小说创作的定式,故事停在蒋百嫂命运的最悲哀处或许会是很多创作者的选择,但迟子建没有,她继续往前走,又遇到一对经历不幸的父子,故事临近尾声,「我」由小男孩带着,到森林里一处最清澈的溪流处放河灯,祭奠故去的亲人,依旧是她深爱的自然,给了悲哀的人们最深切的抚慰,矗立在这样一条溪流边,「我」拿出魔术师的剃须盒,将一直保存的残留的胡茬儿送进水流。「我的心里不再有那种被遗弃的委屈和哀痛,在这个夜晚,天与地完美地衔接到了一起,我确信这清流上的河灯可以一路走到银河之中。」
故事的最后,「我」再一次打开剃须刀盒,迟子建给这个悲伤故事的结尾是,「一只精灵般的蓝蝴蝶飞出了剃须刀盒,落在她右手的无名指。」
罗纯睿觉得迟子建身上就是有这种乐观和生命力,「换我们一般人,一个事给你打击得,你就狼狈得不行了。她从不狼狈。」罗纯睿说起陪央视做迟子建节目,到过她家里,家被她收拾的特别清爽干净,很多书,但从不杂乱,迟子建的居室挂着她随意画的小画,画里是她钟爱的山川树木,花花草草。
采访第二天要拍照,迟子建带了一个小小的绸面的化妆包,化妆包上绣着几朵小花儿,她依然爽朗地笑着,对着摄影师大呼上当,但仍旧咬牙配合着。这天她穿一套很精致的深蓝色绒面套装,深蓝色是她喜欢的颜色,会让她想到故乡的夜空。脖子上系一条橘色花纹的爱马仕丝巾,丝巾一侧,她还别上一枚金黄银杏叶型的胸针,丝巾和金色胸针点亮了深蓝色的沉闷。
平常不怎么化妆的迟子建还特意涂了淡淡的口红,让办公室的同事们大呼意外。结束拍摄后一起吃饭,饭桌上迟子建很自然地说起,自己和丈夫结婚那年去拍婚纱照,也画了红嘴唇,扑了厚厚的粉,化完妆出来丈夫都不认识她了,「当时两个人笑的啊」。
忆起往事,迟子建是那种特别真诚的快乐。罗纯睿觉得这是迟子建身上那股子坚韧生命力的外化,还是陪她拍纪录片的那次,在迟子建家,看到了她和爱人过往的一些合影,每翻一张,罗纯睿的心就像被剜了一下,「就看着他们那么好,特别疼,真是特别疼。」
迟子建是操持家务的一把好手,那次罗纯睿和同事看着迟子建在家中忙忙碌碌,打点一切,「后来她说我这一辈子,其实我能做一个非常好的贤妻良母,我什么都会,但人生没能给我这样的机会。」罗纯睿至今记得迟子建当时的表情,不是凄凄然那种,很平静,很淡然。
罗纯睿说,「我们的人生里失去了什么,会伤心啊,过不去啊,她不是,她想的是拥有过就很美好了。」但有时候迟子建的那个坚强,还是让罗纯睿心疼,在工作关系上,两人是上下级,「我能为她做些什么,我特别愿意,我就老问,你让我做点什么吧。她很少,几乎没有,都自己一个人干完了。」

「哈尔滨下雪了」
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迟子建身上有这种勇猛和欲望。
黑龙江省作协副主席司兆国原是省委机关的干部,进作协工作之前,他心里想,「这个著名的女作家,会不会不好打交道,我也不懂文学对吧?」但真正共事之后,司兆国在迟子建身上也发现了那种勃勃生机,作协工作人员只有十几个,但要负责全省的文学工作,常年写作让迟子建的颈椎腰椎都落下了毛病,但「她从没有说太累了,或我要写书了,就推脱什么,她能平衡得很好」。生活也是,司兆国和迟子建住同一小区,有时候碰到了,她买个花儿什么的回来,买个什么都很高兴,「她是真的会生活,爱这个生活。」
阿来写过跟迟子建转机时的见闻,「在机场等待下一个航班,用了9个小时,说了多少回话,喝了多少回咖啡和茶,又逛了多少遍候机楼里的免税店。每逛一遍,这个有点购物狂的迟子建,都要买一两样什么,好像她对守着冷清店面的店员都深怀同情。」
「阿来把我写得,买东西啊还有那个笑,写得跟王熙凤似的,其实哪有那么夸张。」采访中迟子建笑着为自己辩白,但很快她顺口就说出来,在阿根廷机场看到一个玉质的小鹿摆件,「很好看啊,下次来不知道什么时候,那就买吧。」又一次,看到一件墨西哥的小花毛衣,还是「很好看啊,下次来不知道什么时候,那就买吧」。
5月发完新书,6月不容侵犯,因为世界杯来了。迟子建是老球迷,世界杯、欧洲杯、美洲杯、欧冠都会追着看,这个夏天每个看球的夜晚,她都给自己准备红肠、水果,边吃边看,这种快乐蔓延到这次采访中,「莫德里奇真是特别棒。」
迟子建还爱看电影,文艺片娱乐片都看,今年看了《江湖儿女》《邪不压正》《影》《海王》《无双》。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在哈尔滨排片很少,迟子建一查,离自己住的地方好远,还是想看,溜达到地铁就去了。影院所在的地铁站离医院很近,迟子建就观察了一路那些被生活摧折的面孔,她想说不定他们中的某个人会成为之后小说的人物。最后在一家藏在装饰材料城内的有点老旧的影院看了《小偷家族》,「很不错。没白跑一趟。」
看电影或是外出路过花店,迟子建也会顺路买一束花。前段时间家里瓷砖松了,迟子建买来玻璃胶,自己把瓷砖收拾好了。她会很自然地说起,这个家里没有男主人,所以很多事要自己做。但语气中绝对没有丝毫的抱怨、不甘,或是委屈,命运那么样来了,那就承受好了。
跟人们通常理解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女作家不一样,迟子建对烟火人间那是爱得不行,寻常日子里的迟子建爱吃,这是打小儿的习惯,小时候的迟子建会去偷母亲当作菜的腐乳,把小指头伸进去抠出来吃。甚至是婴儿的时候,妈妈说她会在吃奶时把肚子撑得滚圆,然后承受不住了吐奶。
长大后的迟子建本性不改,在鲁迅文学院上学的时候,因为食堂伙食不好,她从外面买那种很多刺儿的鲢鱼,自己用电热杯煮着吃。
如今,身为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厅级干部,迟子建有时甚至会觉得公车就是个累赘。她偶尔会享受一下那种从自己身份逃出去的畅快和自由。
哈尔滨夏天有夜市,有天迟子建突发奇想,打了辆的士直奔夜市,夜市里都是好吃的,也没有人认识她,有一家卖梅干菜烤饼的摊位前排了好长好长的队,迟子建排队领一个空袋儿。队伍太长,先到隔壁摊位吃一份水爆肚儿,边吃边回来跟着大家一起等烤饼,排到了,刚出炉的烤饼焦脆焦脆,文文静静吃完是不可能的,那一点儿火炉里焙出的热乎气儿,一定要趁热吃光才算不辜负它。
吃完接着逛,一定要吃到心满意足了,再打个车回家,这一天才算没虚度。
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迟子建也热衷厨房里的发明创造。采访中那些文学上的问题,迟子建答得兴致一般,追根究底,文学是自我的,好像没什么特别可说。
但说到吃,迟子建像分享武功秘籍似的说起自己新近发明一道菜的菜谱:新鲜的柚子拦腰切成两半儿,把果肉挖出来,这样柚子壳儿就成了容器,然后用糯米和叉烧鸭,再切上一点儿胡萝卜丁,放到锅里去蒸,时间一到,柚子的香气,叉烧鸭的香气,全部都沁到糯米里,「哎呀,那个味道真是太棒了。」
总的说来,迟子建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唯一不满意的是,今年哈尔滨只下了一场小雪,也没那么冷,「这还叫东北吗?」
不管是在文学世界还是现实世界,迟子建一直笃信万物有灵,不知道是不是听见了迟子建的抱怨,哈尔滨的冬天很快有了表示,采访结束回北京的次日,迟子建发来信息,「哈尔滨下雪了,还不小呢!」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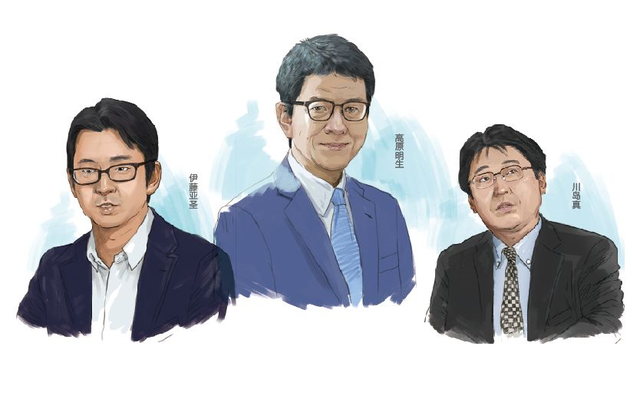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