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300万晋江人,哪家没有一段生离死别的辛酸故事?”
“这就是典型的晋江人。在他们的性格里,有沙子般的柔软,也有礁石般的坚硬。”

晋江,奔流向海

“晋江经验”题材报告文学《晋江,奔流向海》在《中国作家》(纪实版)上刊登后,我们进行了首次连载。
☞晋江故事登上《中国作家》
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副主席任林举创作,文章展现了40年来晋江波澜壮阔的改革历程,同时也展现了晋江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以及多姿多彩的侨乡风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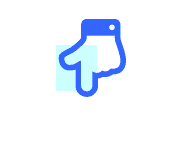
中国
作家

《中国作家》创刊于1985年,旬刊,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的国家一级文学期刊。
任林举

吉林人,曾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第六届冰心散文奖、第七届老舍散文奖、第二届丰子恺散文奖、首届三毛散文奖、2014年最佳华文散文奖。

“人文晋江”持续连载《晋江,奔流向海》,敬请关注!
相信用心的你,会从作品中读到晋江波澜壮阔的改革发展历程,更能够在隽永、优美的叙事中感受到闽南文化的深厚和文字本身的力量……

连载
2
晋江,奔流向海

第一章 海的声音
晋江东逝,一去千年,似乎从来都没有回答人类的任何疑问,但却一直都在紧紧地牵引着人类追问的目光,直至那最后的舍身一跃。
随着一个羸弱的声音和一泓单薄的流水消隐,大海腾起了滚滚巨浪,浑厚、雄壮的潮音响彻天地。一个过程完成之后,甘甜与苦涩相互溶解,涛声与潮音浑然和鸣,追求与境界彼此对接。如今,显现于人们面前的只有海,只有海的声音……那是一个雄浑、幽深、强悍和恢宏的存在,那是水的终点、水的归宿、水的成全。
“闽地瘠民贫,生计半资于海,漳泉尤甚。故扬帆蔽海,上及浙直,下及两粤,贸迁化居,惟海是藉。”(《八闽通志》)
从唐代开始,就有了晋江人以航海为生的记录。据《西山杂志》记载,隋初东石人林智惠、高逢桢驾舟远航文莱一带,因为“往来有利”,所以后来有很多晋江商人“竞相率航海”。及至宋代,晋江人闯荡海外,开启海上商贸或定居海外者就更是屡见不鲜。接下来的元代、明代、清代、民国时期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都有大批晋江人离开大陆或近海,远渡重洋。于是,一条“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得以确立,一代代从晋江出发的人们,带着金色的梦想,远涉重洋,去印尼,去新加坡,去马来西亚……入东南亚,过马六甲,打开了亚洲大陆和海外联络的蓝色通道。
<< 滑动看大图 >>


▴海滩即景 施海滩/摄
千年之后,当党的十九大上再一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伟大方略时,人们才重新将目光聚焦到时间深处那场旷日持久的海上大迁徙,发现并确认了那个历史事件的重大意义,也才发现了这一历史事件为促进东西方经济、文化、宗教、语言的交流和融汇,对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文化传播、物种引进,各民族的思想、感情和政治交流以及创造人类新文明,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由于长期往返于晋江和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越南、中国台湾地区之间,空间距离和物质的世界在晋江人的眼里变小了。虽然大洋周边码头之间的来去,多有千万里之遥,往来没有那么便捷和容易,但在他们已经变得越来越宽广的视野和胸怀之间,也早已不是什么难以逾越的鸿沟或障碍了。
世世代代的晋江人,临江而居,依海谋生,在不断与江、海打交道的过程中,参悟着水性和水道。在谋求生活的同时,探寻着人生的真谛,开拓着人生的境界,形成了与大陆文化截然不同的海洋文化。崇尚冒险,崇尚竞争,崇尚力量,崇尚自由,崇尚浪漫与激情,是他们从古至今一直没有遗失的文化基因。在晋江人的话语体系里,少有“好汉不吃眼前亏”“三思而后行”“靠天吃饭”“守成本分”“知足常乐”,更多的是“勇往直前”“爱拼敢赢”“奋不顾身”“向死而生”。
后来,他们在旷日持久的颠簸、沉浮之中,终于能够听懂海的声音,领会海的意志,听从海的召唤,应和海的节奏并与之共振、互动。

▴晋江两岸 吕俊英/摄
01
来自南太平洋的风,越过台湾海峡,拂过亚洲这片古老的大地,年年带来温暖、潮湿的气息,年年带来遥远而又迷离的梦幻。
对于地瘠民贫的晋江人来说,那些大洋深处的岛屿,不仅意味着逃离困苦的方舟,也是实现梦想的乐土。
300多万晋江海外游子,虽然每个人漂洋过海的年代、方式以及最初的动因千差万别,最后的结局和生存状态也各不相同,但最主要的理由却只有一个──追求美好的生活,而对其行为的描述也只有一个──下南洋。
如今的安海,高楼林立,道路纵横。五光十色的霓虹和喧闹繁华的市声之中,已经很少有人能够想象得出,就在这些飞旋的车轮之下,曾深深埋藏着安海的前生──古安平以及它的另一世繁荣。
举世闻名的安平桥,就坐落在安平古渡的旁边。时间的潮水将往昔的一切夷平、淹没,昔日的海湾已在人类历次的填海活动中,被填成平地。经年累月,平地上又耸立起一座座、一排排现代化建筑。而这座古老的石桥却仍然不屈不挠,从岁月深处探出它覆满沧桑的身姿。昔日桥头的那座白塔还在,却已和石桥在视觉上切断了联系,茕茕孑立,在失去了如林樯帆和往来客商的昔日渡口,显得格外孤独和寂寞。
所谓的古渡,据年长的老人介绍,已经只剩下两排尚且完整的石阶和一堆旧码头坍塌后遗留下的乱石,但人们能够看到的,不过是一圈严严实实挡住了视线的铁皮围墙,围墙里封存着那个失去原貌的古渡遗址。
这里就是晋江早期经商者──安平商人下海出洋的重要港口之一。

▴安海古镇 施清凉/摄
早年的番邦客们,正是提着柳条箱辗转行过三里街或跨过五里桥,来到这个泪水和海水交融的渡口,告别故土,告别亲人,乘船远去,开启了充满艰辛的梦想之旅。
明代李光缙《景璧集》曾经对晋江安平(今安海镇)商人有这样的描述:“贾行遍都国,北贾燕,南贾吴,东贾粤,西贾巴,或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墟。”这说明至少从那个时期开始,晋江人的经商足迹就已经遍及海内外。特别是在明代禁海期间,晋江商人更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力。他们依托安海港海上交通的有利条件,私贸海外,奔逐于欧洲殖民者泊踞的海岛,如活屿、南沃、香山沃等地贩私、贸私,甚至远航至吕宋、占城、琉球、渤泥以及日本等地进行贸易。
在安平商人群落里,李寓西(1522—1572)应该是较早出洋并见之于记录的先行者。据《晋江县志》记载,李寓西12岁即随人去广东经商。他从小聪慧,在商业行为中诚信待人,灵活应付,因而得到人们的信任和尊崇,广东当地的商人都愿意跟他合作。后来,他又到了外国商人集聚的南沃,与他们频繁交往,又刻苦用功,学会外语,渐渐成为专营进出口商品的大海商。
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西班牙人占据吕宋,招募华人去吕宋经商,开始无人敢去冒险。由于李寓西长期与外商交往,情况熟悉,于是率先贩运出口商品进入吕宋进行商贸活动。因为他懂外语,不用翻译便可以与殖民者的首领直接对话,得到了他们的重视和信任,很快就打开了市场,获取巨利归来。
李寓西首航吕宋成功,带动着安海商人纷纷前往吕宋经商,以至于“十家而九”都争着去吕宋,为数百年来晋江人竞趋吕宋侨寓经商首辟了一条新的航道。
大批“下海”者,以巨大的基数和较小的概率,造就了一个个闪光的传奇,让一批幸运者、佼佼者和成功者,如陈斗岩、曾友泉、柯治宇、史小楼等,和李寓西一同以商业英雄的形象被历史和后人铭记,并激励着一批又一批的追梦者继续迎风踏浪前行。
然而,人们的双眼总是习惯性地凝视着成功者头上的光环,却常常忽略了成功背后的艰辛,也忽略了成功者背后或脚下的那个庞大而又灰暗的基数。

▴新加坡晋江会馆旧照
时至今日,对于半个世纪以前的苦涩往事,新加坡晋江会馆永久名誉主席柯千衙仍然记忆犹新──
过了1941年的冬天,家住晋江罗山林口村(今灵源街道林口社区)的柯千衙,就要过10岁生日了。这是日本侵略者攻占厦门的第三个年头,时局动荡,民不聊生,衣食无着,身家难保。
那时,因为土地没有收成,家家以红薯充饥,十天吃不上一顿饱餐。为了减少消耗,天一黑,家家户户的大人就会不停地催促孩子们早早睡下。这一天,小千衙虽然听从母亲的吩咐,早早地躺在了床上,却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里,同村的大人们一直在讲那些出洋的人如何个个过上了风光的好日子。那些下了南洋的人,在村民的描述中,俨然都活得跟神仙一样,不仅住在大洋房里,衣着光鲜,派头十足,还能顿顿有米饭,餐餐有肉吃。最让人兴奋的是,父母亲已经有了送自己出洋的打算。小小的年纪,他已经隐约听到了大海的召唤,已经嗅到了梦幻的气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在急切地盼望着出洋的日子早日到来。
与儿子的兴奋大相径庭。此时,柯千衙的双亲内心充满了矛盾和挣扎──这么小的孩子,放在别人家里,可能尚在娇生惯养,如今就要送他出洋,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吗?此去重洋,千里万里,他稚嫩的身体能经受住那份颠簸吗?到了南洋,人地生疏、无依无靠,他如何立足,又如何找到谋生的出路?在家千般好,出门万事难。就算是找到了谋生手段,一个稚子在外边的孤苦无依、无疼无爱以及那种为生计而付出的奔波与辛劳,是一个10岁孩子能够承受得了的吗?更何况,眼下兵荒马乱,会不会半路上出个三长两短?但转念一想,若让孩子留在家中,守着这几分薄田从土里刨食,能不能保证一家人活命和温饱尚且不论,这样下去,将来又能有什么出息?
这样的煎熬,持续多日,柯千衙父母的心如同放在油锅上反复灼烤的饼子,时时发出痛苦的“嘶嘶”声。最终,他们还是把心一横,决定将孩子托付给一位从印尼返乡的华侨,让儿子去印尼闯一闯。一旦能够在外边站稳脚跟,将来一生的幸福和荣光或许可期可待。
这就是典型的晋江人。在他们的性格里,有沙子般的柔软,也有礁石般的坚硬。从中原到海边,不可抗拒的命运之旅,让世代的晋江人养成了一种只向前看而不愿意回头的天性。他们深深懂得,人生的希望永远不会出现在身后,希望在未来。为了未来,为了梦想,他们甚至不惜以身家性命为注也要全力一搏。

▴电影《海角有个五店市》中船上横幅:
过番好摊镭(赚钱)
尚未涉世的幼子即将远行,做父亲的心里如同打翻了百味瓶,酸酸苦苦、辛辛辣辣的汤水,盈满胸膛,从肺腑直逼双眼,但男儿有泪不轻弹,他得在孩子面前忍住。
临出门,他一改平日的节俭,亲手为儿子做了一大碗鸡蛋面线。
柯千衙少不更事,吃完这顿平日里难得一见的好饭,乐乐呵呵地随着父亲出了家门。可是父亲却不论如何也舍不得离开孩子。本打算出了村,把孩子托付给别人即回,可心里一阵酸软,便决定亲自把孩子送到厦门。
一路上,父亲埋着头一言不发走在前边,柯千衙人小步短,上气不接下气地跟在后边。两人好不容易从晋江赶到了同安境内,望着去厦门的方向,父亲突然停下了匆忙的脚步,紧紧拽着儿子的小手,沉吟半晌:“衙啊,我们今天不走了,明天再走!”
小千衙诧异地望着父亲,不知道为什么走了这么远还要回去,可是父亲并没有向年幼的孩子做出任何解释。
他看见父亲眼中闪动着异样的光亮,然后把头扬起,很坚决地转过身,拎起他,牵着往回走。多年后,柯千衙才懂得,那天,父亲转身时,是在强忍着眼中的泪水。
就这样,两人又从同安返回了晋江。
第二天,还是同一个时间,还是同一种方式,父子俩共同走到同安,父亲再一次牵着儿子的手,返身,把他领回了家。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
在柯千衙的记忆里,父亲这样送他出门,半路又带他返回晋江,来来回回一共7次,足可见别离之痛、亲情难舍。
然而,这相似的情景,又何止柯千衙一家!海外300万晋江人,哪家没有一段生离死别的辛酸故事?怎奈,在那些不堪的旧日,国弱家贫,资源紧张,生计难谋。为了温饱,为了尊严,也为了那些无力和无意远行的同族同类,只能远走他乡。这种孤注一掷的出洋,与其说是为了追逐个人的梦想,莫不如说是为了无法远行的人们留下一条生路。

来源:人文晋江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