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同志到跨性别《翠丝》:本是女娇娥,偏生作男儿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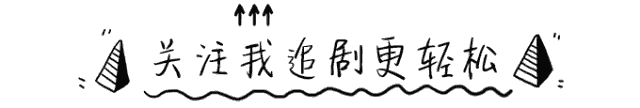
来微博找我玩吧@知影知视
微信公众号:看最新电影电视


作为华语影坛第一部“跨性别”题材的电影,没有像《谁先爱上他的》一样有“死者为大”作为掩护,《翠丝》里面的家庭是因不够温情而迎来的崩裂。
但实际上,《翠丝》已经比“同志”往前一步,涉足的是更为复杂的跨性别议题。

【剧透预警,介意绕行】
在LGBT题材上,不同于台湾电影倾向于个体情绪抒发,
香港电影更关注社会环境对个体的影响和改变,香港电影曾经是LGBT题材的拓荒者,只是近年式微。

而《翠丝》则在这种情形下,往前跨了一大步,
从关注同性恋者转移到对跨性别者及整个东方家庭的深度探讨。

虽然还是集中于小家的波动,
但《翠丝》将LGBT群体的社会辐射扩大到妻儿朋友以及陌生人,他者的介入,即是挑战也是希望。
谁是翠丝?
一场自我逃避到自我认知的旅程
翠丝(姜皓文饰)在52岁以前都是一个男人,名叫大雄(姜皓文饰),身份证上性别为:男。大雄结婚多年,妻子(惠英红饰)是一位粤剧名伶,并育有一儿一女,儿子正考虑是否去英国读书,丈夫是大律师的女儿已经怀孕两个月,即将迎接家庭里的新生命,一家人的生活平淡而美好。
然而死党阿正的死讯和骨灰由他的同性爱人阿邦(黄河饰)带回,原来阿正、阿俊(葛民辉饰)、大雄三人从高中时期就是老友。后来阿正去了英国,并与新加坡的阿邦相识相爱,在英国正式结婚。前往叙利亚的阿正最后只能以骨灰的形式回到香港,并因为香港未承认同性婚姻,阿邦不能够直接将阿正的骨灰通过香港海关。

少年阿俊、大雄和阿正分别代表
直人、跨性别者和同志
于是大雄帮助阿邦,找到大律师的女婿通过已经出柜的议员解决这件事。这一件事却让大雄家中的缺陷暴露:大雄和妻子多年来始终相敬如宾,大雄太过规矩,规矩得不那么“正常”,妻子对大雄的性向也有所怀疑,女婿经常在外玩乐,沾染性病回家,女儿为了让丈夫回家,只好用怀孕这一招,儿子思想开明,行动激进与妻子传统的师奶思想相悖,很难沟通。
通过议员解决骨灰的事情中,阿邦揭露阿正与大雄在高中时期已经相互喜欢,然而大雄却一直逃避,不敢面对阿正。直至阿正去世,大雄仍旧是阿正最爱的男人,于是阿邦想要了解清楚大雄的真实想法,想要帮助他进行自我认同,不要逃避自己是同志的事实,并提出这是对妻子和儿女不负责任的表现。
大雄告诉了阿邦:他是女人,外面不是,里面是。白天在公司里面穿着胸罩和女性内裤,晚上回家前又脱掉,十分厌恶自己的身体。大雄是一个跨性别者。
早在高中时期大雄就认识了一位跨性别者唱粤剧花旦的打铃哥,打铃哥同样告诉了阿正和大雄。而打铃哥同样知道大雄的秘密。在阿邦的指引下,大雄向阿俊COME OUT,于是阿邦、阿俊带着异服的打铃哥和大雄去兰桂坊享受变装之夜。
打铃哥在变装派对中突然死去,异服的大雄意外被儿子看到,于是大雄决定告诉妻子,两人大吵一架。那晚大雄拿起刀片伸向了自己的下体,七个月后,大雄离婚、变性。将一切都送给了妻子,变性、换回女装,重新改名成为了翠丝。
最后在阿邦和翠丝的一场床戏中结束了整部电影。

《翠丝》的故事聚焦一位有儿、有女、有妻子的大龄男人阿雄,
偶然的机遇,他决定坦承揭示深藏已久的秘密,他想要成为女人,自此,平静的婚姻生活顿时发生剧烈家变。

所以,《翠丝》也有着《丹麦女孩》的相似之处,
跨性别者终究只是表现形式,最重要的还是重新认知自我的过程,两部电影的结局也就不谋而合了。

阿雄店里的老伙计评价他从小到大性格都很温和,如今社会已经没有这样的人了,
与之对应的是阿雄的儿子,任性张扬,因为妈妈偷翻保姆的私物闹着要搬出去,家里狗死了,责备爸爸还深夜给有孕的姐姐打电话,
和儿子相比,阿雄似乎没什么个性,总是很温和很包容,对待妻儿或者店员都是一如既往的谦让平和。

会哭闹的孩子有糖吃,可总会有一些人比别人更懂事,
他们或因为贫穷,或因为取向,或因为身体残疾,他们内心里觉得自己是比别人差的人,所以没有资格去挑衅别人,
相反他们要更努力、更忍耐、更礼貌,这样他们内心的缺陷才能填补。

我们总是在问自己:
我们喜欢这世界吗,却从来不敢问这世界喜欢我们吗!
阿雄是那个不敢问缩在自己壳子里伪装自己的人,阿正则是那个不屑去问,抛开世界拥抱自己的人。

姐姐离婚是家庭矛盾第一次集中爆发,
阿雄的妻子坚持女儿回归花心丈夫的家庭,儿子立贤则反对让姐姐离婚,实则是在反抗母亲的迂腐和传统,
母亲和儿子两人所代表的正是当今香港社会的撕裂。

保守派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激进派只管斗争,不顾民生,
而却没有一边是代表阿雄的,他们要么是假装不知,刻意抵制,要么就是利用他们的身份,获取自己想得到的利益,
他们是没有权利的一方,没有人保护没有人真正关心他们。

有像安宜这样视而不见的同妻,
有像阿雄女婿一样只知道利用别人的政客,
也有像阿雄儿子立贤这样假装很开明,只要风波不波及到自己的伪开拓者。

以阿雄为代表的跨性别者,比同性恋者更多了一层身份认知障碍,
再加上社会的身份定位,他们包裹了三层对自身认知的困境,
第一层是生理和心理,第二层是自己和他人的,第三层是个体和社会的,
如果曾经的阿正不死,那个阿邦不回港,那么,阿雄就会带着面具活下去了。

酒店的那一晚,几近崩溃的阿邦像溺水之人抓住最后一根稻草一样抓住阿雄,
阿雄在秘密被暴露后慌乱地逃离,阿邦和阿雄之间,有着对自我认知的不同:
出柜还是不出柜,也正代表LGBT群体内部的困惑,
接受现代教育提倡追求自我的阿邦和一直周旋于家庭责任无暇顾及自我的阿雄,必然有着不同的处理方式。

值得欣慰的是,《翠丝》并没有强化外部环境对阿雄身份找寻时期的干扰,
阿雄的家庭,阿雄的朋友都能包容他,这也正是阿雄一直真诚待人所得到的回报,

阿邦等人带打铃哥去酒吧疯玩的那一晚,
打铃哥精装打扮在女厕梳妆镜前仔细地凝视自己,细细地涂抹口红,脸上的沟壑纵横,
究竟这一场关于自我的放逐会以什么样的姿态回归平静?
打铃哥意外去世,死在了他可以放肆做自己的那个晚上,
而阿雄在那个黑夜里也看到了自由,自由是会上瘾的,一旦试过就无法回归过去的平静和安宁。

阿雄和老婆安宜的那场坦白戏,堪称两人的演技高光,
一个歇斯底里只想遮掩一切做普通人,一个无地自容祈求给自己一个身份,
尤其饰演妻子安宜的惠英红把一个痛不欲生的“同妻“表现的淋漓尽致,更把一个爱面子的东方传统女性刻画的入木三分。

安宜的诉求是我想做一个普通的师奶,安度晚年,
因此安宜像对待一个叛逆期的孩子一样期待自己的些许牺牲能够挽回自己的老公,
那些欺骗,不解,歧视,情感,解脱都融入两人的肢体冲突和躺在地板上无助的哭泣里,
上帝用语言和性别禁锢着人类,让他们永远无法通往极乐。

安宜和儿子立贤因为父亲对家庭爆炸式的冲击,反而能平心静气面对彼此了,
立贤花了些时间了解了父亲,安宜虽然心理上别扭但依然饱含着对阿雄的爱,
施加在LGBT群体的伤害遵循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定律。

不公平的地方倒不是理解和认同的问题,
而是他们身份问题来源于基因和成长环境这些外部因素,
外界塑造了他们的身份,却又撇清一切关系不去认可他们的身份,将他们无法控制的部分强加于他们自我消化。

最终,阿雄决绝地撕开了掩藏了几十年的谎言,积极地做了手术,
他开始重新审视自我,而阿雄身边的人因为阿雄身份的置换也不得已重新看待他人,
社会变了,看待别人的眼光也要变了。

安宜拒绝在一夫一妻联名书上签字,立贤陪在母亲身边,碧儿离了婚独自抚养孩子,
《翠丝》给了阿雄一个光明的结局,
但在《翠丝》以外的世界,却没有这样温暖,
见诸报端的骗婚,LGBT权益合法化危机,社会歧视仍然潜伏在普通人生活里。

在故事里,从始至终,阿雄都没有太过激烈的反抗,
他本本分分赚钱养家,尽到了一个为子为父为夫的责任,和安宜协议离婚后也把自己经营了半辈子的眼镜店交给了安宜。

对于不理解的人他给了更多的包容,这传达着创作者一种淡然的态度:
光反抗是不够的,更多时候你得守住初心,等待社会发展走向更多元。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