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艺术|张钟萄:从艺术城到城市的艺术:上海吴淞的艺术城试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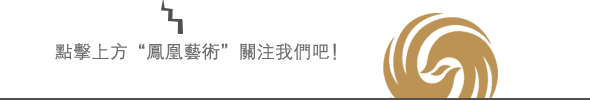
上海吴淞国际艺术城
当艺术不再只是艺术家为了进入美术馆和档案,以便进行展示或留存而焦头烂额的新产物,甚至不惜对立于生活,而是如它诞生时那样,是生活(如祭祀和宗教)的一部分,或者将生活和城市本身,当做艺术活动来推进的城市艺术和生活艺术时。艺术将呈现怎样的发展走势?吴淞国际艺术城便做了这样的试验。“凤凰艺术”特约撰稿人,张钟萄为大家深度解读上海吴淞国际艺术城的试验本质。
近一年来,众多城市加入人才大战,这表明城市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人才大战意味着“人力资本”成为社会经济下一步发展的重心。但与此同时,富士康这样雇佣了上百万工人的大厂,又计划在未来几年内,用大量机器生产替代人力生产。一方面,抢人大战中的优惠政策入门门槛越来越低;另一方面,机器-智能取代人力的新闻不绝于耳,泼我们冷水,引发未雨绸缪的恐慌感和矛盾感。毋庸置疑,这是技术进步导致机器生产力大幅提高的结果。原本生产力最为发达和集中的城市,必定最先受到新一轮生产力提升的冲击,这继而要求相关产业因应变化。就历史而言,无论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伦敦、伯明翰或曼切斯特,还是20世纪的洛杉矶,莫不如此。
上海同样如此。身为中国的老牌工业和制造业城市,尽管它兼容了金融资本对城市发展的助推作用,却在最新一轮的互联技术中不那么显眼。2018年初,上海公布了“上海2035城市规划”,其价值导向,由注重经济导向转变为更加突出以人民为中心,试图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面对新一轮工业革命(所谓工业4.0),今年2月,上海张江区被批复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尤其是推进人工智能的研发和运用。但另一个对于未来城市同样重要的试验也值得关注,上海吴淞国际艺术城。

莫奈,《圣拉扎尔火车站》

“上海2035规划”
对于如上海这样的大型工业城市而言,可谓面临“内忧外患”。内忧是指城市自身产业结构,随着生产力和生活需求的变化,必须做出调整;外患则是人力之外的机器生产趋势,正不断取代原有生产岗位。如果我们从城市发展和空间生产、生产技术和产业变迁、以及创意-艺术-未来生活这几个视角来看待当前形势时,也许可以突显上海吴淞国际艺术城的意义,而且,看到它因应当前形势的规划,最终可引导我们重新思考生活、艺术和审美活动。

论坛现场
城市发展:工业化和产业
城市(city),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话说:
“一个城市永远是一个市场中心,它拥有一个市场,构成聚落的经济中心……城市本质上就是个‘市场聚落’。”
虽然这是基于经济维度的定位,他尤其强调其工商业特征,但韦伯也从政治维度界定了“城市共同体”:它要有设防设备、市场、自主的法律和法庭、团体性格和部分自律与自主。从西方城市的特征对比来看,韦伯认为,东方没有城市共同体,因为东方城市缺乏适用于“市民”的实体法,比如他认为,中国的城市居民是通过宗族或祠堂,来维护所属团体。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提出类似看法,他也认为,古代中国和古代印度的社会结构,妨碍了城市的自由发展,“没有任何独立的权力机构能代表中国城市与国家或势力强大的农村抗衡。”

魔都上海
他们之所以这样看待中西城市差异,从经济角度来看,是因为西方城市的发展轨迹,如布罗代尔(以及刘易斯·芒福德)所言,乃与资本主义合二而一。照布罗代尔的看法,1293年以羊毛业和染色业为主的行会在佛罗伦萨取得政权,意味着市民社会的诞生,但这也是一种新的精神面貌,即创业精神和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精神面貌:包括规则、计算、财富、理智和谨慎等。尽管如他所言,西方的城市发展可以追溯到13世纪,但工业革命真正推动了现代城市的加速发展。为了生产需要,大量人口聚集到城市和工厂之中,人际关系不再如此前那样,是零散或小聚落的生活和生产模式,价值关系也发生相应变化。所以研究者认为,在工业化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是一种基础力量,工业生产的供需要求,塑造了城市生活。无论是稍早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和城市的分析,还是后来的波德莱尔或齐美尔对城市现代性的批判研究,或者是印象派的绘画,都与此过程相伴而生。

《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到20世纪,美国逐步取代英国,成为全球工业和经济的中心。在产业上,以福特汽车为代表的大规模生产、装配线和大规模消费;在经济政策上则是带有政府干预的福特-凯恩斯式的战后经济繁荣路线;在城市上,原先以曼切斯特或其他因工业革命的工厂车间和作坊为标志,得以大力发展的城市范例,如今由拥有大规模批量生产系统的芝加哥和底特律所取代。研究者用“福特主义”来描绘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的资本主义发展。到70年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市场需求具体表现的变化,也由于诸如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崛起,研究者逐渐用“后福特主义”(或后工业社会)来描绘此后的工业发展。生产逐步细分和个性化,消费趋势看起来也越发个性化,与此相伴生者,是政治和伦理上,民权-平权运动悉数登场;在意识形态和哲学思想上,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试图取消宏大叙事或单一的语言游戏;在艺术上,年轻艺术家开始反叛抽象表现主义等主流流派、美术馆-画廊等艺术体制,要求艺术走向户外、融入日常生活;在音乐上,有摇滚乐和多重曲风的交织、嬉皮士风潮,以及如约翰·凯奇等的实验等。

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更具体而言,经济上要求自由市场和小政府,再加上全球交通-信息通信网,推动信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流通,形成大型跨国公司,世界由此飞速进入美国现任总统所极力抵抗的全球化。此时,在城市研究中,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继承马克思主义遗产,极大改变了关于城市和空间原有的认识论和研究范式。先前认为,工业化引发了城市化-都市化的看法,他却说“认为都市化是工业化这个重要进程的外在、次要且偶然的结构,而我们却肯定,事实正好相反。”就此而言,城市和空间,不再只被视为用于安置厂房和用于生产的场所,相反,空间自身也会生产。原有的规模庞大且固定的生产线,变得更具弹性和流动性,所以生产、劳动、成本、市场和管理等在全球化进程中四处流动,形成了迄今虽更分散,却也依赖更紧的供应链。

福特模式生产线
全球城市和创意城市
80年代,在城市研究学者弗里德曼提出“世界城市”(World City)假设后,另一位城市研究的领军人物萨森提出了“全球城市”(Global City)。所谓“全球城市”,它包括的部分特征是:要有强大的国际金融服务,包括金融、保险、房地产、银行和会计等业务;有众多跨国公司的总部;证券交易所和主要金融机构所在地;主要的制造业中心,并伴有港口;全球媒体通信网中心;要有能吸引国际学生和科研能力的高等教育机构;为地区提供法律、媒体和娱乐的多功能基础设施;高度多元的语言、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等。

全球城市的代表之一东京
由上述线索可见,从生产力和产业而言,全球城市是全球经济、科技、文化、政治、教育和媒体通信等资源的集中地。根据日本森纪念财团在2017年12月发布的“全球的城市实力指数”(Global City Power Index),排名前五的城市分别是伦敦、纽约、东京、巴黎和新加坡,而它们同时也是艺术家访问指数最高的城市。而根据GaWC最新的“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研究”,级别最高的全球城市,前几名与前述榜单几乎重合,分别是最高级别的伦敦和纽约;第二级的新加坡、巴黎、东京,以及紧随其后的上海。上海在最新城市规划中,定位为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就某些指标而言它尚需加强,但更关键的是,吴淞国际艺术城的思路似乎提出了一种试验方案,因为它的目标思路是“将教育资源、艺术资源转换为生活品质,提升整个城市的文化风貌。

西欧夜景卫星图(经济发达指数的视觉表现)

东亚地区卫星夜景图
从西方经验来看,进入后福特主义(或后工业时代)后,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心是“创意城市”。1988年便有学者提出将艺术和文化整合进城市规划之中,推进一种新型创意城市。但直到1990年后这个概念才备受关注,如英国的格拉斯哥试图打造欧洲文化重心。到2002年,理查德·弗罗里达出版了关于创意阶层之兴起的书,此时,创意阶层已被视为当代资本主义中重要且新的社会阶层(social class)。根据城市研究学者斯科特(Allen J. Scott)的研究,后福特主义城市的趋势正是“创意城市”(Creative City)。城市中的经济生产,主要集中在非标准化生产上,包括技术密集型生产、商业、金融、个人服务,以及大量文化工业。根据他的经验研究,洛杉矶是工业城市转型的典范,它从曾经与德国鲁尔区齐名的工业区,转为为高科技中心,以及以诸如好莱坞而知名的文化工业中心。

洛杉矶主导产业演进示意图
尽管中国城市-城邑-都城的发展轨迹,就历史而言与西方确有极大不同,再加上无论从公共政策、决策体制、中央-地方关系,还是经济-法律系统,都与西方有差异,但我们终究步入了以工业化为核心的产业现代化和城市进程,所以西方的既有轨迹依然有某些参照价值。根据斯科特的最新看法,城市-都市发展正在经历第三次浪潮,它既不是19世纪那种基于工厂和作坊体系的发展,亦非20世纪的福特主义,而是(自20世纪80年代起)强调学习、创造力和创新的认知-文化资本主义(Cognitive-cultural capitalism),这已经体现在了北美、西欧和亚太某些地区的发展趋势之中。如在纽约、洛杉矶、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东京和首尔这些城市中,创意领域的一个核心要素便是技术密集型、服务和文化生产,构成了经济基础。而且,福特主义城市中白领/蓝领的劳动分工,到如今,呈现为创意阶层/低薪服务的下层阶层之分。萨森的全球城市研究得出类似结论,她认为全球城市体现出两级分化特征:金融、管理等服务业VS大量低收入工人。我们可在此城市发展、生产力提升和产业转型的线索下来看吴淞的试验。

上海吴淞国际艺术城与会专家参观宝钢工业遗存
吴淞国际艺术城:从城市的艺术到大都无城
上海吴淞区有为中国工业化进程做出重大贡献的“宝钢”(已更名为“宝武集团”)。宝钢的主要生产线已悉数迁出上海,留下大面积工业遗存,如今的问题是如何利用工业遗存。2018年5月11日到12日,一大群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到沪参加“上海吴淞国际艺术城论坛”,为此建言献策。艺术城将以上海美术学院为主体,并包括艺术机构、美术馆、艺术地产等生态和居住区。根据美术学院执行院长汪大伟的介绍,吴淞想打造从3岁到99岁终身学习的未来之城。就此而言,似乎确有不同之处。根据中国城市和产业研究学者王辑慈对产业集群的调查研究,她曾提出,希望中国的产业集群能够超越“集群经济”的层次,也就是说,不要打造依靠低成本和规模扩张的产业链或产业聚集区,如文化地产、科技地产等,而是多领域、多层次合作的产业集群,尤其是有技术创新和文化创造力的产业集群。如果吴淞的试验,能够将斯科特所谓创意城市之核心要素的学习、创造力和创新,与美院的教育相结合,从认知和文化上,培养城市发展新趋势下的人力,那么将有可能超越现有集群经济所面临的问题。

上海吴淞国际艺术城论坛的与会嘉宾
照斯科特的看法,“学习”是有准备头脑的根本要素,是创造力的准备工作,那么上海美院就扮演了关键且重大的基础角色;“创造力”是萌生有意义且新的想法;而“创新”,是将这些想法转化为具体且有效的成果,那么吴淞和上海美院,乃至教育部门,应当尽力提供相应的公共政策支持,推动产生创造力的制度环境,以及提供相应的配套设施和产业机制,使创造力最终能真正转化为创新的现实。实现这种创新,不仅可为社会文化提供土壤和观念基础,从而有利于更广泛的科技创新;而且也是将艺术重新融入生活的体现。艺术此时不再只是艺术家为了进入美术馆和档案,以便进行展示或留存而焦头烂额的新产物,甚至不惜对立于生活,而是如它诞生时那样,是生活(如祭祀和宗教)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吴淞国际艺术城,不该只是一种瞄准艺术产业集群的艺术城建设,而是将生活和城市本身,当做艺术活动来推进的城市艺术和生活艺术,而且,一旦机器生产大规模取代人力劳动,那么解放出来的人力劳动和时间,要有事可做。不过,说它是试验,是因为它仍面临一些有待展开、乃至不可控的具体问题,比如如何解决教育所涉及的公共政策问题;如何将新的技术革新,融入传统的艺术教育系统中;而后工业时代的上海,又如何真正在不抛弃工业生产和制造业的情况下,既发挥艺术和设计之于工业和制造业的溢价功能,又发挥其提升生活品质和审美水平的作用。

伦敦Tate美术馆馆长分享Tate的发展经验
根据汪大伟和主办方的说法,似乎为了承接全球化和供应链的大趋势,他们还提出了“无界之城”。从前述梳理可见,“无界”的弹性和流动性,确为当前和今后经济运行的机制。他们希望吴淞能笼络全球的艺术家和艺术资源,为之提供平台和资源,齐聚一堂交流学习,从而将吴淞打造为无界之城。实际上,就中国历史而言,根据考古学家许宏的研究,古代中国从二里头国家到汉代的两千年间的绝大部分时间中,都城都没有城墙(大城),“甚至可以说这一千多年是不设防的时代”,他谓之“大都无城”。那么,吴淞和上海最真切的无界,大概还要心怀大都之志,接受更多元的价值和生活方式,确立中国城市更全面现代化的范例。

论坛现场的讨论环节
关于作者
张钟萄,哲学博士,关注伦理学、艺术哲学和城市研究,并从事艺术相关研究工作。
(凤凰艺术 独家报道 撰文/张钟萄 责编/yyc)
凤凰艺术
最具影响力的全球艺术对话平台
艺术|展览||对话
这么好的新展览 不点图去看看?

克里斯蒂安·波尔坦斯基在中国的首次大型个展——《忆所》


程昕东当代雕塑艺术作品收藏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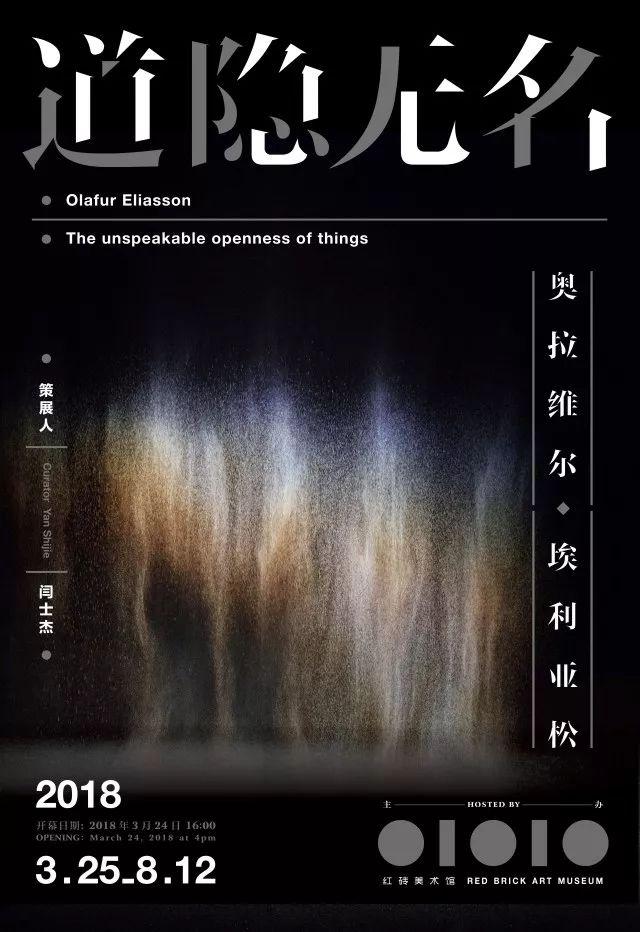
点击长按图片保存,识别二维码,关注“凤凰艺术”
版权声明:凡本网注明“来源:凤凰艺术”的所有作品,均为本网合法拥有版权或有权使用的作品,如需获得合作授权,请联系:[email protected]。获得本网授权使用作品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并注明“来源:凤凰艺术”。未经本网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上述作品。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