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用相机拍下了宋徽宗的松树,想不想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曾翰是较早用社会景观摄影方式系统地拍摄项目的中国摄影家之一,当中国城市化在本世纪初开始加速时,他于2004开始关注、拍摄包括主题公园、三峡水库和青藏铁路等大型工程,以及中国各地城市化进程中涌现的人造社会景观。他深受法国思想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关于人为地生产或再生产出来的“真实”比真实还真实的“超真实”的观点启发,进行题为《超真实中国》的项目,使用大画幅相机细致地复制中国各大城市正出现的 “如幻境式”的超真实景观。但随着行走和拍摄的延展、深入,他越来越感到仅仅套用西方的景观摄影模式是很难表达对于当下中国的思考和理解的,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视觉作者,自然而然地转向我们的传统寻求解决之道。
图像的生产从来不是单独偶发的,和背后运行的社会、文化不可分割。山水画在中国延续了一千多年,这套图像的生产机制又会怎样作用于当下?方闻说“艺术即历史”,而历史学家克罗齐也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曾翰历时十数年的《酷山水》和《真山水》系列摄影创作主题就是对艺术史的当代呈现,也是他试图用摄影去调研和书写的当代史。古人的山水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而今我们又当如何溯得“心源”呢?风景是一种媒介和文化;景观则是加上了“社会的”“批判的”“消费的”等定语的风景,而山水更是一种理想意象的风景。
在《中国摄影》的云课中曾翰将介绍自己十几年的风景摄影创作和探研,讲述如何由“景观”及“山水”,由“景”观及“山水”,用摄影发问。
课程将于10月21日(周三)、10月22日(周四)、10月23日(周五)每晚8点上线~如何报名请见文末~~~

讲师简介
曾翰,1974年生于广东,1997年毕业于暨南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专业,2009年毕业于纽约视觉艺术学院“全球摄影”项目。1997年至2008年,任《新快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报刊摄影记者、编辑,《城市画报》图片总监。曾在中国、美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十几个国家的美术馆、艺术双年展、摄影节、画廊等举办展览; 多个系列作品被上海美术馆、加拿大安大略美术馆、香港M+美术馆等机构和各国收藏家收藏。曾获中国摄影家协会TOP20•2011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奖等奖项。作为策展人,曾任2017年广州影像三年展策展人;2012新加坡国际摄影节策展人;2011年第三届大理国际影会策展人,获金翅鸟最佳策展人奖 ;2005年首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策展人,获年度杰出策展人奖。

断桥,北京,超真实中国01,2006
风景、景观、山水——一种文化的隐喻与洄游
摄影并文/曾翰 文章摘自《中国摄影》2018年11期
从开始拍摄风景起,我就一直将风景视为一种媒介,而且视摄影为这一媒介的最合适的表达工具。2002年,我在当时供职的《城市画报》杂志开设了一个名为《风景》的专栏,栏目英文名没用landscape,而是用了cityscape这个单词,开宗明义就是关于城市风景的内容。这个专栏很简单:一张跨页彩色照片,一小段关于这张照片的文字描述。彼时,《城市画报》刚刚发布了新的主题语“新生活的引领者”,我就在想,引领这个时代的中国的新生活最显而易见的是什么?应该就是我们每天都能目力所及不断变换的新的风景了。从《风景》专栏开始至今,我一直在持续不断地拍摄这个时代这片土地上的“新风景”,正如米切尔的“风景即媒介”所论,我的风景摄影就是这个时代的人与他们所处的空间之间的价值交换,也是作为拍摄者的我与他者之间的价值交换,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风景是“社会象形文字”。“风景作为一种媒介不仅是为了表达价值,也是为了表达意义,为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最根本的,是为了人类与非人类事物之间的交流。”(W.J.T.米切尔《风景与权力》)风景作为媒介本身,而摄影作为媒介的载体,它们一起组成了风景摄影,成为工业时代以降至今,人类社会最为重要的文化和图像生产之一。
进入21 世纪的中国正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文明交汇与衍生的内爆过程,虚妄荒诞的景观构造出一个想象的异邦。一手制造出种种乱象的人们却似乎愈来愈无法掌控和适应,就像科学家面对自己创造的异形一样手足无措。在这样的情势下,摄影不得不以它与生俱来的特性—“上帝的眼睛”—凝视当下,沿袭西方科学和理性的“景观摄影”应运而生。

欢乐今宵4,2004,曾翰
从2004年开始至今,我一直在拍摄的各个主题的景观摄影计划,从最开始拍摄城市里倒闭的卡拉OK俱乐部的《欢乐今宵》;到在全国各地拍摄各种状态的主题公园的《世界遗迹》;还有近年来中国一些超乎想像的巨大工程,以及环游多个中国城市拍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所呈现的城市风景的《超真实中国》。我一直使用大画幅相机企图以超细致全景式地复制社会现实。然而随着行走和拍摄的延展深入,我越来越感到仅仅套用西方的景观摄影模式是很难表达对于当下中国的思考和理解的,层出不穷的奇观很容易就变成了一种模式化的样板收集。贝歇夫妇创立的类型学摄影可以将西方的工业建筑按照球形、矩形、三角形等几何图形进行分类拍摄,是基于照搬西方工业文明严谨而理性的发展逻辑,而发生于当下中国的剧变并不像西方那样有清晰的逻辑结构可循,时间也更加急促,如果生搬硬套西方的摄影经验似乎也力有不逮。怎么办?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视觉作者,我自然而然地会向我们的传统寻求解决之道,而纵观中国艺术史,有一个主题两千年来一直被中国的艺术家持续不断的创作着——山水。

世界·遗迹45 ,2004-2005 曾翰
山水,是中国人表达与所处世界之间关系的观察和思考,大约在11世纪以前的一千年里,中国画家致力于使绘画成为有力的媒介,借以理想地呈现外在世界的物象与人内心的思想,从而达到良好的平衡,唐代张璪提出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就是千余年来中国艺术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在古代中国人眼里,绘画就好比《易经》中的卦象,具有造物的魔力。画家的目标在于把握造物的灵动与变化,而不仅仅限于模仿自然,绘画应当包孕并且掌握现实。”(方闻《心印:中国书画风格与结构分析研究》)山水画延绵不绝的核心动因,就在于人与自然的互动和融合,而这种关系到了今天又将何以为继呢?
于是我尝试通过“山水”的观察角度和思维方式重新审视中国的当代景观,从2005年起我尝试将类型学、新地形主义和传统山水散点透视法融会贯通,以山水长卷的方式拍摄蓄水后的三峡库区开始的《酷山水》系列。从2002年为《城市画报》拍摄“风尘三峡”专题开始,我几乎每年都去三峡,带了各种相机去拍,试图找到一种最合适的表达方式,直到2005年,我读了很多关于中国山水画史的书,着迷于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和夏圭的《长江万里图》,就想能不能用长卷山水的方式去拍三峡,于是买了一台624宽幅全景相机,从三峡大坝一路拍到重庆朝天门。那个时候三峡大坝已经建造起来开始蓄水了,当年汹涌奔腾的大江已变成了“高峡出平湖”的水库,止水微澜,甚至平静如镜。我觉得就像是在给那个正在逝去的三峡拍摄最后的“遗照”,所以坐着轮渡,一个码头一个码头下来,找一个半山腰高的点,水平对着江对面取景,三分之一水面,三分之一对岸的山与城与废墟,三分之一天空,心如止水般一张一张拍摄下来。蓄水之后的三峡有一种喧嚣过后镇静,有一种暴雨将至的不安和肃穆,正所谓静水深流,潜流暗涌,我越是冷静地拍摄这山水,而这山水却在对着我“此恨绵绵无绝期”地欲说还休。所以,与其说我在选取拍摄地点,不如说是那些地点在选取我,在几年反复拍摄之后,最终我选取了十张长卷照片,组成了《酷山水》系列最早的一组——《三峡止水图》。

三峡大坝,酷山水01-三峡止水图,2006,曾翰
在十年《酷山水》的拍摄中,我便将自己转换成一位被时光机器抛到当代中国的古代文人,睁大那渴望与宇宙自然沟通的眼睛,俯瞰这当下的种种山水,那被污染成稠绿的湖水,那被挖掉大半的青山,就是我的青绿山水吗?那被暴雪压断的烟雾弥漫的山林,就是我的云山图吗?那被地震震得粉碎坍塌的山脉峡谷,就是我的皴染山河吗?我不得不思考传统东方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的结合究竟会诞生出怎样的结果?会否像科幻电影里经常描述的主题那样:将不同基因结合后,总会制造出能量超强,但破坏力超大的异形?与此同时,自然也并全都像人类一厢情愿地想象那样永远都是美好的,和谐的,它自身的残酷性甚至超出人类的预料,尤其是近年来,地震、海啸、洪水、雪灾、飓风等等特大自然灾害频发,在它的破坏力面前,人类的力量简直渺小得不值一提。在持续不断的人与自然的斗争中,两败俱伤是最终的结局,中国古人的至高理想——天人合一,现在就像个虚幻的,一触即破的肥皂泡。

酷山水31-南岭断树图七,2008,曾翰
前面十几年创作《酷山水》系列时,我花了很多时间精力去学习研究中国山水画史和画论,还去国内外的博物馆美术馆看很多山水画原作,我很想搞明白山水画的视觉范式为什么能在中国这样的时空下形成,且对很多地区比如日本、韩国的艺术产生影响。传统视觉艺术背后的思想和哲学,到了今日会怎么样应对成现实中国的风貌。用山水的方式去观看和呈现,就是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提问和思考的开始。很多人会把这些图像理解成为批判性的作品,或者是一个纪实性的作品,但其实对我来说,应该是思考性的作品。
与西方的艺术概念最为不同的是,山水既非写实也非抽象,而是一种类似结构主义的既写实又写意的图像重组。中国艺术史家方闻在其代表作《心印:中国书画风格与结构分析研究》中就此做出了详尽的分析和梳理,他认为:“中国古代绘画基于传统图像形式,就是画面平面,而非光学化组构而成的。相对于西方绘画用笛卡尔线性‘单点透视法’(one-point perspective),中国画并不从单眼镜(monocular)‘注定的视觉点’来制造‘墙上一洞窗’,把画面关在镜框里边。(谢赫)所谓‘经营位置’,用‘移动的视点’(moving focus),一步一步加添三角式山形,创造了超越镜框限度外的‘括大的视觉范围’(expanded field of vision)。从视觉模型而言,以马·普赖生(Norman Bryson)用语来说,中国古山水画遵循‘瞥视’(glance)而非‘凝视’(gaze)的逻辑。因为中国画家注重‘读’画,跟西方‘看’为方式的绘画大不相同。”怀着对上述理论的巨大好奇,我决定开始一场旷日持久的探秘揭迷之旅,用摄影对山水画史上的重要作品进行实景地考据,以拟仿的图像进行跨越时空的解构和重构。

宋徽宗的松树07,2016,曾翰
中国山水画有一种与西方艺术思想不同的理论——“仿”,即指以敬古为由,摹仿先辈大家之风,反复进行各种风格实验,最后创造出独特的个人风格,这其中以晚明的董其昌为集大成者。根据王阳明的心学观点,“‘宇宙便是吾心’,既然天下无心外之物,因此师法自然意即师法吾心;同理,‘六经者无他,吾心之常道也’,既然心外无理,因此,复古即是归返吾心。艺术里的写实主义,如果不能理解为是艺术家心印的投射的话,便无意义可言。以是,艺术家并不只是单纯地模仿自然或是仿古。而是按照‘率意’的方式,重新建构自然理则,或是改作古代大家的作品。”(何惠鉴《董其昌的新正统》) 传统山水意象在摄影上的运用,在摄影术传入中国后,就一直有人进行尝试,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民国时期的郎静山,但郎静山更侧重于东方符号拼贴式的画意摄影,他对于摄影语言本身与山水精神之间的关系并无太多探索。
仿真,拟像;仿古,心印——摄影与山水,也许可以透过这样的关系重组成为一种新的“写真”。带着这样的思考,新计划《真山水》系列开始一步步的实验,并渐渐成型。

宋徽宗的松树03,2016,曾翰

宋徽宗的松树04,2016,曾翰

宋徽宗的松树02,2016,曾翰
松树,是中国文人画家最热衷描绘的对象,就像西方画家热爱画橡树一样,它们是一种精神象征的可视物和视觉符号。2016年春节前,在一场江南大雪中,我邂逅了会稽山中,宋六陵上的松树。位于绍兴东南山谷里的宋六陵遗址,曾经浅葬着南宋的六位皇帝与他们的皇后,以及北宋徽宗的衣冠冢。自公元1277年,元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珈率众首度盗掘诸陵起, 近千年间宋六陵屡遭劫难;至文革期间,悉数夷为平地;历经千年风雨,沧海桑田,肃穆皇陵如今已变身茶园;及今,只剩寥寥古松,标示皇陵遗址所在。雪中徽宗陵上的孤松,像极了《听琴图》里的那棵松,孤寂而高贵,我仿佛听到了阿多尼斯那句著名的诗:“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但其中只有一棵树。绝望长着手指,但它只能抓住死去但蝴蝶。”我留了下来陪伴了它们一年,反复地用相机与它们对望对话,拍出了《真山水》的第二组作品《宋徽宗的松树》。摄影评论家李楠微信里发给我她对于这组作品的感想:“所谓山水,并非古典的沉吟与怀旧,摄影家也不是将自己装扮成书生与隐士,那既可笑又矫情。一株宋徽宗的松树,出现在一张当代照片里的意义,并非因为它是古典的意象符号,那样的话,我们还是去故宫博物院看它好了;而是因为摄影家使它成为一个现实的紧迫问题: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如是,宋徽宗的松树才成为曾翰的作品,而非曾翰成为宋松树的临摹者。这也正是山水之于当代摄影的关键。”
五代山水画大师荆浩在《笔法记》中认为:“画者,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意即审度表现客观对象的形似,从而去探究把握其内存真实。荆浩所言之真,就是不局限于客观真实的哲思与生命体验的真,格物致知的真。五代到北宋初年,以荆浩、关仝、范宽、李成、郭熙为代表的北方画家创造一种极端自然主义的雄浑风格,后称之为“北宗山水”。2018年初春之际,我据史书画论等文献考据,遍游了北宗山水大师们曾经长期生活创作的大山,如秦岭、南太行、中条山等地,对照《匡庐图》《溪山行旅图》《关山行旅图》《早春图》等不朽画作,竟一一觅到相似度极高的山体实景。只不过在现实中,我们是无法用人眼的单点透视去验证这种真实性,但当我用无人机航拍器将一座丹霞山峰从山顶逐次下降拍摄,最后竟拼接出了在同一个画面呈现俯视、平视与仰视三种透视法的《溪山行旅图》;用大画幅移轴相机上下移动焦平面,竟也拼接出了《匡庐图》那种将三维空间垂直平面化的幻视。可见,北宗大师们是如何突破人眼的视野局限,对客观事物进行全方位跨时间地“格之”,从而“致知”终极的真实。

笔法记考01,2018,曾翰
荆浩虚构的导师石鼓岩子对他说:“子既好写云林山水,须明物象之源。”而不断习画到最后则“可忘笔墨而有其真景”。摄影与客观世界之间其实并不存在所谓真实复现的关系,如果以摄影为笔墨,又该怎样去描绘当下的山水呢?在这样的思考下,我尝试用过期摄影胶片的特殊感光色彩去改变所拍摄山水的时间属性,创造出一种错乱和超越时间的混沌感,同时用摄影的机械之眼去进行改变肉眼透视的观看与呈现。客观世界原本并不存在所谓绝对真实,每个人所见的“真实”其实都是通过光和人的视网膜与脑神经一起产生的化学反应来认知的那个有了色彩和形状的“客观真实”,所以我的拍摄的山水,与荆浩所画的山水,虽然在空间中是同一所指,但又因不同的时间与观看,而产生出不同的“物象之源”与“真景”,也许这就是我所要考据与思考的“真”。
郭熙《山水训》篇言:“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焉,耳目断绝。”意即山水作为一种至高的理想,连做梦时都在,只不过被耳目所隔绝了。所谓林泉高致在当下就真的像梦,世人的耳目早已与之隔绝。我在郭熙当年写生出没的山中,试图打开被隔绝的耳目,直抵林泉之梦的真实。这些自然的山石林泉,历经千年,早已渐化为人的生活场域,尤其在当下之粗鄙的世俗生活,梦寐以求的林泉之志也从文人的理想想像,跌落粉碎为一地鸡毛。我的慕古追思,只能在沾染灰尘的粗颗粒底片上显影成一种白夜般的暗黑,在摄影中我的耳目尚未断绝,也许在这个时代,摄影才是最适合描绘林泉高致的笔墨。

林泉高致考01,2018,曾翰
图像的生产从来不是单独偶发的,和背后运行的社会、文化不可分割。山水画在中国延续了一千多年,每一个时代都在做这样的事情,而且经常会有复古的说法。到了现在,我们也谈“复兴”,这套图像的生产机制,在当下是什么样的?方闻说:“艺术即历史”,而历史学家克罗齐也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真山水”的这个创作主题就是对艺术史的当代呈现,可以说是我企图用摄影去调研和书写的当代史。
课程购买后可以反复收听,具体报名方式如下:
长按下方课程图片
☟
识别图中二维码进入报名页面
☟
关注“千聊公众号”
☟
进入报名页面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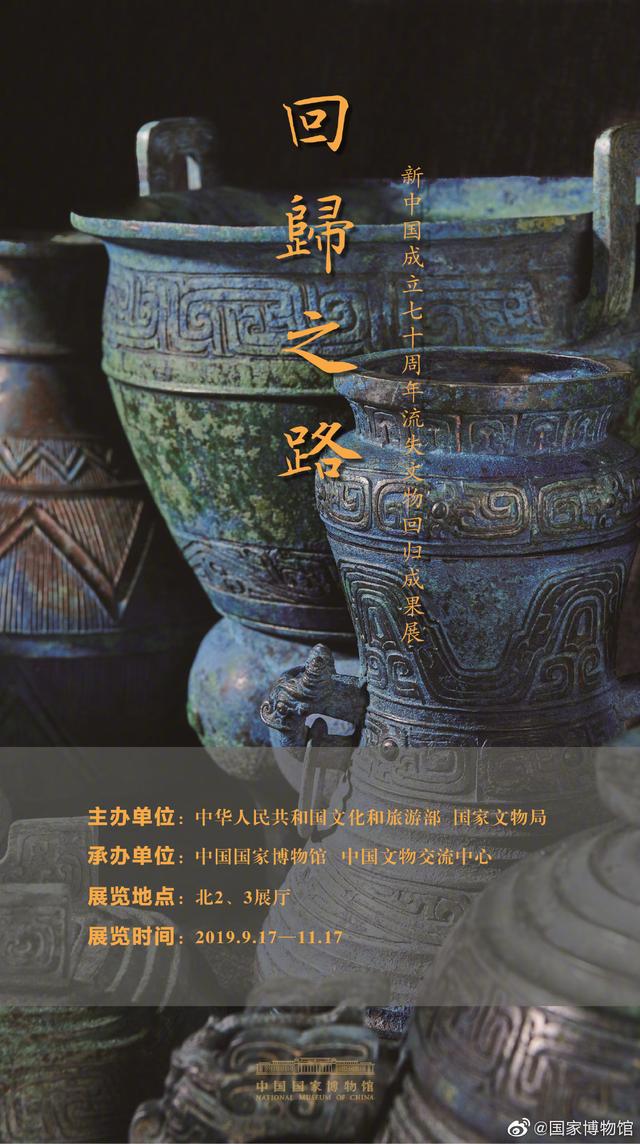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