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然《顿悟时刻》分享“文学公开课”携一把“小说解剖刀”重达故事现场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新冠疫情的到来,让全世界都处于在变动、不确定之中,英国作家毛姆说的“阅读是随时携带的避难所”,也比以往更深入人心。在众多类型的阅读中,要说到比较纯粹、安静的阅读对象,莫过于对文学的阅读。
很长时间以来,张悦然是以80后作家群体的一个典型代表,为众多文学读者熟知。 近几年,她除了继续写作,还走进高校授课,如今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作为一名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计算机专业的理科生,她的文学积累纯粹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这种自我教育的主要方式就是——高质量的阅读。她给学生分享自己是如何走进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在写作的过程中,又该如何在主角和配角之间把握平衡,等等。她将对小说的阅读与人的生命状态联系起来,“通过小说发出的光芒,发现自身的遗失之物,并用读和写,再次赋予其生命。”
张悦然的文学课,得到学生们的认可。每次下课,都有同学都追着她下楼,要跟她继续交流。学生们对文学的热情感染着张悦然,也改变了她的看法,“这些学生将来大多并不从事文学相关的工作,也有可能因为生活的忙碌而逐渐远离文学,而我所做的事,就是尽可能让文学多留在他们生命里一段时间。”
8年人大文学授课精华 20多年阅读创作积累
她一直过着文学的生活
如今,就算没有机会在人大听张悦然讲文学的人,也有福了。因为她用3年时间,将自己在人大8年所上的写作课教学经验,以及自己过去20多年来的文学阅读创作积累,写成了一本书《顿悟时刻》。阅读这本书,就像上一堂堂张悦然的文学公开课:她是如何读村上春树的?波拉尼奥给了她怎样的启发?艾丽丝·门罗、伊恩·麦克尤恩又对她展现了怎样精彩的内心风景?是什么促使作家动笔写一篇小说?是什么让读者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开始了思想的跋涉?大众小说为什么能感动更多的人?

从《都柏林人》到《嫌疑人X的献身》,从《刺杀骑士团长》到《2666》……张悦然犹如化身携一把“小说解剖刀”的领读人,开辟鲜为人知的阅读路径,带领读者重新抵达故事现场。她的领读不断提醒我们,有限的故事却能帮助我们了解世界与他人,尤其是当我们凝视小说家笔下的爱意和伤痛、煎熬与畅快,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身处之地在时空中的坐标,从而更好的理解自己。
在最敞开的公开课里,我们却能看到张悦然最细密、最个人的阅读方式。比如张悦然读书没有做笔记的习惯,但她会在读完一本书之后的几天里,留给自己一点时间,不断回想那本书。“那几天很宝贵,我尽可能不去读新的书,我用这样的方式确认是否可以和一本书建立更深的情感。有时候刚读完一本书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几天之后会忽然感受到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她通常不让自己马上做出判断,而是尽可能延迟这种判断,看看它可否在心里生成更多的东西。
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难免会产生变化,阅读越来越成为张悦然生命中相对恒定的部分。她说,有时候阅读并不是为了指导和启发自己的写作,“单纯地,就是一种度过生命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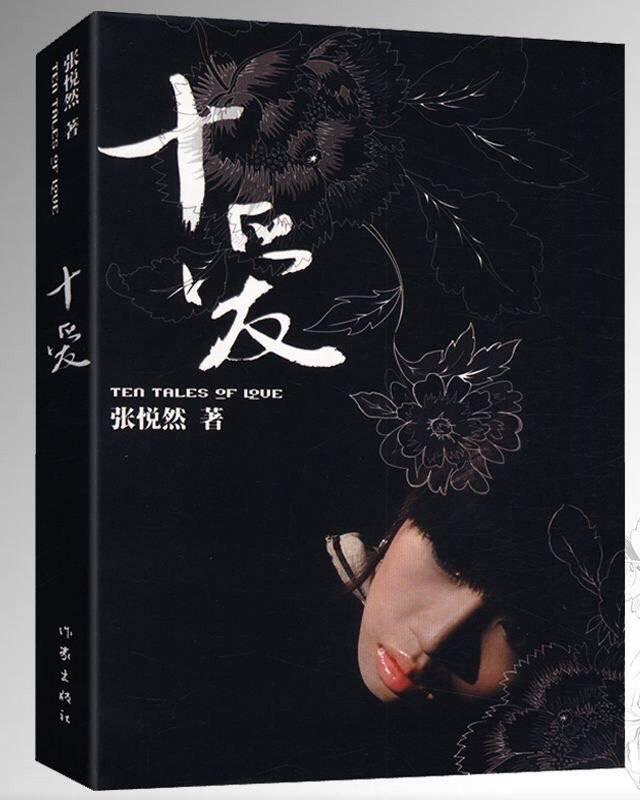
她与文学没有走散 与读者没有走散
优秀的文学写作者不是浪花,而是标杆
大概近20年前,非常火热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把当时还非常年轻的一批80后写作者,推到了备受瞩目的聚光灯下。出生于1982年的张悦然就是其中一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批作家有的拍电影,有的经商,有的则是消失在大众的视线之外。大家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渐行渐远,有了不同的选择。但张悦然一直还在文学的路上,创作状态稳定。这位15岁就开始发表作品的山东女孩,还有一段“下南洋”的经历,她的大学是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读的,专业是计算机。在陌生的异国,面对毫无温度的专业,她用文学写作来抵抗孤独。大学期间,张悦然晚上的时间大多用来写作,有时写到天亮,听见鸟的叫声。
在她早阶段的作品中,比如《誓鸟》、《水仙已乘鲤鱼去》、《樱桃之远》等作品中,她用才华书写着当时自己那个年龄阶段必然会关注的青春心灵状态。2016年,以父辈生命经验为题材的《茧》,也被评论家认为她的写作进入更广阔的地带。如今,2020年之夏,她戴着文学阅读手记性质的《顿悟时刻》,仿佛在告诉读者,这么些年来她一直在耐心阅读,阅读一直是护卫她行走的铠甲,她一直过着美好的文学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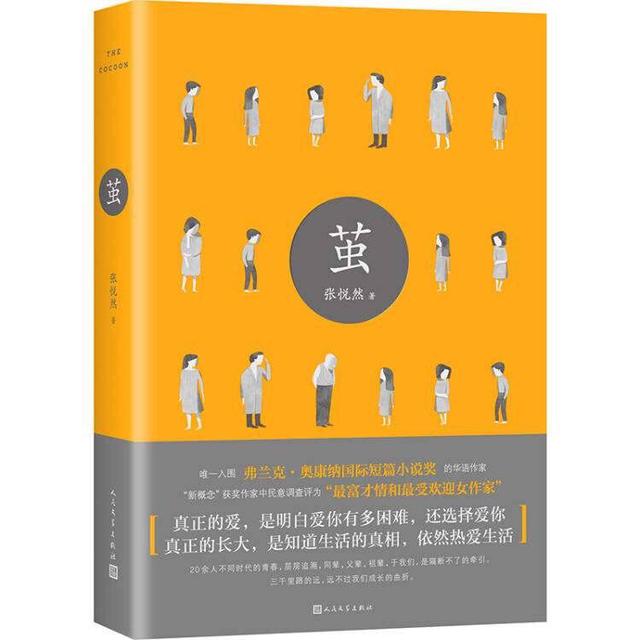
与张悦然同龄或者更年轻的读者,或许并没从事文学写作,但却跟着她一起,通过文学整合着自己的当下人生。她与文学没有走散,读者也没有与她走散。
随着后浪90后、00后逐步走上社会的聚光台,在“80后”这个概念也正在悄然褪去其新闻性。但好在优秀的文学写作者不会被世代困住,而是会超越时间,成为不会被浪花拍在岸上的标杆。
封面新闻对话张悦然:
深度阅读所面临的挑战来自“很容易被消耗和转移的热情”

张悦然
张悦然,2001年获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小说集《十爱》入围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茧》入选《亚洲周刊》2016年度十大小说。2008年创办文学主题书《鲤》系列,担任主编。2012年起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封面新闻:现在社会,各种诱惑很多。人的精力很容易就被分散掉。要保持深度阅读的状态,其实是不容易的。对此,您有怎样的感受、经验?
张悦然:没错,保持深度阅读是一种能力。失去它比我们想象的要容易。有的时候,如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找不到一本真正喜欢的书,也会失去阅读的热情。虽然仍在阅读,但读得很浅,那种感觉就像小时候课间一边走着神一边做广播体操一样。动作看起来是一样的,可是意识完全没有参与,身体并未得到任何训练。在这样一个时代,深度阅读所面对的困难不仅仅是有限的、碎片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很容易被消耗和转移的热情。这种热情是需要保护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把阅读放在生活中很重要的位置,不让它被其他事物取代。
封面新闻:很多阅读者并不一定从事文学写作,他们的工作也与文学距离比较远。但是他们依然要从文学阅读中获得力量。但同时,文学往往在相对小部分的人群里有影响力。在您看来,文学与现实,我们的生活,是怎样的关系?会有感到文学比较无力的时刻吗?
张悦然:文学的地位的确越来越边缘,影响的人群也越来越小。从年轻时代一路走过来,我见到很多同路人离开了文学,因为文学无法供养生活,也因为自身对文学的热情在减少,这是很自然的事。我忧虑文学的未来,但也并不比我对世界的未来的忧虑更多。我也会因为这份忧虑而去尽力做些事,让更多的人关注文学。比如2018年鲤杂志所做的“匿名作家计划”就有不错的反响。
封面新闻:在书中分享了您近年常读的村上春树、波拉尼奥、门罗等同时代的作家作品,可以聊聊您为什么挑选了这几位作家吗?以及阅读这些作家给您带来哪些特别之处?
张悦然:就像我在序言里所说的那样,因为喜爱和各种机缘,我所挑选的这些作家,是过去几年里我阅读得比较多的。我也经常在课堂上与学生谈论他们。因为学生很喜欢他们的作品,希望可以做更细致的探讨。因为讲课的缘故,我经常需要重读他们的作品,对他们的作品比较熟悉。此外,我认为他们是与我们同时代的作家,无论在文学观念还是关心议题方面,都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的面貌。通过阅读他们,我们也能更了解我们所身处的时代和世界。但当然,阅读经典也同样有意义。这本书里也同样涉及到一些,比如以亨利·詹姆斯为例分析小说视角的篇章,还有契诃夫、托马斯·曼、托尔斯泰也作为例子散见于书中。比较遗憾的是,还有一些我非常喜欢的作家,来不及书写,比如库切、石黑一雄、安吉拉·卡特、哈维尔·马利亚斯等等,一方面是时间有限,一方面是我可能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希望日后有机会,完成他们的阅读报告。
封面新闻:《顿悟的时刻》容纳了你在人大8年所上的写作课教学精华,以及自己过去20多年来的文学阅读创作积累。在人大教书8年,对你自己的阅读和写作,是怎样的影响?
张悦然:教书确实督促我做了一些系统化的阅读。我尽量避免讲重复的课,即便是相似的主题,我通常会更换一些用于分析的小说文本。因为讲重复的东西会让我自己失去热情,没有热情的授课,是在虚度时间。所以为了保证课程有新的内容,必须以阅读和重读来提供充分的准备。不能说这些阅读和重读对写作有什么即时的帮助,有时候它们甚至相隔比较远,但是写作和教书又的确共享着同一片文学的土壤。我将多数时间用在了耕耘这片土壤上,然后让它们进行各自的光合作用。
“灾厄面前,人类远没有自己所想象的那么强大”
封面新闻:在小说创作方面,最近手头在写什么?疫情期间,不少写作者的状态都很受影响,你是什么状态?是否有计划将这些写进小说里吗?作为一个青年作家,你对世界的看法是,悲观多一点还是乐观多一点?
张悦然:疫情对我的生活有一些改变。有一段时间我几乎完全浸没在日常生活的琐事里。写作变得没有那么重要。我变得更热爱生活,更能从中获得滋养,从这一方面来说,这段生活经验很宝贵。现在生活正在逐渐恢复,我在写新的小说,但进展缓慢。这个时期对世界的忧虑不可避免会变得很多。瘟疫所带来的影响,目前尚不能看清,但它带来的影响是不可逆的,再也回不到从前了。灾厄面前,人类远没有自己所想象的那么强大。而那种强大,正是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幻觉。
封面新闻:现在有越来越多揭露复杂人性的作品,比如大热的国产剧《隐秘的角落》。站在创作者的角度,您是如何处理人性复杂的作品的?也需要作家对此产生共情吗?
张悦然:在早年的作品里,我的很多人物都具有偏执和极端的人格,它们十分强烈,但并不复杂。这是由某种年轻时代的审美趣味造就的,同时也和我个人的天性有关。我时常觉得自己的“天性”不够复杂,甚至有点简单或者简陋。这在生活中可能是种福气,一方面我没有给身边的人设置太多相处的难题,一方面我也不太会因为内心某个不见光的角落而备受折磨。但是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是个巨大的弱点。它意味着如果我要成为更好的写作者,必须学着去认识和理解他人,必须不断去拓展心灵的边沿。在近年的作品里,我对现实和历史的热情,也正来自于对藏匿于其中的复杂人心的探究。在《顿悟的时刻》的一个篇章里,我讲到了亨利·詹姆斯的长篇小说《一位女士的画像》,女主角伊丽莎白的认知世界的外沿被黑暗所包覆,她的人生使命正是不断用自我学习拓展认识,照亮那层黑暗。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自己和伊丽莎白很像,即便我不写作,那也是我人生旅程的一种使命。
封面新闻:您认为文学爱好者在探寻写作之路的过程中,阅读文学评论类的书籍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张悦然:我个人非常喜欢阅读文论。从早年的迈克尔·伍德的《沉默之子》、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到近年的乔治·斯坦纳、伊格尔顿及詹姆斯·伍德的诸多著作,我都非常喜欢。还有一些作家的文论给我带来过影响和启示,比如库切的《内心活动》、戴维·洛奇的《小说的艺术》、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等等。好的文论总是能唤起阅读和写作的热情,总是使文学和你的关系更亲密。而且,有的时候文论本身所呈现的文法、语句之美,也同样令人沉醉。
【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欢迎向我们报料,一经采纳有费用酬谢。报料微信关注:ihxdsb,报料QQ:3386405712】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