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人物|剧作家汤姆·斯托帕德的悲喜人生
参考消息网3月2日报道美国《纽约人》周刊网站2月22日发表文章《汤姆·斯托帕德的悲喜人生》,全文摘编如下:
2007年,剧作家汤姆·斯托帕德去了莫斯科。他去那里是为了指导排练他的三联剧——统称为《乌托邦彼岸》的《航行》《失事》和《获救》。这部三联剧2002年在伦敦首演,2006年移师林肯中心演出。如今,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重归故里。剧中大多数人物虽然被流放,但来自俄国(最引人注目的例外是一个名叫卡尔·马克思的德国人),而且他们将首次用俄语对话。一向彬彬有礼的他想在排练时亲自到场,提供鼓励和建议。由于斯托帕德不会说俄语,所以这些话是通过翻译传达的。有一天吃午餐时,上了一道不知名的肉片,斯托帕德问那是什么肉。有个人绞尽脑汁寻找合适的英语单词,然后说:“是语言(language)。”
当然,这道肉菜是舌头(tongue)。这是赫米奥娜·李在她的新传记《汤姆·斯托帕德生平》中讲述的数百桩趣闻之一。如果要让如此有趣和情有可原的错误发生在哪位作家身上,那就非斯托帕德莫属了。在李的书中,他是个被人簇拥的磁石般的人物,快乐的意外、偶然的邂逅、新的爱情和俗世的财富如铁屑般聚拢过来。有位朋友说,他“善于接受崇拜”。与斯托帕德同为剧作家的西蒙·格雷给出了这样的评价:“这其实是汤姆的成就之一:除了他的外貌、才华、金钱和运气之外,他没什么可羡慕的。”
童年流亡
说汤姆·斯托帕德出生在兹林、出生在摩拉维亚没有错,但这并非事情的全貌。对斯托帕德来说,故事永远没有全貌。
1937年7月3日出生时,他被取名为托马斯·施特劳斯勒,是犹太裔捷克人欧根·施特劳斯勒和玛尔塔·贝科娃的次子。兹林现在还是兹林,但它在1948年到1990年是不存在的;相反,它被冠以“哥特瓦尔德夫”的名字,用以纪念在1948年到1953年统治该国的共产党人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还有摩拉维亚。它在20世纪初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在20世纪末是捷克共和国的一个地区。正如李所说的那样:“所有名字都变了。”
兹林是一个以拔佳制鞋厂为中心的公司城镇,欧根是公司医生。1939年4月,德国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施特劳斯勒一家和其他犹太人匆忙离去。施特劳斯勒一家和他们的邻居格勒特一家可以选择目的地:去新加坡还是去肯尼亚?选前者还是选后者?托马斯和家人去了新加坡——李写道:“可能途经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然后又去了热那亚。”随着日本人向新加坡推进,1942年年初,玛尔塔和两个儿子乘一艘拥挤的轮船逃走。他们在斯里兰卡的科伦坡换乘了另一艘船,玛尔塔以为这艘船驶往澳大利亚。但是,并不是,它驶向了印度。在战时的颠沛流离中,一个简单的误解可能会改变整个人生。
施特劳斯勒家的两个男孩再也没有见过他们的父亲。斯托帕德几十年后得知,欧根可能搭乘了在苏门答腊附近沉没的一艘船。玛尔塔带着两个儿子在孟买下了船。
战争结束了;玛尔塔与英国军官斯托帕德少校结婚。因此,在漫长旅程的最后一站,施特劳斯勒一家变成了斯托帕德一家,乘船去了英格兰。
渴望成名
如果像格雷厄姆·格林对约翰·勒卡雷所说的那样,童年是作家的信用卡余额,那么八岁的斯托帕德在英格兰登陆时已经很富有了。他和哥哥彼得进了寄宿学校,迅速接受了他的新国家的经典传统:板球、飞钓和外交掩护。
斯托帕德的青少年时代飞逝而过。他从未上过大学:这是个不同凡俗的缺省,使他加入了萧伯纳和莎士比亚的行列,并且保证了一种永不满足和减退的精神欲望。斯托帕德在布里斯托尔从事记者工作,在《西部日报》担任记者,后来又供职于《布里斯托尔世界晚报》。
他还在英国最著名的地区性剧院——布里斯托尔老维克剧院——出没,与冉冉升起的新星彼得·奥图尔交上了朋友。斯托帕德在老维克剧院反复观看奥图尔扮演哈姆雷特;在斯特拉特福德剧院看他出演《驯悍记》《特洛勒斯与克瑞西达》以及《威尼斯商人》;他深受打动,写信回家告诉玛尔塔:“我想出名!”
想不到,梦想成真了。在这个过程中,他断断续续地尝试创作小说,包括一本疯狂的小说《马尔奎斯特勋爵和月亮先生》。还有广播剧和电视剧的剧本。他第一次去了纽约,在那里认识了导演梅尔·布鲁克斯。他搬到了伦敦。他烟不离手,一根烟吸三口就扔掉——这表明文句即将形成。他甚至把火柴盒上的砂纸剪下来贴在桌上,这样一来,他不必把笔放下就可以一边写作一边点烟。
经过他早年的颠沛流离和学徒生涯的跌跌撞撞,当成功降临时,反倒具有一种奇怪的拉平效应,就像战争使和平显得平淡无奇一样。
阳光灿烂
斯托帕德与第一任妻子乔斯·英格尔离了婚。他得到了两个儿子的主要监护权,其中一个儿子后来说英格尔是“精神分裂的酒鬼”。斯托帕德写给哥哥的一封信讲明了这场危机,具有一种不寻常的紧迫感:“我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生活。”
经历了这样的低谷之后,在20世纪70年代初,斯托帕德时来运转。1972年,他与米丽娅姆·斯特恩结婚。后者的科学和医学电视节目往往意味着她的名气超过了丈夫。这段婚姻持续了20年。他们的日记里记满了在不同大陆的约会,为了争取在一起的时间,他们有时要搭乘协和式飞机:这是对斯托帕德童年颠沛经历的古怪超音速模仿。
荣誉和义务像露水一样落在斯托帕德身上。就这样,他春风得意,成为了完美的英国人——或者,按照他谦虚的说法,“冒牌英国人”。2014年,他与萨布丽娜·吉尼斯结婚。这像是话剧的终场:“鲜花用了五天时间来摆放,三层蛋糕用夏日繁花装点,抛撒了玫瑰花瓣,房子里有个大帐篷,阳光灿烂。”
如今的政治鼓噪——在英国和美国,在欧洲东部和西部——极其刻薄,我们可能很费劲才能听到像斯托帕德这样的温和声音,他提出的“我没有被艺术打动,因为它有政治色彩”的勇敢观点似乎越来越难以坚守。他的立场是平衡的,他的终生主张符合他宽容的本性——人皆有过。
斯托帕德的最新剧作《利奥波德施塔特》于2020年2月在伦敦首演,短短一个月后因为新冠肺炎暴发而停演。场景是维也纳犹太人默策家的一个大房间;我们从20世纪初开始,一个孩子把大卫星放在圣诞树顶端,然后发展到1924年、1938年和1955年。默策一家起初是被同化的,后来家破人亡。
奥斯威辛
传记作者李说该剧的起源要追溯到1993年。当时,斯托帕德与到访的表亲聊天时得知,他是百分之百的犹太人。他对此感到惊讶,而他这位表亲对于他毫不知情感到难以置信。他后来承认,他对血统问题“差不多是故意视而不见”。他的母亲把他培养成为信奉英国国教的学生,煞费苦心地忽略了这些问题。与她那一代的许多幸存者一样,她更喜欢宽慰人心的轻快的新生活,而不是沉重和悲惨到难以承受的历史。正如李总结的那样,她的态度是“此一时,彼一时”,斯托帕德几十年来也是这样想的。
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成为公认的连接过去与现在的大师;他的作品集是与时代合拍的舞蹈。他还认为,事实表明,最转瞬即逝的机会(登上还是错过前往印度或英格兰的船,在等待哈姆雷特王子的时候掷硬币)可能关乎生死。在汤姆·斯托帕德的生平故事里,条条大路都通往《利奥波德施塔特》。在剧中,灯光熄灭前的最后一段对话发生在英国青年利奥(他说,他母亲“不希望我有犹太人亲戚,因为希特勒可能会获胜”)与他的美国亲戚罗莎之间。他念出亲戚们的名字,她告诉他,他们是怎么死的,以及死在哪里。对话是这样结束的:“贝拉。”“奥斯威辛。”“赫尔米内。”“奥斯威辛。”“海尼。”“奥斯威辛。”

2018年斯托帕德在纽约林肯中心剧院外。(美国《纽约时报》网站)
来源:参考消息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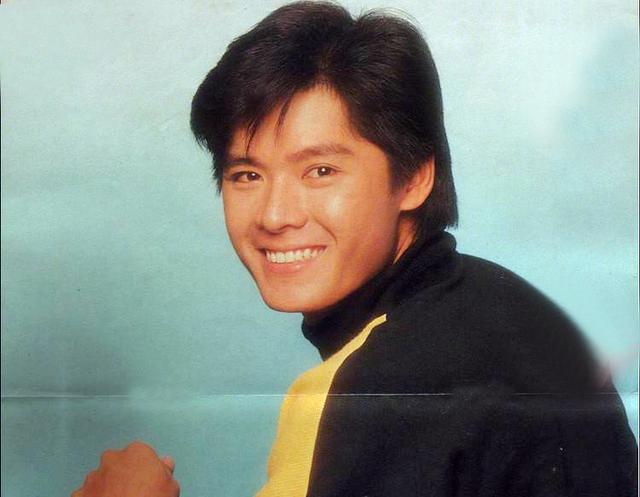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