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出破亿票房的《咒》,彻底打脸台湾省内电影“爱最大”通病
由柯孟融编剧、执导的《咒》在台湾省内上映以来取得破亿票房,并在网络上引起讨论热潮,成为继《红衣小女孩》、《返校》后又一现象级台湾省恐怖电影。有趣的是,纵观近年来的台湾省内电影票房占比,恐怖与惊悚电影尽管存在着“票房天花板”──意即有大半观众不敢看就是不敢看──却一向是台湾省内电影产业稳定输出、最终也获得稳定收入的类型大宗。
《DailyView 网络温度计》曾于2020年发布“2017-2019 年电影票房分析 解译台湾省内电影爱好者族群轮廓”,统计2017至2019年上映的台湾省内电影,在计算每个类型的平均票房后,发现恐怖电影以超过5000万元台币(约合1100万人民币)的票房成绩引领其他类型,远高于台湾省内电影平均票房的1500万元台币(约合340万人民币)。
又以2020年的台湾省恐怖电影为例,《馗降:粽邪2》、《女鬼桥》依旧取得票房佳绩,甚至评价惨淡的《杏林医院》也有近3千万台币(约合680万人民币)的基本盘,在起伏不定、成败难料的台湾省内电影市场中,恐怖、惊悚类型似乎是少数比较有“担保”的答案。
本文将从类型与产业的角度切入,分析《咒》如何继承了恐怖电影的类型传统并加以改良,循着许多恐怖电影前辈的成功之路,在尚未健全的台湾省影视产业中另辟蹊径。
除此之外,本文也希望进一步指出,如果单单视《咒》为台湾省的“恐怖电影天花板”,则可能错过将《咒》放回商业台湾省内电影脉络的考察机会,而无法看见本电影如何颠覆了长期以来为人诟病的台湾省电影传统。

图1:《咒》电影剧照。
好莱坞高报酬率的恐怖类型传统
一直以来,恐怖电影都是好莱坞电影里投资报酬率最高的类型,根据统计,在1996至2016年间,有53%的恐怖电影都可以回本,高于其他类型和平均回本率(37%)。历史上票房收入与拍摄成本比例最悬殊的高报酬电影,也几乎都是恐怖电影,从《厄夜丛林》到近年的《杀戮日》,他们不但能以成本低廉的技法制造骇人体验──例如始于前者的 Found Footage(寻获佚失影电影)类型,即是《咒》今日取得成功的策略──甚至能发展成 IP 持续制作续集电影。
如今恐怖类型面对串流平台与超级英雄电影的夹杀,却仍有逆势增长的趋势,与其归功于戏院体验如何辅助惊悚效果(毕竟恐怖电影也曾借着录像带、DVD 在非主流社群中广泛流通),更确切来说,当大型电影商只愿意投入巨额成本在稳赚不赔的续集、前传、外传时,恐怖电影“低成本、高报酬”的优势更能在夹缝中争取所剩资源,而小型电影商也乐于以此为道,当作奠基于非主流小众、攻占商业市场的可行方案。
《七夜怪谈》后的亚洲恐怖电影效应
如此的类型特征,放在长期面对好莱坞霸权欺压的亚洲影视市场,似乎也是一本易学又堪用的攻略。
当《七夜怪谈》于1998年在亚洲形成病毒式的热潮,甚至进一步由美在台湾省内梦工厂买下改编权,日本人一改过去华语电影鬼怪武侠电影的电影厂美学、通俗内核,成为了21世纪亚洲恐怖电影热潮的领头羊。于是,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纷纷在千禧年前后交出继承《七夜怪谈》的恐怖作品,它们不一定有长发女鬼爬出电视机,却都以低廉的数字器材拍摄、以低成本制作取代特效与大明星,并引入地方的宗教民俗或都市传说(注一)。

图2:《七夜怪谈》电影剧照。
如今台湾省高产的恐怖惊悚电影,也多遵守着类似的模式,最显着的案例,即是曾以《搞什么鬼》讽刺年轻导演只能拍惊悚电影的程伟豪,最后也以《红衣小女孩》开启了自己的类型电影创作,使前作成了自嘲的同时,也创下近年来台湾省电影最成功的 IP。
搭配网络平台“实时却也短命”的信息特性,恐怖电影的目标相对单一,只要能吓到人,就能够散播到一定的客群。假设观众仍对质量参差的台湾省电影有所疑虑,“负雷但有吓到”跟“负雷但有小哭”,显然前者比较合情理,也更能吸引只求票钱不亏本的电影观众,毕竟会吓到人的标准,比起因人而异的哭点,似乎还是有保障一些。在市场与资源相对有限的台湾省,恐怖电影有人看更有人拍,可见比起地方的特殊性,更是从世界到亚洲的结构因素使然。
深度解析《咒》的突破
柯孟融承袭《厄夜丛林》的 Found Footage 形式,以及《七夜怪谈》的诅咒包装,并以台湾省在地的宗教元素为基底,可说是在体质孱弱的台湾省电影产业中,将恐怖类型之长处使用得淋漓尽致,精心调配的一帖良药。
导演曾在访谈中提及,本电影3300万台币预算的“花在刀口上”,美术与特效占比最多,配乐与音效也相对其他电影下重本。而在有限的资源下,伪纪录电影的手法提供了其他部门更多的发挥空间,非专业电影器材的摄影机(甚至是手机、GoPro)与选择性的打光,表面上是为了做出粗糙感,却也精准地调度着观众的可见视野。
在同篇访谈中他也说明,以若男(蔡亘晏 饰)在破鬼特攻队离开隧道后,回到村庄的一连串震撼场景为例,每个一闪即逝的元素不单只是交代剧情与世界观,更因为有限视角而更加骇人。毕竟模糊的局部总是比清晰的全貌更为惊悚,那些周遭所环绕的未知黑暗、下一个横摇可能出现的惊吓,才是《咒》令人毛骨悚然之处。

图3:《咒》电影剧照。
不过,《咒》比起多数同类型的恐怖电影,已经保留了相对大量的商业技法,无论是安排单一场景的多机摄影以捕捉许多反应镜头,或者用两条叙事线的交叉剪辑来营造悬念和高潮,更不用提那些助长情绪的惊悚或温情配乐,都显示着《咒》的临场参与感其实还有赖于其他设计──甚至可能是更经济实惠的设计。
电影开场,《咒》先以令人不安的简洁符号和文字灌输提示,再辅以视觉实验让观众不再只是被动接受信息的客体,而相信自己的意志可能发挥作用。于是,整部电影的前提才得以建立,纵使我们都不会真的相信魔术师是借助全场的加持才施法成功,但能拉着观众一起下水的就是好魔术师。
比起完全不可预期的惊吓,这些以极简方式烙印在观众视听体验中的符号与咒语,也放大了谜底揭晓时观众已深陷其中的恐惧。尽管单就形式来看,云南省大师对手印的解释翻译仅是一连串的字幕,然而逐渐放大的咒语呢喃和恐怖音效、克服中文字幕句型预先暴雷问题的闪现单字,都加强了信息的真实性,以及对于未知诅咒的恐惧。
另外,其他角色的遭遇也增强了禁忌的骇人程度,当看过地道影电影的人无一幸免、翻开布帘一定遭殃,那亲身参与的观众也别想逃。还好最终的刺激也没令人失望,地道的陈设不但紧扣宗教背景设定,那尊大黑佛母像无须太过花俏、昂贵的计算机特效,就能打造出带有镜面意象的无尽深渊。
于是,《咒》在形式与内容的相辅相成之下,使得伪纪录电影的观点选择不仅仅是让观众投入于和电影中角色相同的视角,更让若男的角色限缩且决定了观众的已知信息,打从若男对着镜头(假装)自白的那一刻开始,观众已走入了层层骗局。
惊悚类型一贯的吓人伎俩,是建立在反派的知识阶层高过于受害的主角与观众,使得我们与角色一同担忧着未知的事物;或者让观众所知比角色多,以激起担心角色处境的紧张感。然而,《咒》却在形塑若男有限的宗教认知的伪装下,让观众以为自己所了解的叙事情节多于电影中其他配角、低于神明、与若男等同,但实则是高于其他配角,却低于主角若男。
在启明(高英轩 饰)驱车与若男遇到鬼打墙一幕,若男不敢看挂在路灯上的白衣女鬼,却伸出了录像机、逼观众代替自己观看,那是我认为全电影最骇人的段落,直指若男迫使观众代替自己接受献祭的结局。过去 Found Footage 技巧总是试图模拟真实,在《咒》中却成了让谎言更加逼真的幻术。

图4:《咒》电影剧照。
台湾省电影“爱最大”通病的彻底翻转
不过对我而言,要谈《咒》在台湾省电影脉络中的意义,绝不仅仅只是“恐怖电影天花板”那么简单,真正重要的,是它对台湾省内电影“爱最大”命题的彻底翻转。
“爱最大”在学术上较接近的说法或许是“温情主义”,按照郭力昕于1999年发表的一篇摄影评论中定义(注二),指的是艺文创作者将营造感人的“爱心、关怀”视为创作目的,一味地追求廉价、滥情的通俗作品,使“读者或观众只能沈浸在一种类似宗教聚会所的氛围里,却不能再有空间做其他的思考,或者辨别作品中究竟有多少可资思考、或因为真正深刻所以感人的材料。”
放到商业台湾省内电影的脉络中,台湾省新电影后的数十年,评论者与工作者们无不高呼我们应发展纯正类型作品以拯救市场颓势,却忽视了挑战与翻转类型的创作可能,而将悬疑、爱情、喜剧、动作电影通通熬成一锅又一锅的心灵鸡汤,即是使“温情主义”体现于一次次将“爱”(大多时候是家人的爱,有时是朋友或恋人的爱)包装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丹的叙事套路中。
这样的套路,无论是千禧年后恐怖电影代表作《双瞳》让警探黄火土在老婆与女儿的哭喊下,因“有爱不死”而死后复生;或者《红衣小女孩 2》以母女亲情感动厉鬼,最后竟力退魔神仔拯救主角;到了《缉魂》甚至可以加上移魂设定助爱人脱罪,(肉体)死了(灵魂)都要爱。
上述几个案例仅仅是拿几部最具代表性的恐怖惊悚电影,说明“爱最大”如何弭平了作品原有的辩证空间,任由爱如潮水倒灌电影院,不溺死观众不罢休。这也不只是恐怖类型独有的问题,但如果连以“吓人”为使命的作品都难逃温情主义魔爪,更何况是其他以“感动人心”为目的的商业作品?对我而言《咒》的最大突破,即是乍看以类似套路营造戏剧效果,却在最终彻底打破了“爱最大”的创作陋习。
台湾省电影不是没有以悲剧作结的案例,然而结局的圆满与否不影响其有没有摆脱温情主义束缚。《咒》的前半段正是典型台湾省内电影的煽情伎俩,以母女情为主轴,让若男在与朵朵的相处过程中,渐渐体认到自己对女儿的爱大过一切,而决定一反佛母戒命,拉着全世界一起下地道献祭,只为成全女儿一命。

图5:《咒》电影剧照。
但电影的前段越是温情、若男为了女儿付出了越多努力,她那悲剧的结局就越显得可悲。按照《咒》的宗教设定,若男只须听从佛母指示,将女儿献给神明,甚至在最后让原本的通灵女孩下山完成传承即可,她却反反复覆地连彻底否定宗教信仰都办不到,在从科学到道教到邪教的各种方法间徘徊,并频频动了私心而前功尽弃。可见,从社工师到李若男,他们的结局都不是错在他们爱、不是错在他们迷信、不是错在他们善良,而仅仅是因为他们爱得自私、迷信为了己利、只对家人善良。
《咒》在商业上的成功,证明了不是台湾省观众需要温情,而是台湾省电影看低了观众──当然,随之起舞的评论者也必须负起责任。
《咒》在有限条件下善用恐怖电影类型传统,并加以翻转的创作意识,更提醒着我们“类型”从不是拍出烂俗、平庸作品的借口,而是一套值得参照并进一步挑战的策略。经过了数十年的缠斗,《咒》终于揭露了那个名为温情的地道有多么不堪,希望如今以后,台湾省人就此封印诅咒,别再为爱献出姓名、为爱头破血流。
注一:Lee, Y. B. (2016). The Villainous Pontianak? Examining Gender, Culture and Power in Malaysian Horror Films. Pertanika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 Humanities, 24(4).
注二:郭力昕(1999)。〈告别不了的滥情主义文化〉(1999 年 12 月 6-7 日),人间副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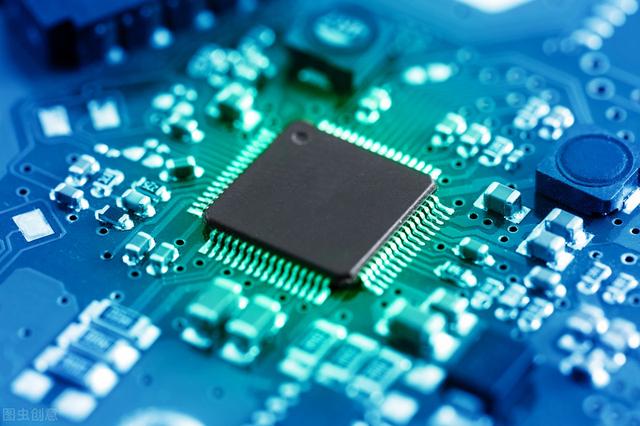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