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萨克斯坦治国理想是新加坡,但纳扎尔巴耶夫的布局只完成了一半
可以想一个问题,一个新独立的国家,国内发展程度不高,没有主体民族,没有强有力的制造业,部族主义跃跃欲试,周边大国环伺,这样一个国家如何实现自身的安全和稳定?
哈萨克斯坦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在1991年真正从苏联独立时,哈萨克斯坦就不得不面对一个原本处于苏联边缘地带、内部充满了各种以削弱本土独立为目标设立的制度和社会结构。哈萨克斯坦原本也缺乏现代国家的建国经验,其所有真正意义上本土的经验都是游牧社会。在苏联解体的浪潮之下,如何建构一个差不多全新的独立国家,便是哈萨克斯坦面对的一大难题。

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文明离婚”后需要“文明再造”,而这个过程中哈萨克斯坦重构了史观,一方面承认俄罗斯对哈萨克游牧文明的“文明再造”,另一方面则将哈萨克描述为自由豪放的游牧民身份,这样避免了对俄罗斯的完全对立,获得了既有源于苏共的哈萨克斯坦高层的正当性,同时也不失自身的自主性。当然,“去俄罗斯化”依然是这一离婚后的必然路径,这点作为哈萨克斯坦独立的基石,也必然在外交上表现为大国平衡的基本政策。俄罗斯对哈萨克斯坦依然有很强的影响力,不过哈萨克斯坦政府始终有着充分的自觉去平抑俄罗斯的影响力,哪怕有大量NGO也在所不惜。
纳扎尔巴耶夫对于哈萨克斯坦有功则于此,他选择了一条强集权的道路,并且能够长袖善舞地维持这种集权模式。哈萨克斯坦的总统权力在议会和法院之上,这一结构让奉三权分立为圭臬的西方国家不满,但确实非常有效地维持了哈萨克斯坦的政治秩序稳定,这就与其他四个中亚国家有不小区别。也因此,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可以保持较好增长,充分发挥在苏联所有加盟共和国中油气资源储量最大的特点,大量出口油气资源获得收益,哈萨克斯坦人均GDP也早早超过1万美元水平,位列独联体第二,仅次于俄罗斯。

在经济可以保障持续增长的情况下,纳扎尔巴耶夫也获得越来越多的手段进行布局和控制,比如在部族主义突破苏联钳制后复兴的特点,形成了以大玉兹为主题,小玉兹为联盟,中玉兹为对手的基本政治格局,确保反对派势力微弱。
纳扎尔巴耶夫也毫不掩饰自己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这种一党独大的政治模式的喜爱,他认为新加坡的模式可以更好地推动国内民主政治发展。他亲自打造了祖国之光党,并对祖国之光党多次表示支持。而从纳扎尔巴耶夫卸任的路径上看,他也试图走出强人政治权力交替不稳定的痼疾,试图利用祖国之光党作为一个理性化的政党、组建国家安全会议、让渡部分总统权力等方式,克制潜在的、个人化政治带来的权力交替难题。这一系列举措也确实说明,纳扎尔巴耶夫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常见的政治领导人,新加坡模式确实对他的执政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当然,新加坡模式的几个基础哈萨克斯坦并不能很好具备。新加坡毕竟只是一个城市国家,新加坡也高度奉行贤能政治,所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规模很小容易协调和凝聚共识,而且这批大量西方一流名校留学背景的高知人士个人能力也颇为出色,甚至如果不是牛津剑桥毕业的人基本无缘人民行动党核心决策圈,这些条件都不是哈萨克斯坦所具备的。甚至可以说,除了少数哈萨克斯坦的权力精英外,哪怕是亲总统的祖国之光党和亲总统集团内部也聚集着大量庸才,哈萨克斯坦无法聚集出比例如此之高的贤能。而利益规模的扩大也让裙带关系变得更难克制,哈萨克斯坦抬头的部族主义也是新加坡不会有的。
因此纳扎尔巴耶夫有理想,不过实际情况来看也不可能达到那么美好的程度。同时,纳扎尔巴耶夫的亲信也毫不顾忌地利用权力垄断大量利益,很显然他们的想法与新加坡差距甚大,倒是与草原文明更为接近。在这一背景下,发展的红利也很难被及时分享,而利益集团为了在国际市场上逐利也不惜破坏本国民众的利益,此次暴乱直接导火索恰恰是这点。从纳扎尔巴耶夫铜像被推倒来看,民众对于亲总统集团的垄断怨言是非常大的。
哈萨克斯坦的国际环境也非常复杂。对于西方国家而言,西方希望的是在俄罗斯和中国的后方插入一些不安定因素,以扰乱、分散中俄的战略注意力和战略资源,其次则是试图更多地获得哈萨克斯坦的油气资源利益。而土耳其的向东战略的主要目标也是利用泛突厥主义在中亚扩大影响力,而中亚国家也对此颇为受用,哈萨克斯坦社会也因此出现了不少“精神突厥人”。此外,由于哈萨克斯坦在与俄罗斯“文明离婚”的过程中也复兴了伊斯兰主义,这让宗教极端主义有了生存的空间,宗教极端主义也在哈萨克斯坦社会内时隐时现。颜色革命、宗教极端主义是哈萨克斯坦一如既往存在的问题,而泛突厥主义则可能与宗教极端主义合流,会是未来的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此次未遂政变中,这些力量都或多或少地粉墨登场了。

目前来看,托卡耶夫通过此次暴乱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但是本质上不论是政变派还是托卡耶夫派,他们都来源于纳扎尔巴耶夫的集团。因此,纳扎尔巴耶夫的布局倒不能说是完全失败的,只是他没有解决的问题在于集团内部的权力交替,以至于反对派能够发动数万武装人员进行夺权。这也是非常草原式的政治事件,哈萨克斯坦如何真正解决权力交替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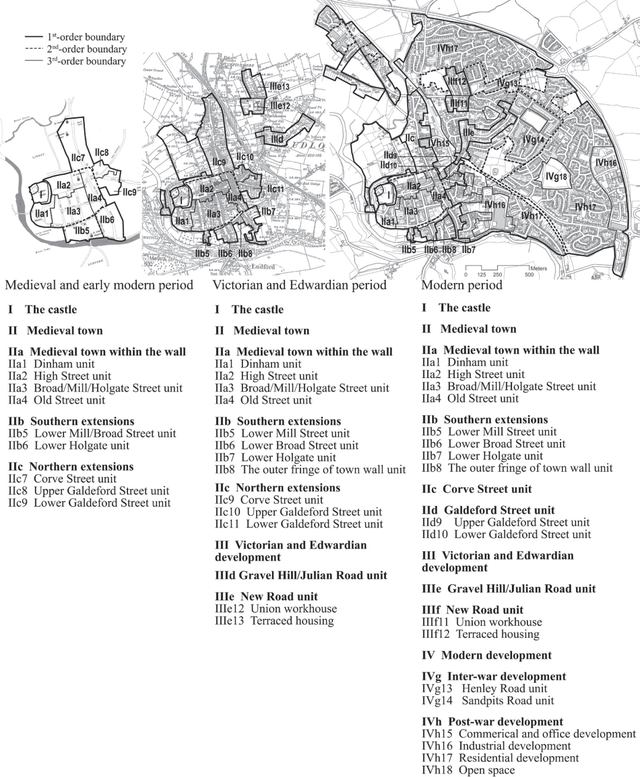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