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海谈中国的关羽信仰
王兴/采访、翻译

田海(Barend ter Haar) (章静 绘)
关羽败走麦城,后为吴军俘杀,此后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成为重要的神祇,被尊为关公或关帝,至今仍受民间敬奉。德国汉堡大学汉学教授田海(Barend ter Haar)的著作《关羽:由凡入神的历史与想象》(Guan Yu: The Religious Afterlife of a Failed Hero)结合大量史料遗迹及田野调查资料,考察关羽的成神之路,追溯相关信仰的历史演变,揭示了口头文化在其中的关键作用。田海教授曾先后任教于莱顿大学和海德堡大学,2013-2018年任牛津大学邵逸夫中文讲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传统中国的宗教文化、萨满文化、当代中国宗教、中国文学等,代表作有《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天地会的仪式与神话:创造认同》等。在《关羽》中译本出版之际,《上海书评》邀请田海教授门生、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王兴副教授就传统中国的关羽信仰采访了田海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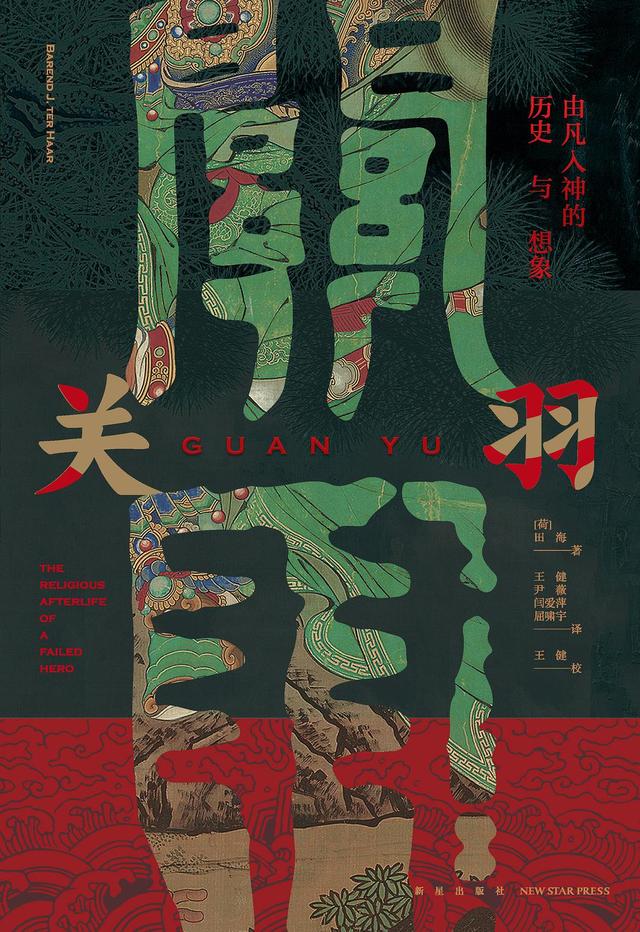
《关羽:由凡入神的历史与想象》,[荷兰]田海著,王健、尹薇、闫爱萍、屈啸宇译,新星出版社2022年2月出版,348页,78.00元
能否请您先简要介绍一下《关羽:由凡入神的历史与想象》这本书的缘起和研究经历?
田海:研究的缘起背景比较复杂,我只能简要说一下。我对这个话题的兴趣最早是在1982-1984年留日时期开始的。当时我对于用地图和统计数据解决历史问题很感兴趣,而且那是在电脑普及之前。我当时认为学者可以通过研究某一种文化现象在地理图像上的分布和这些地理分布变化的时间线来解答文化现象的口述传统与书写传统出现先后的问题,特别是宗教文化中某些重要神祇信仰对应的口述文本与书写文本如何产生——关于关帝这种重要的神明信仰应当放在这样的框架中去理解。但是当时的这个计划被博士论文关于白莲教的研究打断了,而且同时另一位美国汉学家芮乐伟(Valerie Hansen)正在进行类似的研究,我就没有将这项计划继续下去。另外,关于关帝信仰的材料体量庞大,我当时很难找到一种比较好的叙述模式来整合这样庞大体量的材料,整个研究就暂时搁置。比较令我沮丧的是,我本来在日本的图书馆中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关于关羽信仰的材料,可当时没有把研究成果出版。当我在2012-2016年重新开启这项研究的时候,发现很多学者尤其是中国的同行们已经开始非常主动地投身于这个话题,而且出版了很多研究文献。此时利用电子工具尤其是数据库来整合研究资料已经变得非常容易,因此我的这些研究成果看上去似乎是建立在近两年的前人研究和数据库资料之上的一项全新的研究,但实际上我对于理解关羽信仰口述史与地理文化分布关系的构想是大概四十年前在日本进行文献研究时开始酝酿的。另外就是,对于关羽的圣传化研究是我另一个灵感来源,这一点在我书中有所提及。

在您的研究调查和田野工作中,对哪一地区和历史时期的关公信仰印象最深呢?您能否简要描述一下比较有趣的经历?
田海:当我开始进行这项研究,尤其是开始接触一手史料的时候,我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内容。对我来讲整个关羽信仰在中国的历史演进如同一幅巨大的拼图。但是如果要让我选出研究中印象最深的地方,那么应当是那些能够帮我理解关羽信仰整体语境的诸多有趣的蛛丝马迹。比如发现某个遗址中龙的传说帮助我更好地理解早期关羽神话的产生。这些看似细小的蛛丝马迹背后实际上是某一时期整个关羽信仰语境的缩影。另外让我惊讶的是,我们历来已知的关于关帝的宗教常识实际上是基于很晚才出现的宗教传统而非古老的习俗。还有一个最让我惊奇但是在书中没有详述的话题是晚清时期发展出的关帝信仰的全新层面——作为救世主的和扶乩神的关帝。所幸另一位法国汉学家高万桑(Vincent Goossaert)和其他一些学者已经对这个话题有持续的讨论。
您的书中提到,以口头文化为载体的关公信仰可能是最早传播的基本形态,而非佛教道教的信仰,您能详细解释一下通过历史文本研究口头传播宗教的基本思路吗?什么是“口头传播”的宗教呢?
田海:通常来讲,口头传统的研究会面临很大的困难,因为过去口头的东西无法留下太多历史线索,更不可能有现代社会的视频和音频材料保留下来。但是口头传统往往又很容易进行常识性的想象和推演。举个例子,在一个家庭或者大的亲属宗族单位中,养育孩子和传播家庭内部的一些流言轶事非常常见。在我自己的家庭中,我们经常会讲我的高祖父(爷爷的爷爷)的一则故事,而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十九世纪,死于1925年。他是荷兰十九世纪晚期一位非常活跃的政治家。他曾经收到过一只由他的选民猎杀的野兔作为礼物,但是这同时可以被解读成一种贿赂。我的这位高祖父有着强烈的道德感和原则性,因此即使是收受贿赂的嫌疑对他来讲都无法接受,但他也没法把这份礼物原物奉还,因为这只野兔在到他手里时已经开始腐烂了。因此他的家人吃了这只野兔,之后把等值的现金寄给了这位选民。我这里讲这个有趣的家庭轶事是为了说明我的家族已经反复口头传播这个故事超过一个世纪,而很有意思的是今天的这份访谈稿是这个故事在二十世纪唯一的书写来源,而且还是被翻译成中文的版本(因此口头传统与书写传统之间有着巨大的时间差)。
可见研究口头传统有着显而易见的困难,但并非完全不可能。一旦书写文本在某个节点介入到一种文化中,口头传播的内容就有可能偶然地被写下来。书写文本可能会影响人们的生活,但是更普遍的现象是口头文化实际上在人们的生活中(至少在古代)还是居于统治地位。透过书写文本去理解口头文本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研究思维的转变。那么问题就只是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讲——包括我个人在内,我们这群人都精通文字和高等教育的思维体系,而令这些专业历史学家在心理上接受口头传统的重要性实际上非常难。我在另一本著作《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中已经详述过口头故事的巨大影响力,关羽的研究是另一有力例证。1983年当我还是一名在日本的留学生时,开始着手人生第一个专业研究计划,当时我就已经对中国帝国晚期的神明崇拜来源于像明代《三国演义》这种书写文本的看法抱持高度怀疑(在当时是一个被接受的学术观点)。因此我开始搜集各种关羽神祠建立和重建的日期信息。就像我在自己的书中已经详细解释的一样,如果关羽崇拜在印刷书籍的影响下不断传播,那么我们应该能找出关羽崇拜活动和神祠以文人团体为中心分布的证据——比如早期长江下游的关羽信仰应当有最庞大的文人信众——但事实并非如此。另外,关羽的传说也应当与印刷出的小说相一致,但很遗憾史料上也无法支撑这一点。这些我在本书中都做出了详细的说明。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作为佛教伽蓝和道教护法出现的关帝,实际上是日渐成熟的口头传播的关羽信仰影响精英宗教的一种结果?
田海:其实这里“佛教”“道教”一类的词汇非常有问题,因为古代中国人很少将他们视为独立互不相干的宗教类别。但更重要的是,我试图提出佛教与道教版本的关羽实际上没有任何区别。在任何语境里,关羽的主要角色都是降妖除魔——不论是引起干旱的恶龙(这是与天台宗智顗有关的一则传说)或是在山西解州盐湖或其他任何地方引起天灾的妖魔——而这一形象的产生最初实际上和佛教道教都无关。
您在书中提到,不仅仅是佛教道教的宗教话语,连与三国时期有关的史书和文学都不是最早关公信仰的起源,反而是灵验奇迹促成了不同地区对关帝的集体崇拜。但就这一点来说似乎有些反常识,一个地区在树立某种神明信仰,并且通过宗教物体、空间和仪式具象化这种信仰的时候,难道不会从某种精英文本的原型中寻找神明身份的信息吗?或者说,是否有一套口头信仰的历史叙事实际上长期存在于不同的信仰团体之间?
田海:很有意思,实际上你的问题应该是预设了大部分我这本书的读者脑中都会有的一种思维定式。但是为什么不识字的民众必定会从书写文本中创造自身的文化呢?这本身就是反常识的。如果真的是这样,识字率极低地区的宗教文化究竟如何从书写文本中汲取灵感?我并非反对书写文本对宗教生活的影响力和重要性,但是我也认为书写文本的这种影响力是逐渐在历史中发展出来的,而且我们需要对这种影响的程度进行谨慎的评估和研究。我们不能假定书写文本永远作为口头文化与实践的唯一来源。关羽的案例为我们提供了有力证据,证明宗教崇拜的传播与小说、阅读文字的文化分布相迥异。相对地,我认为戏剧文化与这类信仰的传播非常相关,但是在一系列关羽戏剧中带有明显宗教标志的人物是阎王和关羽,而非关羽崇拜中的重要神明。所以我认为任何在相对偏远和低识字率的乡村进行田野考察的研究者都会强调口头文化依然非常重要。我刚才说了我的家族轶事,即便不是低识字率家庭,口头传播也一直是家族历史传承的主体。我的祖先十七世纪(也就是中国的晚明)从德国移民到荷兰,大多是法律文献的专家,在十七世纪之后的两百多年也都是荷兰比较富有的精英家庭。刚才提到的我的政治家高祖父就是法官兼法学教授,也是一所大学的校监。很明显,讲述和传承一段完全脱离文本的口头历史在所谓的“文化家庭”也是非常常见的。那么作为对你和对中国读者的问题的一个回应,我只能说书写文化或许对口头文化有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的程度亟待证明(或证伪)。在此之前我们不能默认口头文化的现象一定来源于书写。

您在书中提到,您反对学界一种中国帝国晚期宗教神明“标准化”的说法,您能否结合关羽信仰的问题详细谈谈呢?
田海:著名的汉学家华琛(James Watson)自1985年开始提出中国民间宗教“标准化”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人类学家未经批判地阅读史学材料时常犯的错误。在华琛的理论中,他主要考察帝国晚期福建地区的方志,然后发现天后娘娘或妈祖信仰在此地广泛传播,而这些地区的文献中不再大费笔墨提及其他神明的信仰。因此他认为这就证明了晚期帝制中国民间神系的标准化(或固定化/原文:standardisation)。他实际上犯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地方志本身只对政府官方封号认可的地方信仰较为推崇,而基本不载没有被政府和精英集团纳入到正统神系的信仰。由于妈祖信仰是当时这一地区几种官方认可的地区宗教崇拜(就像关羽崇拜一样),因此这一信仰其实表面上看上去在不断取代一些原有的崇拜体系。但是我已经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系列论文中证明华琛的猜想是错误的(如"The Genesis and Spread of Temple Cults in Fukien", in: E. B. Vermeer ed.,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Fukien Province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Leiden, pages 349 – 390;"Local Societ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Cults in Early Modern China: A Preliminary Study" in:Studies in Central and East Asian Religions 8: pages 1-43)。事实上,华琛的猜想在南方中国尤其是长江流域基本是不确切的,只有在北方中国的局部地区有一定适用性。我自己的论文一开始并没有受到重视,而华琛的著作影响巨大,导致标准化的研究框架被学界所接受。
您又是如何理解美国学者芮乐伟(Valerie Hansen)关于宋代以来中国宗教越发实用化、市场化的论断?您认为宋明清三代关羽信仰越发实用化了吗?
田海:其实芮乐伟是我很好的朋友(详见本书序言),但我不完全同意她的观点,我想她应该不会介意。包括我们称之为教义化的佛教、道教和其他类型宗教的中国宗教文化都有非常实用的一面。Ian Reader和George Tanabe两人已经提出,佛教自产生之初就有非常实用的面向。我们读一读《妙法莲华经》就能发现关照现世生活的“实用”内容有多少!当然这也完全不令人意外。只有非常非常非常少数的人关心宗教文化中的哲思、教义层面。大多数人对于宗教实践都有着具体的、个人化的诉求与目的。我们能够推测的是,十一世纪开始的前所未有的商业扩张很明显影响到了中国人的宗教生活。人们的实用需求——包括商业层面上的需求也在不断复杂化,因此不出意外我们当然能找到关于奇迹、灵验故事中这方面不断增长的主题。但这不是因为十一世纪之后中国宗教的本性发生变化,宗教生活一直紧密地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联系在一起。我只能说我在这一话题上依然是马克斯·韦伯和卡尔·马克思的粉丝,因为就宗教的实用层面,经济生活所塑造的文化思维一直与宗教伦理不断互动。

您认为整体来看,历史上中国的关羽信仰能反映中国人精神世界与文化生活的某些特点吗?
田海:我不大确定如何评价精神世界的问题,但是很多人被关羽的故事启发。我可能把这些故事看作史实上失真的故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故事的内容和影响可以被忽略。举个例子:我个人并不认为关羽真的是一个非常忠诚的人,因为他加入了一场三世纪早期对抗天子与朝廷的起义。但是或许根据历史记载来看,他对以刘备为首的小团体极为忠诚。在关帝历史的神圣宗教叙事中,他不仅是忠诚与正直美德的代表,还是非常关心地方民众命运的一位慈悲的神明,我想这是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扶乩活动中关羽地位显著的原因,因为他被看作是一位可靠的预言者。这大概是能够反映中国人共有价值取向的一个细节。
您如何理解当代华语世界的关羽信仰呢?在大陆南北两地以及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关羽信仰有什么新的变化和现象吗?
田海:我的专著并没有着重研究古代中国之外的关羽信仰发展。这是另一个宏大的话题。但是我对于一种在中国大陆之外持续传播的现象——关羽扶乩非常感兴趣,这种扶乩活动甚至在越南都有很长的历史。
您有哪些话想和中译本的读者说呢?您希望中文读者如何阅读您的这部著作?
田海:我希望中国的读者通过我的书能够开始真正关注自身文化中的口头传统,而不是将他们视为一种书写传统之下的不重要的现象。另外,我非常高兴能够把我自己的分析和想法分享给别人。我从之前在中国和日本的实地研究中受益良多,但是我也与中日两国的学者有些分歧。因此我认为能够通过本书的中译本将良好、健康的学术争论继续下去是一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我期待能够再次到中国旅行!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张亮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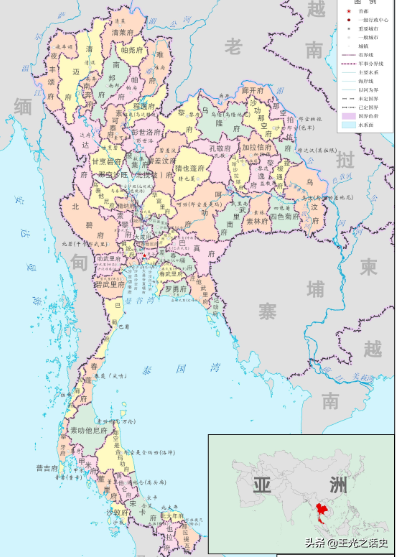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