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鹤:早稻田大学藏书一瞥

一个大学的名气由许多方面的因素所造成,其中图书馆的好坏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图书馆的好坏又不单由藏书的数量来决定, 更重要的还在于其质量。贵重书、罕见书的多少是尤为学人所看重的。在日本,由于中日文化的特殊关系,收藏汉籍的数量与质量更是判断图书馆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早稻田大学是日本的“ 名门” ,其图书馆自然也有特殊之处。
藏书数量之大自不必说──号称有420万之巨,质量尤为上乘,有些藏书或资料何以会到这个大学来,简直令人感到意外。
首先值得介绍的是《玉篇》和《礼记子本疏义》写本残卷。这两件都是中国唐代写本,但现在却都成了日本的国宝。
《玉篇》为南朝梁代顾野王所著,是东汉许慎《说文》以后最重要的字书之一。其原本自然早已不存,宋代所刻《大广益会玉篇》又因后人的增删改窜而失其真,只有此唐代写本最能体现其原貌,所以其学术价值自不待言。这一写本能保留一千三四百年而至于今天,不能不说是万幸,所以即使残篇断简也贵重无比,日本将其定为国宝是有道理的。值得一提的是,同一唐写本的《玉篇》残卷分成四段,藏在日本的四个地方。
早稻田大学所藏部分最长,达1306厘米,内容为第九卷言部第92字“谕” 到幸部第117字“ 执” 。其他三件分别藏在京都的大福光寺与高山寺以及滋贺县的石山寺,这三件当然也都定为日本国宝。日本虽然也有兵燹战祸,但由于日本人崇尚佛教,所以破坏止于佛门之外,这就是藏于佛寺的书籍与资料得以长期保存的原因。高山寺与石山寺两段合起来是《玉篇》完整的第二十七卷。大福光寺则保存了卷二十四鱼部的19字。
一百多年前我国著名学者杨守敬访书日本时曾借高山寺残卷影写,刻入《古逸丛书》中, 但未听说及于早稻田大学的这一部分。早大的《玉篇》残卷曾藏于九州秋月藩主手里,后来入于皇宫,又于1914年由宫内大臣某赠于该校。但其初如何流传到日本,就没人说得清楚了, 只能抚卷长叹。
《礼记子本疏义》唐写本残卷内容是《礼记·丧服小记》第十五的疏义,南朝陈代郑灼所撰。罗振玉认为此写本是六朝写本。据《唐书·艺文志》, 梁代皇侃著有《礼记义疏》五十卷。此郑灼即其门人。此卷卷尾捺有奈良时代光明皇后所用的“ 内家私印”,大约就是当时从中国传入日本的。此书在中国早已佚失,不但不知其如何到的日本,并且在奈良时代以后也不知道经过怎样的九九八十一难,而忽然在明治二十三年(1890 年)出现在东京琳琅阁书店(此店名现在犹存,在东京大学附近,当时则在下谷池之端)。
在此之前,杨守敬不惜重金搜购中国流入日本典籍的行动已经尽人皆知,所以有某日人劝宫内大臣买下,以免流出日本国外。该大臣买下后又复制多份以赠同好之学人。明治三十八年,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的首任馆长要求宫内大臣亦送该校一份复制件, 没想到天上真有掉馅饼的时候,送来的竟然是原件!
1931 年,此写本与《玉篇》残卷同时被指定为日本国宝。一个大学而有两件国宝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这不但是该图书馆的荣光,也加重了早稻田大学作为名牌大学的分量。
一个图书馆光靠自身在市场上采购当时出版的书籍是不大可能产生丰富的(指数量与质量两方面)馆藏的。必须有专门家与学者私人藏书的赠予或转让,或其他库藏的并入才能造成一座著名的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从成立伊始,就不断有人赠书,从清朝驻日本留学生监督钱恂所赠予的汉籍,到日本海军部移赠的俄文图书,不一而足。
私人藏书的寄赠更是重要。日本许多大学图书馆都建有以学者命名或以专门命名的各种文库,是一个增加图书馆库藏与提高图书馆水平的好办法。这些学者大多独具慧眼,不但能注意到一般学者都了解的珍本秘籍,还能从自己的专长出发搜集一些旁人看来无关紧要甚至是无用的书籍。因此以文库的方式保存这些藏书不但可使后来者了解这些学者做学问的途径,而且如有同好,利用这些集中在一起的藏书也很便利(我国尚未有实行此法者,即使有些教授遗赠为数不少的书给学校,这些书也往往按类别分散开来, 查找十分困难)。
如早大图书馆的洋学文库就是几位洋学者(研究西洋学问的学者)的捐赠组成的,其中颇有一些罕见的书。如《英话注解》一书,是咸丰年间出版的一部初期我国学习英语的读本,用宁波话注音。这类书的木刻本极少见,包括被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改编的《华英通语》在内,至今发现的只有四五种而已。而此书在我国未见有图书馆入藏,在日本也仅见早稻田有,尤其可贵。这个文库还有许多相关书籍,如1850 年出版的《英粤词典》,如麦都思的《英汉辞典》,集中在一起,对照比较很方便。
早大图书馆已经整理并开放的文库就有20个,还有未整理的不计。这些文库不可能在这里──介绍,正好今年风陵文库开放,就拿它作例子。风陵文库为原文学部教授泽田瑞穗所赠,以黄河山陕间的风陵渡为名。泽田先生40年代到过北京两次,收集了许多与中国民间生活习俗有关的书籍和实物。其中有他研究的专门“宝卷” 类,还有清朝末年颇为常见的宣讲圣谕一类的书,更有清末民初民间流行的俗曲、鼓词、剧本、笑话、相声等,还有皮影、对联、灶君神像,甚至冥纸。这些书籍数量达三千多部,过去被看得一文不值,现在自然也进不了善本书的行列(也许其中一些明代的宝卷,今后可能会进),但却是地地道道的罕见书。就以我所特别注目的那些宣讲书而言,就不但是中国公私藏书均不见,即其他国家也未遇到。
在巴黎,我虽然曾看到不少在康熙年间出版的阐释圣谕十六条的书,也是极为罕见的,但那些书均为达官贵人所刻,无一是坊间流行的。只有泽田先生有心于此才收集了这些虽然刊刻粗糙,却是做相关研究必不可少的宣讲书。康熙圣谕宣讲了一百来年,多是老调重弹, 引不起老百姓的兴趣,有些宣讲人于是另辟蹊径,多以因果报应的故事为主题来吸引听众,使枯燥的宣讲形式变成为一种有趣的娱乐行为。这些宣讲内容被编成书,销量大概不小,所以越出种类越多。但这类书素来为有识者所看不上,从未有人加以收藏,因此今天无法在图书馆里找到。我因为打算将清代诠释康熙《圣谕》与雍正《圣谕广训》的书辑为一编,几年来颇注意此类书,才真切地感到泽田先生有眼光,为研究者保留了这么些宝贵的资料。
其他如著名数学家小仓金之助还在世的时候就寄赠的大量数学书,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为此而建立了小仓文库。其中日本算书、天文书九百多部, 中国算书、天文书三百多部。由于是专家藏书,所以同一书的不同版本也尽量搜罗殆尽,以资比较。往往同一部中国算书就有明版、清版与朝鲜版、日本复刻版多种,大大方便了后来的研究者。还应赘上一句的是,由利玛窦与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初版本(万历三十五年,1607)也被囊括在这一文库里。
图书馆不但藏书还应收藏各种资料,包括重要文书。早大图书馆就有好几种文书极有价值,其中以该校创办人大隈重信为名的大隈文书,以原长崎藩主大河内辉声为名的大河内文书最为重要。大隈文书中有一通1914 年孙中山给大隈重信的信,一开头就说:“大隈伯爵首相阁下,窃谓今日日本宜助支那革新以救东亚危局,而支那之报酬则开放全国市场以惠日本工商。此中相需至殷,相成至大。” 此时孙中山正遭遇二次革命的失败而亡命日本,意图以某些条件换取日本方面的援助。
大河内文书则是原长崎藩主大河内辉声在明治十年前后与包括中国外交官员、学者以及一般人笔谈的原稿。这些笔谈数量很大,最多的一年,就有178次记录。笔谈的内容涉及面很广,其中论诗文、评书画的占了很大部分,表现了明治初年中日人士交往的一个侧面。
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曾对该文书下了很大的研究功夫,写了介绍评论与翻译并重《大河内文书》一书,又与新加坡学者郑子瑜一起,将笔谈中有关黄遵宪的部分整理出来,出版成书。但实藤先生从善意出发,只写了中日友好的一面。其实其中还有辛酸矛盾的一面。与大河内辉声交往最深的是王治本。这是一个考不上进士做不上官的读书人,为了谋生,来到日本。先被大河内尊为老师,向其学习汉诗汉文,后来因为区区薪水问题,两人闹得几乎要不欢而散,双方来往信件都口谈义而实为利。大河内将其与王治本的笔谈及来往信件都保留了下来,题之曰漆园(治本的号)笔话。我们今天看了,对名为师弟实为主仆的两人关系会有实质性的了解,在义与利发生矛盾时双方如何在保护自己的蝇头小利时攻击对方。这是不加修饰的赤裸裸的社会史的第一手资料。当时王想要把这些来往信件销毁,大河内不肯。好在不肯,一百多年后让我们看到了人性被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所掩盖的另一面。
早稻田大学好书委实不少, 不是一两篇文章的介绍所能概括的。六年前我为了查阅日本学者长久保赤水的《唐土州郡沿革图》来过这个图书馆,就对其藏书有初步的印象。这次呆的时间较长,感触就更深。最后再随意举几部中国学者会感兴趣的书,以见其藏书之质量。一本是徐松的《西域水道记》。此书中国也有,不算稀奇,稀奇之处在于它是徐松自己亲笔的校注本,此处无法详言,当另文专述。另一本是《China Monumentis, Naturae& Artis》,1667 出版。作者Athanasius Kircher是耶稣会士,又是著名学者,精通自然科学、语言学、考古学和音乐。他在此书中翻译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详述了马可波罗以来的中国的生活、习惯、宗教、自然、艺术等方面内容,并配以精美的铜版画。此书即使在欧洲图书馆也极少入藏,可惜至今未有中译本。
应该庆幸的是,早稻田大学既躲过了1923 年的关东大地震,又免遭二次大战时的空袭,因此藏书基本上未受损。东京大学图书馆在大地震时就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我曾说到书之厄有四:水火虫兵,愿所有图书馆都能永远避免这四厄。
原刊《中华读书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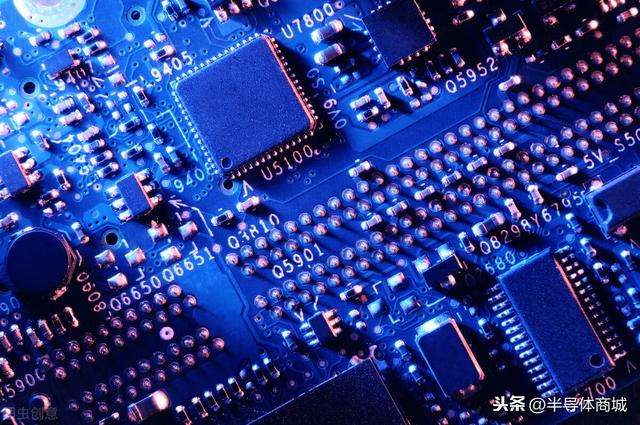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