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孤岛求生”的那些事
作者:刘梦蝶
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特别的话题——孤岛求生。可以说它一直是一类受创作者青睐的题材。不管是在文学领域、影视,还是游戏,故事的构造者都乐于将故事放置在这样的一个环境,抑或说装置里。
电影《大逃杀》《饥饿的游戏》就是让落难者在主使者营造的孤岛上互相残杀的延伸设定,文学上的突出代表《鲁滨孙漂流记》甚至会被戏称是“种田文”的鼻祖。
拥有多样变种的孤岛求生其实可以拆分为两个核心要素,正如它的字面想要传达的那样,一在“孤岛”,二为“求生”。“孤岛”场景重在强调与世隔绝的条件,弱化外界的存在。根据作者的意图,这种场景会对角色产生正向或负向的影响。
角色到达孤岛后,就将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求生。它是故事的核心内容,也是孤岛上角色的目标。在极端的生存压力下,人性会迸发出闪耀的光辉还是暴露阴暗的脓疮;为了生存,文明人会委身野性,还是坚守道德和秩序。可以看出,孤岛求生深层次上是一种对既有环境和规则的打破,现代社会用秩序井然的框架让人远离生物间的弱肉强食,可同时人类也要继续在有限的资源中拼搏厮杀,这种对决更为文明,但残酷的程度绝不会减少。
在依靠法律、权力、技术等所编织的牢笼中,规训与惩罚对人的身体、行为、主体的塑造将人逼向了“异化”的边缘。人何以为人?一些人选择了在更为原始的环境中寻找答案。当现代人被剥夺处于需求层次最底端的生理以及安全需求时,他们是否就能展露压抑的本性?答案在文学和艺术的领域中千姿百态,而现实中真实发生过很多类似的事件。在没有人工卫星和GPS定位系统的年代,遭遇海难而被放逐孤岛的意外时有发生,留下记载的也不少。
在这些记录中,有一位女性的遭遇就更为离奇而富有传奇色彩了。
一切还得从1836年的一场海难说起。一位名叫伊莉莎·芬瑟的苏格兰女性同她的船长丈夫乘上从悉尼开往新加坡的航船。不幸的是,船沉没了。伊莉莎同她的丈夫漂流至孤岛沦为当地土著的奴隶。
伊莉莎的丈夫没多久就死于饥饿(也有因为伤口感染致死一说),而她本人终于在一位爱尔兰犯人的帮助下逃出生天。回国后,关于伊莉莎的事迹在伦敦广为报道。而后,人们将她落难的岛屿冠上她的名字。位于澳洲东岸、世界上最大的纯砂岛也就由此得名。
当然,伊莉莎本人并没有留下日记或相关文书记述她的心境,这也就给了其后的创作者们以更大的想象空间来发挥。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怀特就这位女士的事迹专门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树叶裙》。在书中,他沿用了伊莉莎沦为奴隶和获得犯人帮助的设定,并为女主人公增添了完整的身世背景和情感纠葛。但怀特的本意并不是创作一部新颖的冒险小说。
《树叶裙》[澳大利亚]帕特里克·怀特 著 倪卫红 李尧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在《树叶裙》中,他探索了作为个体的艾伦·罗克斯巴勒夫人内心深层广阔的世界,并以艾伦的双眼为媒介,再现了19世纪尚处于殖民地时期的澳大利亚原住民的生存境况。在艾伦寓意纷繁的意识流中,怀特借机探讨了种族、阶级、性别等后殖民时代所要面对的议题,从而兼顾了故事本身的趣味性与意义表达。
故事中的艾伦是康沃尔乡村的一个平凡农家女孩,她的青春是在挤牛奶、帮父亲干杂活中度过的。机缘巧合下,她同暂居在家里的英国贵族罗克斯巴勒相爱,结婚后成为受人尊敬的贵妇人。而严厉的婆婆要求她遵循烦琐的礼拜仪式,叮嘱她记日记提升素养。家中的仆人对她时而冒出的粗鄙之语议论纷纷,沉迷阅读、身体虚弱的丈夫也无法帮助调节枯燥的生活。这样的身份割裂感让艾伦无所适从,属于她本真的性格被压制,她的一举一动被规范和约束。
直到他们登上从澳大利亚返航的航船发生海难为止。她目睹丈夫在沉船前只护住本无用的诗集,最终死在原住民的矛下;她见到阅历深厚、久经风雨的船长只剩下一摊腐肉和骨架。她的礼服也被土著的女人们扒下,只能用芦苇叶围成一条树叶裙遮挡身体。在同原住民共同生活后,她的金色长发被用石片割断,白皙的皮肤也被黑泥覆盖,属于她的特征被一一剥去。在原始的弱肉强食中,艾伦反而从强调身份等级的父权社会中解放了出来。她无须考虑尊严和仪态,与狗争食、攀树捕鼠,适应变化的环境。即便在无数个夜晚,婆婆还是会来到梦中问她是否有写日记,丈夫的婚戒还是锁在树叶裙上提醒她应该回到的世界。
艾伦最终脱逃成功,当她打算遗忘那段经历时,手上粗糙的厚茧、囚犯鄙夷的眼神和同为海难的幸存者又向她发出质问。乡村出生的农家女、高贵的罗克斯巴勒太太和原住民的奴隶,三重身份在艾伦的内心深处激烈交战,亦像处于殖民统治下的澳大利亚大陆,文明和野蛮不具备绝对的界限,它们共生在同一具身体中。
故事中存在多处对后殖民主义的隐喻。原住民俘虏艾伦后,首先就是通过发型肤色的塑造让她与族人同化,试图以此消除他们对白人压迫者的恐惧。而这种异样的外貌会同时激发出恐惧和敬意。在男人们出去打猎时,女人们又会围绕在艾伦的身边举行尊神的仪式祈祷丰收,将她视为高等的存在。
当回到英国殖民者统治的区域,艾伦被权威的代言人司令官传唤。在司令官的背后是现代社会森严的法律与秩序,只有被他判定符合现代法律的人才有资格回到文明世界。如果司令官得知艾伦曾贪婪地啃食人骨,她无疑会被加入高坡上看到的女囚犯的行列。她虽隐瞒了这部分真相,但骨与血中已留下原住民文化的印记。在她的内心,狂放、野性与对解放的向往让她走在文明与野蛮中间的独木桥上,这让人不禁想起澳大利亚暧昧的历史。何为澳大利亚自身的特征?即便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已所剩无几,他们留下的痕迹也仍诠释了澳大利亚这一地域。
本书的作者帕特里克·怀特在1973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时,他的获奖理由是“他以史诗般的和擅长于刻画人物心理的叙事艺术,把一个新的大陆介绍进文学领域”。经过历代澳大利亚文学家的努力,澳洲文学已然不会被看作英国传统文学的延伸,在文学之林中建立起自身独有的特色。
作为一个出生在英国的孩子,怀特的小说背景虽一贯着陆于澳洲,但可以说他不管是对自己出身的家庭,还是那片大陆的感情,都是复杂的。在他的自传《镜中瑕疵》中,他提到“父母很为我这个娇弱的儿子伤脑筋”,他们总是用羊毛制品严严实实地包裹着他。年少时便患上哮喘的他自然与有着结实肌肉的强壮男孩们不同,家人的视线里他是一个体弱多病、弱不禁风的孩子,而这样的孩子要想作为未来的农场主是令人担忧的。
这样的疏离感让他选择在13岁就前往英国的中学留学,并多次往返。这种处于边缘的陌生感让他在作品中比起关注宏大的历史叙事,更关心作为普通人的情感和命运。尤其是跨越民族、国家界限,同他一样身份暧昧并为此苦恼的个体。
他将史诗的真实和诗歌的感情熔于一炉,烘焙出别具一格的美感。他想要传达给读者的是作为具体个体的价值,这一价值必然超过当前迅速发展的文明所能提供的一切。(刘梦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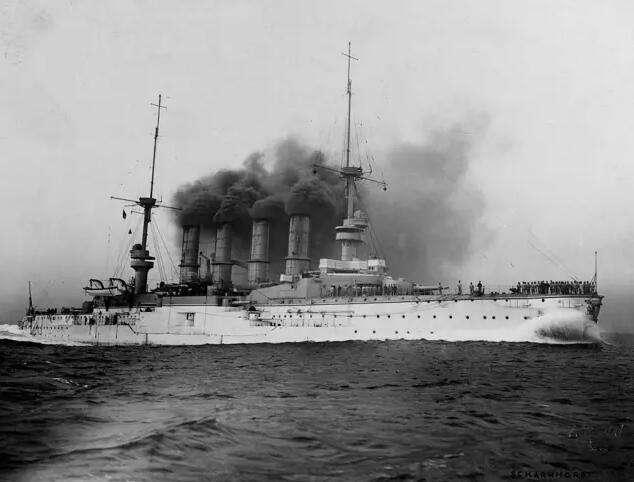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