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人文学项目化管理的利与弊
陈平原
关于学术评价与人才养育,我写过好多文章,在学界有不小的影响,最常听到的反馈是:你说得很好,也很对,但没用,因大势已成,格局早定,谁也扭转不了。这我承认,但只要有机会,还是要说。就好像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文化遗产保护,以及学科评估指标设计等,只要认准了方向,一而再再而三地唠叨,多少还是起作用的。越是弱势群体,越需要奋起抗争,只是必须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心理准备。
这回不太一样,是体制内的思考与献策——具体说就是复旦大学国家智能评价与治理实验基地主持的会议,名曰“反思与探索”,但我希望主要不是发牢骚,也不仅仅是做文章,最好有些微的实际效果。因此,我倾向于“老调重弹”——不是说重要的话要说三遍吗?下面的发言,夹杂自我引述,有的反省,有的坚持,有的则进一步发挥,最后落实为若干建设性意见。
七年前,我在北大校园接受复旦大学“人文社科评估标准项目”课题组专访,那次答问的内容,以《人文学科的评价标准》为题,初刊2016年4月6日《中华读书报》,收入我的《文学如何教育——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东方出版社,2021)等。其中涉及今天我想着重讨论的项目化管理,主要是以下三句话:第一,“项目经费对于社会科学和理工科特别重要,但对于人文学科的意义不是很大——除非你做大规模的社会调查、资料搜集等”;第二,“我反对用得到多少经费来看待一个学者。评判学者,既要看他的学术成果,也看他的教学情况,唯独拿多少钱不重要”;第三,“有些擅长编列预算做大项目的,把很多年轻学者拖进去,把一届届博士生、硕士生也拖进去,弄不好,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呀!”因人各有志,且才华有大小,什么是人文学的最高境界,这里不想争辩,只谈谈以项目管理为标的的“计划学术”之利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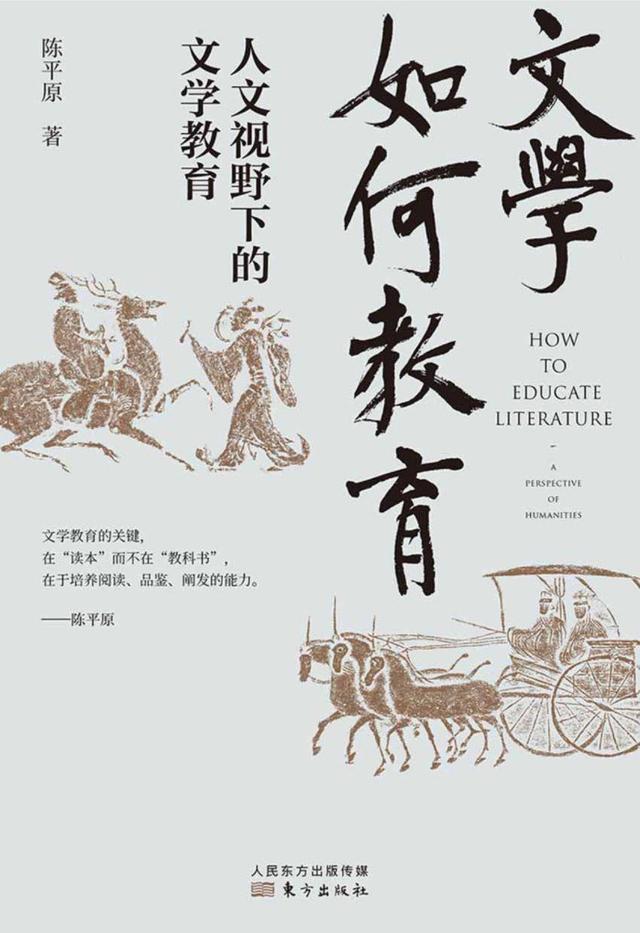
《文学如何教育》,东方出版社2021年4月版
同样读书做学问,老一辈文史专家大都主张沉潜把玩、博学深思,这与今天课题优先、出活第一的学术风气,明显不是一条路。所谓“草鞋没样,边打边像”,或者“出水才看两腿泥”,这种学术风格,在推崇项目化管理的今天,显得十分不合时宜。这个时代,需要的是明确立场、事先规划、大胆吆喝、提前报喜的能力与胆量。项目(最好是重大项目)到手后,稳坐了钓鱼台,那时再自我调整。否则,再好的才华、再大的雄心,若手中没有项目,在今天的评价体系中,极有可能早早就出局了。
多年前,我曾强调:“‘项目’是为‘科研’服务的,允许有‘科研’而没‘项目’,反对有‘项目’而没‘科研’。人文学者以及偏于思辨的数学家或理论物理学家,完全可能在没有项目经费支持的情况下,做出大学问来。”(《要“项目”还是要“成果”》,《云梦学刊》2014年第4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社会科学总论》2014年4期转载)这话今天大概没有人(或很少人)愿意相信了。记得十年前,北大全球招聘讲席教授(全职),那时我是中文系主任,推荐了伦敦大学某名教授,人事部长看了材料,问我:你不是说他很强吗,为何没有研究项目?我当时的答复是——欧美大学的人文学教授,主要自己做研究,著书立说,没必要申请项目。校方接受了我的解释,可惜人家最后选择了美国的大学。为了今天的演讲,我专门请教哈佛大学某讲座教授,不出意外,他也“对这类奖助金项目一向十分疏懒,竟然从来没有申请过”。以有无项目来评判人文学者,这是亚洲华语地区(包括新加坡)的特色,在全世界范围内,并不具有普遍性:“欧美的确没有这套制度。但有ACLS、NEH等有公信力的民间或半官方基金会设立的研究奖助金可供申请(CCK算是国际汉学奖助基金会),但没有任何规定学者必须申请,以此作为晋升标准。最后的判准,如你所说,是学问(出版的文章、书籍)的品质,不是项目、金额的有无。”
那么,为什么在中国的人文学界,会有如此独尊项目的风气?依我推测,第一,最近二三十年,中国经济及文化迅速崛起,基于时不我待的良好愿望,政府希望通过合理调配人力物力,采用类似计划经济的运作方式,弯道超车,体现制度的优越性。第二,这套制度的核心是规划与管理,而管理要想上轨道,必定追求数字化,在确保时间、技术、经费的条件下,尽可能提高生产效率,完成预定目标。第三,项目化运作在工程技术领域确实很有效,用在社会科学也还说得过去,唯独人文学很不适应;而目前中国著名大学的校长多为理工科出身(因需要院士头衔),他们对这套管理体制比较熟悉,且容易亲近与接受。
二十年前,项目化管理刚刚进入人文学领域,国家科学技术部办公厅曾就那时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原始创新”话题,举办了一次跨学科座谈会。第一个发言的是中科院资深院士邹承鲁,第二位发言的陈述彭,也是中科院资深院士;我排在第三位,后面还有好些科学家及人文学者踊跃发言。这次座谈会的纪要,以《自然、人文、社科三大领域聚焦原始创新》为题,初刊《中国软科学》2002年第8期。我在发言中谈及那时刚冒头的“人文研究的工程化”,强调人文学的特殊性:“工程管理需要计划,人文研究则有很大的随意性。学者靠的是长期的修养,靠的是不懈的追求,最后灵光一闪,照亮了平生的积累,抓住机遇,再加上自家努力,就这么出的大成果。根本不可能是原先计划好的,要是结论早先就有,而且可以按部就班地推进,我很怀疑这种研究的价值。”发完言后,一位院士跑来跟我解释,说我误解理工科了,他们真正的学术突破,也大都像我说的那样,“最后灵光一闪,照亮了平生的积累”。
我的批评与质疑之所以不起任何作用,一方面是人微言轻,且所论集中在“原始创新”,没有考虑均衡发展与社会服务,明显有所偏颇;另一方面则是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不断积累经验与资金,如今战绩辉煌:投入二十六亿五千万元,资助各类项目两万四千二百八十三个,推出研究成果四万五千多项,有效地促进了中国人文及社会科学的发展。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范围越来越广,不仅有重大项目,还有专项工程、后期资助项目、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年度项目、青年项目和西部项目,以及单列学科(教育学、艺术学)等,几乎无远弗届。考虑到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收益实在太大,不免有蝇营狗苟之士钻漏洞,因而出现若干偏差,比如过分揣摩趋势与潮流、分析中奖几率、培训填表技能等,好在基金委不断调整策略。如今年初网站发布《2021年12月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青年项目和西部项目结项情况》,通告总共验收了四百五十七个年度项目、青年项目和西部项目结项申请,其中三百二十六个项目予以结项,一百一十个项目暂缓结项,二十一个项目被终止。也就是说,有关部门已经意识到,除了严格评审制度,还得加强后期验收,否则很容易功亏一篑。
今天生活在中国的人文学者,可供申请的,不仅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还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所在市或校的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因此,在大学教书的,不管老中青,大都有这样那样的科研项目,甚至有一部著作或一篇论文挂好几个项目的。以至当有人拿出没有任何项目支持的研究成果时,其学术水平及含金量会被杂志社、出版社、大学科研处以及评奖机构广泛质疑,起码低看一眼——当然,如果是名家,早就表明态度不参与这套游戏的,那又另当别论。可以这么说,以项目为中心的学术生态,乃当今中国大学的一大特色。
这套管理体制,有其利,也有其弊。既然大势已经形成,自然有其合理性;作为个体的学者,我们只能自己选择,尽可能地趋利避害。

十四年前,在北大一套大书的出版座谈会上,我谈及如今这套管理及评估体系,剥夺了人文学者本该有的从容、淡定与自信:“以我的观察,最近二十年,好的人文学著作,大体上有三个特点,第一,个人撰写;第二,长期经营;第三,没有或很少资助。”具体的阐述就不说了,文章最后提出一个设想:“建议政府改变奖励学术的机制,除了现行的课题申请,应增加事后的奖励。没拿国家资助的学者,可以凭已出版的著作,申请下一步的科研经费。经过专家鉴定,确实优秀的,不妨按质论价。”(《学界中谁还能“二十年磨一剑”》,2008年2月18日《人民日报》)文章发表后,不少人叫好,但也有领导表示不以为然,担心没有计划书和时间表,教授拿了钱不干活。我的回答是:凡真正的好学者,做学问犹如穿上红舞鞋,只要生命不息,阅读、思考与表达就不会停止。若这个奖励能帮他/她解除一些后顾之忧(包括各种考核),更加自由自在地探索,那何乐而不为?
八年前,我应邀撰写了上面提及的那篇流传颇广的《要“项目”还是要“成果”》,除了对独尊项目的风气做了若干剖析,文章最后,重提我的设想,希望政府特别表彰那些没拿国家经费而做出好成绩的学者:“今天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资助18万,你自力更生,没拿国家经费而获教育部人文社科著作奖的,给五十万奖励行不行?到目前为止,教育部总共颁了六次奖,我得了五次,其中两次还是著作一等奖。可我所有奖金加起来,还不够一个一般项目的资助。这你就明白,为何大家都把心思放在争取项目,而不是做好科研。为了扭转学风,不妨考虑我的建议,奖励那些诚笃认真、行事低调、不喜欢开空头支票的学者。”
这里的基本思路是:中国的人文研究,产量已经足够了,基本水平也还不错,缺的其实是原创性成果。原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兼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郭传杰接受网易科技《科学大师》栏目专访,称:“从数量上看,我们人才队伍是很大的,据科技部2020年的官方统计,RD(研发)人员已经达到710多万,规模世界第一。但是我认为,其中大量都是普通人才,以二流、三流的人才居多,一流的人才,就是钱学森钱老所期待的那种人才,我们还是很缺少的。”(2022年5月17日《科学大师》)其实,这个问题在人文学及社会科学领域更为突出。科技水平高低有相对客观的标准,成败得失比较好检验,聪明的管理者大都心里有数。至于人文及社科的成果是否具有“原创性”,短时间内,基本上“全凭嘴一张”。不能说没有标准,但相对模糊,很难一目了然,需要时间来淘洗。
因此,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应鼓励天马行空、不拘一格的创新思维与表达。而在我看来,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基本上都是无数次艰难探索乃至失败后的“灵光一闪”,而不是靠人海战术拼凑出来的。在进一步完善现有的这一套行之有效的项目管理制度的同时,尊重那些不太听话、喜欢质疑、特立独行的人文学者的选择,具体策略可简化为三句话:第一,评价大学或具体学者时,大幅减少课题(项目)的权重(起码不该有一票否决那样的提法),转而注重代表性成果;第二,若经费都在同一个盘子,建议相对削减科研经费,转而提高优秀成果的奖励额度;第三,凡事先没有(或不愿)申请项目的优秀成果,获奖后,不用填表申请,直接加倍奖励科研经费,允许其自主决定研究方向、题目、完成时间与成果形式。这么做的目的,是在稳定大局的前提下,保留一块相对宽松、可供自由驰骋的天地,进行另一种研究方法、思路、境界的探试。
这里我必须做一个小小的修正。多年来,我在好几篇文章中提及自己不喜欢“领军人物”这个词,而更欣赏“独行侠”。那是因为,工程技术或某些社会科学,需要大兵团作战,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确实是本事,可文史哲及宗教、艺术等领域,情况不是这样的。“以我浅见,人文领域的创新与突破,大都属于这些壁立千仞、特立独行的学者。领着几百上千人做学问,那只能是整理或汇编,满足领导‘盛世修大典’的虚荣心。‘学术组织者’的能力,与‘千里走单骑’的胆识,同样值得尊重。可眼下整个社会的价值判断,越来越向‘组织者’倾斜,见面先问行政级别、手下人马以及经费数目,这可不是好现象。”(《关于“人才养育”的十句话》,2015年12月22日《光明日报》)后来想想,假如放长视线,且不拘泥于组织形式与课题经费,那些意志坚定、思维深邃、勇于挑战成规与常识的“独行侠”,万一历尽千辛万苦,最终闯出一片新天地,给学界提供可以追摹的新领域、新课题、新方法、新思路,不也是另一种形式的“领军”吗?
目前的制度设计,主要着眼点在建立各种关卡,防止营私舞弊,可不知不觉中,演变成为鼓励稳妥的选题、均衡的思考、平庸的表达。太个性化的探索,很难被接纳。所谓慧眼识英雄(尤其是在其没有盔甲与标旗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的;更何况,一个人说了不算,还必须有好几个伯乐凑在一起。而真正的一流人才,很可能不屑于或没能力填好如此复杂的表格。不能埋怨评审者有眼无珠,而是你走得太前了,且仍在探索中,论证不够严密。审读每份申请表格的时间那么短,评审者当然只能根据自己的立场与思路来做判断。了解这一点,你就很容易明白,再好的制度设计,也都不能保证“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基于这一判断,我才会再三申述,希望有关部门在严格管理,杜绝各种弊端,保证撒下的每颗种子都开花结果的同时,预留一定的自由探索空间,选择/允许一小部分人不计前程,全凭个人直觉与兴趣,放手一搏,说不定哪天会有意想不到的大创获。
(本文为作者2022年5月31日在复旦大学智能评价与治理实验基地主办的“反思与探索——人文学者谈学术评价”会上的发言)
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张艳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