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之:究竟谁在领导德国的抗疫?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根据德国罗科所(Robert-Koch-Institut)周三(4月14日)公布的最新数字,一日内新增感染21683人(上周同日9677),死亡人数达342例(上周同日298);全国每10万人口七天的平均值为153.2(上周同日110.1)。
由于前一阵复活节期间检测减少,各卫生局上报会有延误,因此,本周三之后,数据才算基本恢复“正常的可信度”。
罗科所主席威勒(Lothar Wieler)表示,疫情“非常非常严峻”,患者的年龄正在进一步下降,重症室人满为患。可领导抗疫的联邦和各州政府眼下却还在为“谁执牛耳”这样的权力问题争论不休。
目前,德国正处于比较艰难的第三波疫情中。民众看不出政府的抗疫战略是什么,情绪因而越来越沮丧。
一年多来,德国的抗疫究竟走过了怎样一条路?本文试图就此做一个总结。
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去年的疫情:1月底,新冠病毒首次登陆德国;3月,第一波冲击达到高潮;5月中旬,疫情在全国统一采取“停摆”措施后趋缓,并维持在一个可控水准上。
客观而言,与欧洲其他国家比,德国第一波的抗疫还是相当成功的。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1)从开始觉得病毒离自己还很远到周边国家短期内出现恐怖疫情,德国人亲历了“轻视”和“惊恐”两个阶段。由于没有可以完全照搬的抗疫“样本”,安全意识超强的德国人采取“宁过勿怠”的抗疫措施——停摆,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2)疫情强冲击之下,虽然有相当一部分人内心嘀咕、不习惯戴口罩、甚至认为病毒并没那么可怕,但因为首次遇到这种情况,民众还难以想象病毒会如此“顽强”、紧缩措施会持续这么久,所以,他们开始时对政府的举措还比较“乐观”,也挺配合。
3)为避免立法机构(议会)商讨对策过于冗长,德国在抗疫中启动了所谓的“州长联席会议”(Ministerpräsidentenkonferenz-MPK)这个“非正式”机制。该机制原本用于各州共同面对联邦时协调各自立场,这次本意也是为了与联邦协商措施时最大程度地维护各州自身的利益,但是,由于各州面对如此规模的疫情并无经验可循,所以,它在第一波中与联邦总理府会商时更多是“配合”与“听从”,客观上避免了“扯皮”现象,提高了抗疫效益。

4月9日,德国《时代》周报还发表深度文章,详细介绍了州长联席会议(图片来源:报道截图)
4)面对如此规模的疫情,缺乏经验的行政部门比较认真听取医学专家们的意见,各个相关领域的专家参与了各州以及联邦的决策程序;德国人普遍比较尊重“权威”,因此,学者们以各种方式向政府和民众提供咨询时收效不错,科普工作比较成功。
5)不管是因为“无知无畏”,还是“众志成城”,总之,面对第一波疫情,许多问题虽然已初显端倪,但尚未影响全局,因而也就没有彻底暴露出来。譬如,抗疫物资储备方面“重视大件(急症床位、呼吸机等)、轻视小件”(如口罩、防护服等)的现象;对抗疫的“持久性”、民众的“承受力”、抗疫产生的财政压力、法律后果以及协调复杂性等估计严重不足。
5月底6月初,随着第一轮防控措施的奏效,加上夏日度假期的到来,政府此时即便对疫情未来的发展不敢过于乐观,也无法继续要求民众放弃个人权利和自由。就这样,德国人开始到处旅游度假,就像疫情不复存在一样。
但病毒并未离开,只是在“等待”时机。日常生活恢复之时,也是病毒开始发动第二轮攻击的时候。外出度假的德国人虽然心情大好,返回时却带回了新的感染源。随着秋天的到来,病毒开始实施“秋后算账”,第二波冲击开始了。
与10月相比,11月全国感染人数从230000增至530000,死亡人数从960增至6150。面对这种局面,联邦和各州从11月初开始不得不采取新的限制措施,但决策时瞻前顾后,优柔寡断,搞了一个所谓的“软方案”(Lockdown light),收效甚微。
结果,进入12月后,新的感染人数有增无减,升至675000,死亡人数甚至超过4月的最高纪录(6500),达到17000。政府不得不赶紧“拉闸”,赶在聚会集中和频繁的圣诞节前宣布采取“硬核限制措施”(Harter Lockdown)。
但是,任何措施都不可能马上见效,所以,今年1月,德国的新感染人数高达50万,死亡人数2.4万。当时,日死亡人数超过1000的情况不在少数。
12月底的严厉措施,到2月才略显效应:月新感染人数降至22.6万,但死亡人数依然上万。3月,死亡人数虽然降到一万以下(6300),但新感染人数却出现了反弹,高达36.6万。
当时,变异的“英国版”病毒已在德国占据上风。疫情由第二波几乎无过渡地直接进入第三波,并一直处于某种“高危”状态中。
在此过程中,“旧问题”开始渐渐凸显:第一波中看似行之有效的办法渐渐失去了效力,联邦和各州给人留下的“合力”印象越来越靠不住。与此同时,“新问题”又接二连三地浮现出来:
1)从第一波开始,各级政府就反复强调并保证采取各种措施保护老年群体,但第二波中出现的高死亡率主要集中在养老院。这说明,政府并未兑现承诺,漏洞并未堵住,许诺的“增加测试”措施也未到位。结合政府其他一些没有兑现的承诺(如快速测试等),舆论和民众开始质疑政府的公信力和行动力。第一波中的德国政治新星、卫生部长施帕恩(Jens Spahn)威信锐减。
2)德国的抗疫战略始终以疫苗为基点,也就是说,所有的希望都压在疫苗这一张“牌”上。疫苗投入市场并产生群体免疫效果之前,所有措施只是“过渡性”和“维持性”的,目标是确保公共卫生系统不崩塌。因此,当德国美因兹的“生物新技术公司”(BioNTech SE)与美国辉瑞率先研发出功效达95%的疫苗时,德国官民都很兴奋。然而,接下来的疫苗采购工作却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导致德国和欧盟在接种疫苗方面大大落后于其他国家(美国、英国、以色列)。
3)屋漏偏逢连夜雨。由于欧盟采购疫苗的失误,德国的疫苗本来就供不应求,围绕阿斯利康的争议还偏偏没完没了:开始时,德国疫苗委员会(Stiko)认为该疫苗临床数据不完整,因此不适用于65岁以上的群体接种;3月初,随着多个欧洲国家因脑血栓风险全面叫停阿斯利康,德国也暂时停止了该疫苗的接种,几天后才又恢复。可恢复才两周又出新状况,有关部门这次告知公众该疫苗只适用于60岁以上群体。如此一波三折,不仅严重影响了阿斯利康的市场信誉,监管部门前后矛盾的说辞也让公众对政府抗疫能力的信心大打折扣。
4)媒体揭出政治家舞弊现象:执政的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中有议员利用抗疫物资(口罩)短缺现象,在买卖之间牵线搭桥,从中牟利。这些丑闻影响恶劣,不仅给德国第二、三波抗疫本来就不佳的效果“雪上加霜”,而且也让联盟党(Union)在两个州选中遭受重创。
5)制定限制措施时,“进一步,退一步,甚至退两步”;有些措施的“逻辑和意义”让人难以理解;政治协商机制逐渐失灵,联邦总理府与州长联席会议形成的决议在具体落实中出现偏差,各行其是现象普遍,严重影响了联席会议这个协调机制的威信和效益,为眼下联邦和各州之间的“权力”之争埋下伏笔。联邦要求修改《感染保护法》(Infektionsschutzgesetz),以此获得更大的行政权力;各州的反应不一,有的支持这个意向,有的反对放权。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和舆论无法不质疑各级政府合力抗疫的意愿和能力。
6)政界要么难以形成统一意见,要么在形成决议的情况下仍然我行我素;科学家和专业人士的意见相互对立,有时还前后矛盾,第一波时曾有过的“向心力”不再;政府的决策时而被法院推翻;媒体的表现依然是“世人皆醉,唯我独醒”,报道更多是“揭露”和“指责”,而非“凝聚”和“解惑”。这些都增加了抗疫的难度。
那么,德国抗疫决策中为何会出现这种“七嘴八舌”“莫衷一是”的局面呢?根据笔者一年多来的观察,这与以下几个“矛盾现象”密不可分:
本国与欧盟
这对“矛盾”在此次抗疫中表现得相当突出,以采购疫苗为例:
当去年中旬疫苗有望投入市场的消息传出后,德国卫生部长施帕恩立刻联络法国、意大利、荷兰三国,有意一起“团购”,以期占得先机。可是,当时正赶上德国准备接手下半年的欧盟“轮值主席”。为了不授人以柄,落下“老大率先抢疫苗”的骂名,默克尔闻讯后立刻叫停施帕恩,要求把购买疫苗的事务交给欧盟委员会去办。据说(《图片报》貌似有证据),默克尔还要施帕恩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写信对率先购买的作法致歉。

一年前的施帕恩与冯德莱恩(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如果欧盟在后来的采购中表现好的话,默克尔这个“欧盟优先”的作法不仅不会受到诟病,还会获得国内和欧盟的一致好评。可是,欧盟的采购策略非常糟糕,直接导致现在“供不应求”的不堪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默克尔的“顾全大局”演变成了“丧权辱国”,引起了不少国民的不满。
欧盟政治一体化虽然陷入僵局,但各成员国在制定政策时却又无法对这个政治实体的存在视而不见。德国的处境更加微妙:鉴于历史原因,德国的任何特立独行都有可能引发邻国对“历史重演”的警觉,所以,德国政府说什么做什么都特别顾忌这点。而这恰恰又成为国内极右民粹势力攻击默克尔政府的有力武器。
联邦与各州
众所周知,德国是联邦制。在此次新冠疫情出现之前,这个“德国模式”经受住了各种危机考验,且相当成功,所以招徕过不少的“羡慕嫉妒恨”。可是,病毒无国界,更无州界。如此规模的病毒流行,令德国现行的政体架构陷入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抗疫需要政府部门作出跨州的迅速反应,可公共卫生与教育、文化、警务等领域一样,主要是州事务,联邦授权有限,干预的可能不大。
为了解决这个宪法“漏洞”,“州长联席会议”这个非正式机制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与联邦政府一起,共同协调并制定抗疫措施。
第一波疫情出现时,大家都有点“懵”,各州不愿也无力单独出头,自行解决,所以愿意拿联邦当“主心骨”,这才形成了“抱团合力”的团结局面;第一波之后,德国的抗疫效果不错,各州的表现虽然参差不齐,但都感觉良好,认为已积攒了足够的经验,自然不会再乐于让联邦单独收获政绩红利。毕竟,各州政府的政治光谱不同,首先要面对的是本州的选民。
就这样,“联席会议”虽然照常定期举行,也形成各种决议,但每次会商的时间越来越长,达成一致越来越艰难,会议经常开至深夜。原因不言而喻:各方都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政治权衡(舆论、经济、党争等因素)非常明显。这样“博弈”出来的决议必定是妥协后的结果:看似面面俱到,照顾各方,实质不痛不痒,收效甚微。
就这样,限制措施“down”到现在,病毒照旧在泛滥。民众被限制得精疲力尽,虽然还在勉强配合,但已怨气滔天,渐渐失去耐心。
个人与集体
第一波疫情时,民众在听闻中国的“封城”,随后眼见意大利军车运尸体的场景后,保护意识是起来了,但大家对限制措施到底意味着什么并不十分清楚,所以,面对政府出台的第一批强限制措施,民众虽然不习惯,但还是遵从和配合的。
第一波之后,人们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担心采购不到东西后的紧张,什么是学校幼儿园关闭后自己数周在家带孩子的滋味,什么是聚会娱乐场所被关闭后无处消遣带来的苦恼和烦躁,公共场合必须配戴口罩意味着什么,出行受限带来什么样的不便,包括度假旅游等个人自由无法尽情享受时是什么样的心情,个人权利被“过度”剥夺后会造成何种愤怒和不满。
总之,自由的价值只有当它失去后才能体会到。因此,去年夏天恢复“自由”后,政府面对再次严重的疫情又要实行限制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西方的自由首先是指私权。个人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这是宪法赋予的。在“集体利益”与“个人自由”出现矛盾时,有素质的人(大部分德国人)会顾念到大家的利益,自觉约束个人行为或遵从政府的规定,但有些人还是会坚持自己的权利。因此,疫情期间,告政府措施不当的案件不少,法院推翻政府决定的案例也时有发生。
少数与多数
德国是个民主社会,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这个原则在选举中可以通过选票来体现,可在抗疫中,“少数服从多数”变得难以实现。
以“限制措施”为例:多次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民众都支持“短时间,强限制”这样的抗疫方案,即通过限制更多的个人自由,以期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将病毒传播压缩到可控范围内,然后再谈开放解禁。
但是,小部分人,主要是“阴谋论”的信众、极端主义者等,不相信也不愿意遵从政府的措施,他们上街抗议游行,提出“保护个人自由”等口号。新闻媒体对这类“吸引眼球”和有“轰动效应”的事件比较关注,给予的报道篇幅颇多,造成“他们才是主流”的假象,
加上德国又没有进行“公投”的政治传统,所以,少数人的诉求被过度强化,而代表默默无闻的大部分人的想法(真正的民意)却被忽视了。
这个现象带来的副作用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或“谁动静闹得大,谁就会受到重视”。疫情期间,那些始终坚持在工作岗位上的售货员和医护人员虽然一度被誉为“真正的英雄”,多方呼吁应该为这群人涨工资,但事后真正落实的情况据说并不让人满意。为何?因为他们太“沉默”。
经济利益与社会公正
防疫措施不仅限制了公民的个人自由,还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企业的运转和店铺的营业。数月来,除了去年夏天几个月里曾部分开放之外,酒店、餐饮业、文化设施、健身房、理发店、零售业等非超市及生活必需品的商家一直无法开张,损失严重。
很多行会认为政府的措施不公平,有的实体赚得钵满盆满,有的入不敷出,还有的血本无归;行业之间的互助精神严重缺失。关键是,这些实体运行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成千上万个员工的饭碗,而这些员工后面又是一个个靠他们工资生活的家庭。
如何做到顾及经济利益的同时关注社会公正?这是政府的一大难题。
这次德国投入大量纾困资金,但由于人为错误和技术障碍,很多受损的个人和实体很晚或至今都未得到该得的资金援助。倒是一些犯罪个人和团伙趁火打劫、非法骗取政府补助的案例层出不穷。
政治正确与反智言论
“政治正确”本来是文明社会的一种进步,旨在保护社会某些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为此,德国媒体在《自律守则》(Pressekodex)中规定,报道中应隐去涉及当事人身份、种族等个人信息,以避免引起偏见和歧视。美国的亚裔因新冠病毒而受到歧视和袭击,就是歧视性报道以及官方或政客煽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正确”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如果“政治正确”演变成某种代表正确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流价值观,就会导致另一些问题的出现,譬如,不同意见和少数意见受到排挤和群殴,新的偏见和成见得以强化。
“阴谋论”和反智言论的盛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政治正确”意识形态化的结果之一。感觉被排挤和被压制的一些人就会抵触和反感主流观念,宁愿采信种种“阴谋论”。同时,“政治正确”在坚信自己代表“正确”的时候,也在制造新的“成见、偏见和不公平”。
以疫苗问题为例:世卫组织(WHO)总干事谭德赛日前表示,全球疫苗分配不平衡的现象依然令人震惊,高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接种了超过87%的疫苗,而低收入国家只接种了0.2%的疫苗。
谁应该对这样的局面负责?这恐怕是个不言而喻的事情。但西方媒体不关注这个不公平现象,却盯着哪些国家使用了中国疫苗。
欧洲一些国家因为欧盟采购疫苗不力而求助中方,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因为疫苗被富国几乎垄断而请求中国提供,这被西方媒体说成中国在搞“疫苗外交”。如果中方对这些求援声音置若罔闻,恐怕又会被这些媒体批成“自私自利”“冷酷无情”。
“政治正确”一旦意识形态化,就会背离原先的“大同普世”“人皆平等”的初心,产生新的“分别心”。譬如,德国媒体在提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抗疫的成功经验时,首推韩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按理说,那里的抗疫措施中也含有不符合德国观念的一些做法(手机跟踪中的个人隐私问题等);更何况,这三个国家和地区的岛屿或半岛特性以及面积大小对德国毫无借鉴性,那里封锁起来要比德国容易得多。可德国为何偏偏青睐它们而回避或排斥“中国模式”呢?很明显是意识形态的分别。
这种“姓社姓资”的“阵营意识”到头来对中国毫无损害,耽误的却是西方本身的抗疫成效。再譬如,德国一直排斥俄罗斯的疫苗(原因不言而喻),如今,德国疫苗供不应求了,加上第三波疫情大有失控的危险,所以,卫生部长施帕恩转而表示愿意引进俄罗斯疫苗,前提当然是该疫苗获得欧盟药检部门的批准。巴伐利亚州和梅前州也已经预订了Sputnik V疫苗。
风险与担当
整个疫情期间,德国除若干国会议员因 “发国难财” (在党内和舆论的压力之下)引咎辞职外,没有一个官员因为担责而下台。
是这里的抗疫没有漏洞?是没有出现过任何人为错误?都不是。按照德国的体制,因丑闻下台的官员有,但因渎职下台的却寥寥无几。这导致官员们为了保住乌纱帽而失去担当的勇气和意识。
这次抗疫过程中,许多机构和人名经常会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有些是大家熟知的,譬如各级政府和公共卫生机构,还有大学医院、病毒学、心理学等各相关领域的专家,当然还有各种舆论媒体和各级法院等。
有些则是鲜为人知的,譬如“伦理委员会”(Ethikrat)。该机构平常很少进入公众的视野,即便出现也不为人关注。其实它非常重要,相当于“不是法院的法院”。政府遇到专业问题会请教各方面的专家,若专家遇到难题,就会向“伦理委员会”咨询。有难题,问伦理。它的作用和影响力尤其在政府和专家很难决策或左右为难时更加明显。
一方面,德国这种机制分摊了风险,能在各有所长的基础上集思广益;另一方面,民主的传统和氛围又导致“七嘴八舌”和“莫衷一是”的现象。
疫情期间的一个常态是,政府一个政策刚出笼,各种反对意见即随之而来;某个专家刚提出一个建议,立刻就会有其他专家的反对意见面世;联盟党刚就某事作出表态,联合政府的另一伙伴社民党常会提出反对意见,议会的其他反对党更是有各种表述;媒体作为“第四权”似乎是永远的反对派和有理者,眼睛只看“负面的”,这个世界似乎就没有高兴的事儿,手永远指向别人,自省能力几无。
面对德国一段时间以来出现的各种“乱象”,人们自然会问:究竟谁在领导德国的抗疫?
目前,德国的疫情走向不明。各类数据似乎证明,一段时间以来的紧缩措施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还非常不稳定。因此,掌握更多信息的专家们反复指出德国正处在“高危”阶段,特别是接下来几周,医院的救治能力将临近或超过极限,后果堪忧。
今年将要告别政坛的默克尔总理对德国目前的抗疫状态非常不满,对“诸侯大员”各行其是的作法渐渐失去耐心。两周前,她公开点名批评北威州州长、联盟党总理热门候选人之一的拉舍特(Armin Laschet),“威胁”将绕过联席会议、通过联邦议会增修《感染保护法》来收拢权力,逼迫各州在抗疫问题上向联邦放权。她提出的理由很简单:我就职时曾宣誓要保护德国的整体利益,所以不能对眼下的危险视而不见或无所作为。
默克尔发出警告后,各州反应不一:有的表示理解和支持(巴伐利亚州长、联盟党另一位总理热门候选人索德尔),有的表示反对(社民党主政的一些州),有的开始转向,向默克尔靠拢(如拉舍特),有的沉默以对,有的则坚持己见(如萨尔州长汉斯)。
本来要在本周一(4月12日)举行的联席会议已告吹。上周五(4月9日)早上有消息传出:总理默克尔、社民党籍的财长兼副总理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以及柏林市长缪勒(Michael Müller)和巴伐利亚州长马库斯·索德尔(Markus Söder)这两位“州长联席会议”的召集人开了个“四人会议”,对今后如何操作似乎达成了一致。有迹象表明,默克尔的“曲线收权”方案最终或将占据上风,即通过议会立法的形式来制定适用于全国的抗疫措施。
这意味着,新一轮的“硬核限制措施” 不久将出台;更重要的是,抗疫的决策程序或将出现重大变化,一年多以来最高决策机构(“州长联席会议”)的权力很有可能将被大大削弱。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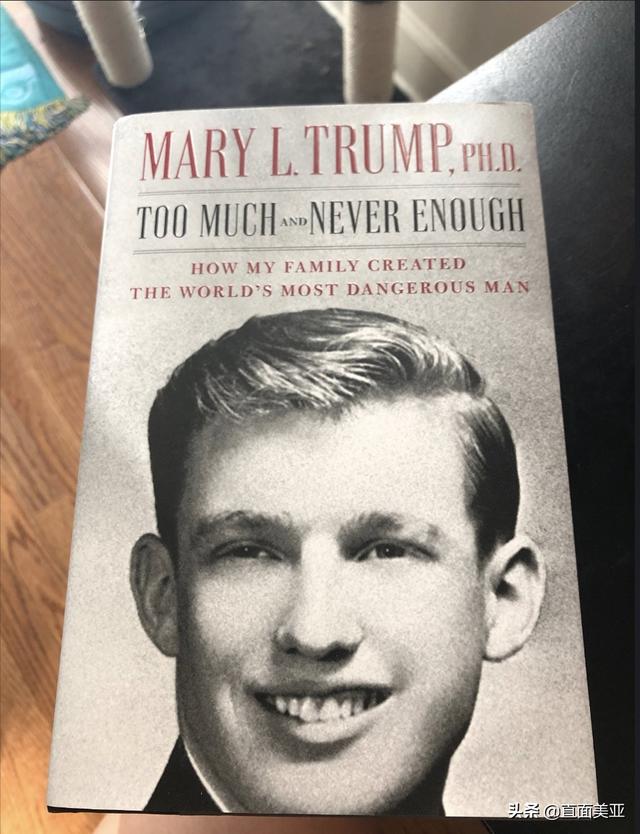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