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连载:白棉花(第三章)

十一年后,我与成了一级厨师的冯结巴冯飞扬在火车上邂逅相遇。他又白又胖,穿着一身呢子制服,手腕上戴着一块足有三两重的大手表。
通过简短交谈,我知道他后来在舅舅的安排下,去了滨海油田,成了正式工人,先当炊事员,又进烹饪技校,去过香港、新加坡,回来评上一级厨师,娶了党委书记的女儿,生了一个胖儿子。话题自然转到棉花加工厂,他说:
“那时过的真是狗都不如的日子,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我很知足。你不知道我们家当时有多么穷。别人还从家背点玉米面投到食堂里,正儿巴经地拿着粮票打几个窝窝头吃,我们家里连地瓜干子都吃不上。背着人,啃点菜团子,喝点开水,就算一顿饭。看到那些正式工吃馒头,馋得我呀,他妈的,眼泪鼻涕一块儿流。不瞒你说,有一次,实在饿极了,我跑到榨油车间去喝过棉籽油,一次喝一铁瓢。肚子受不了,肛门没了约束,不知不觉就流了油……”
我们一起笑了。
这小子现在是头发乌黑,像在油里浸过一样。我们忆着苦,思着甜,话题自然转到方碧玉身上。
“她死得好惨……”我说,“那么好的一个人,落了个粉身碎骨的下场……”
“你认为她死了吗?”冯结巴问我。
“怎么?难道她没死?”我惊异地问。
“她死在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永远不会忘记!”我说,“她死于那一年的一月二十五号,那天正好是腊月二十三,‘辞灶日’,过小年。”
“我认为方碧玉没死。”冯说。
“她的身子都被清花机给打烂了,你还说她没死。”
“她没有死,像她这样的女人决不会自杀!”
“别说梦话了。”我说。
“你还记得那个被皮辊绞死的女工吗?”
“记得。”
冯说:“问题就在这里。”
深秋的夜晚,天很凉了。我感到浑身哆嗦。
站在车间里,郭麻子手指着那一片皮辊机,对我和李志高说:
“你们俩负责供应这三十台车的棉花,误了找你们。”
柴油机轰鸣起来。地沟里,镶着铜牙的柴油机工孙师傅拿着铁撬棍往主传动轴上挂皮带。几十个身穿白围裙、头戴白帽、嘴上捂着白色大口罩的女工各就各位,面对着自己的轧花机。我毫不费力地认出了方碧玉。车间里灯光明亮,胜过白昼,她那两只黑色大眼在雪白衣帽和四周棉花的映衬下,蓝幽幽地放光,像狸猫一样。我看到她在注视着我和李志高。我认为她在对我们表示同情和关注。她在鼓励我们。她一定在为能与我们上一个班感到高兴。你的高兴就是我们的高兴呀,方碧玉。我在心里大声说。
传动皮带猛然抽紧,并发出尖利的摩擦声。传送轴轰轰转动,几十部轧花机皮辊旋转,除籽栅前后推拉,巨大的噪声立即充满车间。姑娘们抱起棉花,放在机前平板上,然后左右开弓,双手抓花甩动,让棉花均匀地落在两只皮辊之间。方碧玉的动作最迅速、最准确、最优美。
“还不快去抬棉花!”郭麻子对着我们大声吼叫。
机器的力量使人兴奋,我和李志高一前一后抬着大篓子,向棉花垛跑去。
另外两个抬大篓子的老手,看着我们笑。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
“这俩小子是热锅上的蚂蚱,蹦达不了多会儿。”
他们笑得有道理,他们说得更准确。
垛在一起的棉花,竟然变得如此坚硬,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从垛上往篓里装棉花,其实是非常艰苦的过程,棉花挤压在一起,纤维粘连,拽着如同胶皮,插手难进。要想使棉花松软能抱,第一是用铁钩子把棉花扯下来,第二是爬到垛上去,坐下,用两个脚后跟找到层次,把棉花像揭饼一样蹬下来,这是抬大篓子的伙计们艰苦摸索后得到的经验。当时,我们在那儿扯呀,撕呀,有货装不到篓子里去,仅装了半篓,就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了。
“你们俩小子,要磨洋工是不是?”郭麻子跑到垛边来骂我们,“几十台车等着吃!你们知不知道两个班在比着干?”
“主任,不是我们不急,是干着急拽不下来。”李志高说。
“笨蛋,用钩子往下抓,上去用脚往下蹬!”郭主任告诉我们。
上去一试,果然有效。很快满了篓。一抬,不起,再一挺,起来了。李在后,我在前,互相看不见。脊梁杆子弯曲,腿哆嗦,不准拿,一路歪斜,扭秧歌一样。顾不上说话,听到郭麻子郭主任在我耳旁说:
“小子,尝尝滋味吧!你们以为一天一块三毛五分钱就那么好挣?!”
进了车间,地上棉花绊脚,正扭着,感到后边猛一沉,李志高没招呼就扔了杠子。全身骨节一阵嘎吧,脸一仰,我一腚就坐在地上。幸好有些棉花垫着,没跌坏尾巴骨。姑娘们哧哧地笑我们,因为我们俩算公认的秀才。我也不知怎么就糊糊涂涂地成了秀才。站起来,哥俩顾不上埋怨,喊声号子,去倒大篓子,忘了抽杠子,倒不出来,又翻过来抽掉杠子,再翻回去,像屎壳郎翻屎蛋,狼狈透了。正想喘口气,郭麻子又吼:“快去抬呀,操你们二大爷!没看到在跑空车吗?”顾不上回操郭麻子的三姑或二姨,抬起篓子就跑,现在李在前我在后,跑急了篓子碰腿。磕磕碰碰,到了垛前,手刨脚蹬,死活不顾,装满一篓,速度大提高。抬起来一溜小跑,在运动中求平衡,实践出真知。郭麻子说:
“这样干还差不多!”
一个小时过去,跑了十趟,抬进去十篓,汗流干了,浑身酸软,想歇歇,坐下就起不来了。躺在棉花上,什么也不想就想死。感到只躺了不到一分钟,车间里又告了急。郭麻子拿着小竹竿抽打着我们的屁股,脏话像吐鲁番的葡萄,一串一串的。没法子,强挣着爬起来,死干吧,干死吧,往死里干吧。感到像干了一个世纪似的。夜怎么会这么长?问李大哥几点了,李大哥几点了?李大哥从腰带上摘下手表,凑到鼻子尖上看了看,说十二点不到,就算到了十二点才算一小半,我的亲娘,什么时候才能熬到下班。车间里的轰鸣声好像把地球都震动了,那几十台皮辊机像几十只张着大口的巨兽,贪婪地吞食着,吞食着棉花,吞完了棉花就吞食我们……车间里白雾蒙蒙,细小的绒毛飞舞着,白炽灯泡上沾满花绒,像白色的猴头蘑菇。尘土和细绒已经改变了方碧玉她们的模样,她们的工作服和口罩变厚了,她的眼睫毛上沾满了花绒毛,像结满了冰霜的树枝。她们在拿着小竹竿的郭主任的催促下,机械地重复着那些动作,郭主任用小竹竿抽打着她们的屁股,催促着:快点,快点,薄撒,均匀,宋春花,你睡着了吧?大个子邹,你想把机器噎死?……室外星光灿灿室内尘绒弥漫。起初我还感到鼻孔发痒,直打喷嚏,现在我连喷嚏都打不动了。我们再也不敢停止手脚的运动了,而且事情正在起变化,感情正在起变化,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肢体的疼痛和疲倦消逝了,感觉迟钝,伟大的麻木状态开始。这时候人的思维十分节约,我不知道我的李大哥如何,我只知道我自己的脑袋里只有黄豆粒那么大小一块明亮的地方,其他的部分都混混沌沌,处于半休眠状态。就是在那一点黄豆大小的明亮里,装着一只竹编的大篓子,一根大杠子和又白又硬又凉丝毫也不松软也不温暖的像毒蛇一样无情地纠缠在一起的棉花。直到十几年后的今天,一想起棉花,立刻便有那又白又硬又凉的感觉像蛇一样爬进我的脑海,使我万分地惊悚。
郭麻子吹响下班哨子时,红色的霞已经满了天。柴油机工孙师傅熄了机器,天地间突然安静,这安静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压迫着每个人的耳膜,肉体,甚至是灵魂。我的耳朵嗡嗡地响着,突然感到眼前的一切都丧失了原来的模样。霞光怎么会是这样?晨风怎么会是这样?路面上的石块为什么会是这样?
我们哥儿俩扔掉大篓子,栽到垛旁凌乱冰凉的棉花上,我想应该说一句:“同志们,永别啦!”然后悲壮地合上眼睛。
方碧玉毫不客气地踢着我的屁股:
“马成功,起来,起来,这样睡下去是要落病的!”
“李志高,老李,起来,起来,这样睡下去是要落病的!”
“李志高,老李,起来,起来,回宿舍去睡!”
我们在爱的催动下,拼着最后一丝力气,回到了宿舍,爬上我的三层铺,如同攀登珠穆朗玛峰。
开工资的日子到了,掐指一算,来到棉花加工厂已经三个月。据说正式工人每月发一次工资,临时工三个月发一次工资。但总算发工资了。什么叫上等人?上等人就是每月发工资。我们三个月发一次工资,处于上等人与下等人之间,可以算做中等人。下等人永远不发工资。
我记得那天晴空万里,阳光明媚,厂外的柳树脱光叶子,垂着柔软的枝条,像一排排默默肃立的革命英雄。棉花收购旺季已过,田野里的棉花柴擎着五瓣的淡黄色花壳,显示出即将牺牲的悲凉与轻松。厂里的柴油机被一个姓张的小子戳弄坏了,需要大修,车间放假,我们都准备拿着工资回家看看。

办公室外拥挤着二百多人,女多男少。都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脸上涂了一层气味逼人的雪花膏、香脂之类。我既无新衣好换,又无东西往脸上抹,心中不甘不漂亮,便偷挤了李志高一些“白玉”牙膏抹到脸上,脸上又麻又痒,着风一吹凉飕飕的,感觉很好。还用热水洗了头发和脖颈,用一块锋利的碎玻璃刮了刮牙齿上的黄垢,刮得牙龈破裂,满嘴血腥。李志高打扮得风度翩翩,满头的乌发与脚上的皮鞋上下呼应,闪闪发光,宛若优质煤炭。我当然发现他吸引了姑娘队里的许多目光。孙红花磨磨蹭蹭地就和李志高靠在了一起,咯咯地笑着。她的笑声令我厌恶,使我生出许多流氓的思想,使我想起村子里那个老光棍的经验之谈:人浪笑,猫浪叫,驴浪巴咂嘴,狗浪跑断腿。我通过观察,确认这是真理。那么,孙红花对着李志高我的李大哥如此浪起来,说明她对我李大哥有意思。只要李大哥要她,她一定脱不迭裤子。想到此,不由我全身发热,像犯了罪一样,偷偷窥视那些与我一起排队领工资的人,生怕他们看到了我心中那些不高尚的想法。尤其不能让方碧玉看破我的内心啊。她站在那里,面上神情淡漠,不和任何人搭腔,像一棵黑色的树。
负责发放工资的,是那位满脸布满纵横皱纹的老蔡。自从开枪、跳井后,他仿佛又老了10岁。他拖着长腔,按照工资表呼叫人名。
终于呼叫到我的名字了。我分拨开众人,挤进办公室,兴奋得有点手脚无措。厂长、书记,还有那些大小头目正式工们,都坐在那里,目光灼灼,盯着我也一定盯着每一个前来领取工资的临时工。我突然感到心里空虚,好像我来领取的不是艰苦劳动的报酬,而是他们的施舍一样。
厂长严厉地说:
“马成功,拿到了钱,要好好想想,党给了你们这些钱,你应该拿出点行动来答谢党的恩情!”
“我好好干活,死命抬大篓子。”我嗫嚅着。
厂长与支部书记对视片刻,支部书记点了点头,说:
“发给他吧。”
厂长对老蔡说:
“发给他吧。”
老蔡说:“过来过来,靠前点。”
他照着册子念道:
“马成功,实干工日八十五个,日工资一元三角五分,应得工资一百一十四元七角五分,扣除水电住宿费八元五角,实发工资一百零六元二角五分。”
他把一大摞钱推到我面前,说:
“这里边含有交生产队的钱,原则上是交队里一半,队里给你记一个整劳力工分。具体交多少,你自己回去跟生产队里协商。”
紧紧地攥住钱,我走出办公室。初次拿到这么多钱,心中充满幸福感。即使是交队里一半,也有五十三元多钱归我所有。我想我应该去买一件蓝咔叽布军便服上衣,买一条灰布裤子,再买双紧口白底青年鞋,最好再配上一双花格尼龙袜子。应该买包香烟。高级一点,“金叶”或“玉叶”,每盒两毛九,不要“勤俭”和“葵花”,每盒九分钱。还应该买柄牙刷,买管“白玉”或“分外香”牙膏,我也要刷牙,像李志高大哥那样,嘴里插着一把牙刷,满嘴吐着白沫,说话呜呜噜噜,显得那么有派头,有文化,有地位,有身份。买了牙膏牙刷,还应该买个红塑料香皂盒,买一块高级的“罗锅”牌香皂,再配一条花毛巾,洗脸时,一定要用毛巾擦,像电影里那些干部。把这一切配齐了,我还应该买辆“金鹿”牌自行车,买块上海产全钢防震十九钻手表,配上两条表链子,一条铁的,一条皮的。夏天用铁表链,冬天用皮表链。那时我一定转成了正式工人,我骑着崭新的自行车,戴着光灿灿的手表,穿着灰涤卡衬衣,挽着袖口,衬衣的下摆一定要扎到腰带里,不要像老农民那样打着伞。裤子,一定要那种深蓝色混纺华达呢,裤线要有缝,没有熨斗,可用装满热水的玻璃瓶子代替。坚决买双皮鞋,要牛皮的不要猪皮的,猪皮毛眼子粗,擦不亮。还要什么呢?足了,什么都不要了。那时我可以每个月开工资,歇星期天也照样开钱。忘了一件大事:要对一个象。方碧玉,方碧玉我还要吗?不要,坚决不要。要找个月月开工资吃国库粮的,要长得漂亮,要有文化,最好会唱歌,会唱那首著名的抒情歌曲,“小河的水清悠悠庄稼盖满沟”,然后是“解放军进山来帮助咱们闹秋收”。实在不会唱歌会跳舞也凑合。“南飞的大雁请我快快飞”……那时候,正式工人马成功,这位英俊潇洒的小伙子,携着她的手,昂着头,挺着胸,分花拂柳,沿着河堤漫步。他口中吟诵着唐诗宋词,手持纸折扇,与美人同行,犹如羊群里的两匹骆驼,鸡群里的两只仙鹤,那些在堤下棉田里摘棉花的女人,都直起腰,看直了眼,看走了神,嘴里发出啧啧的感叹声:瞧人家,郎才女貌,才子佳人,天生的一对,地设的一双,弯刀对着瓢切菜,生子当如马成功!我携着她走进棉田,她穿着一条火红的裙子,迎风招展,像一面鲜艳的红旗飘进棉田,犹如天仙下凡。洁白的棉花与她火红的裙子形成鲜明的对照。她皮肤光滑,唇边两个小酒涡,性格温柔,待人礼貌。大娘婶子姑娘姐妹们,像一群蜜蜂,或者一群蝴蝶,把她当然也把我包围在中央。大娘伸出生满皱皮的老手,把她的手抓住,赞不绝口:瞧瞧这手,瞧瞧这手,像剥了皮的葱白一样,尖溜溜,滑溜溜,溜光水滑呀溜光水滑……姑娘们捧着她的裙子,反复欣赏,有一位还把脸贴到她的裙子上。这时候,我应该拉着一位老大娘的手,对她嘘寒问暖,态度和蔼可亲,要把她感动得热泪盈眶,把我当成县里来的干部或是省里来的演员……我们终于摆脱了这群农村妇女,互相搀扶着,表现出相亲相爱、相敬如宾的样子攀登上大河高堤,在攀登的过程中,最好她的手能被锯齿形的草叶拉开一条血口,不要太深也不要太浅,太深则疼痛,太浅则做作,她轻轻地呻吟一声,我紧紧地抓住她的手,用嘴巴去吮吸她的伤口。这一幕多么亲切感人,会把那些大娘婶子们羡慕得要命,感动得半死,我们知道她们一定在眼巴巴地看着我们,但我们故意不回头,不要让她们错以为我们是表演给她们看。我们是天生的一对情侣,情侣一对天生成,我们的亲密举动源于火一样的从骨髓里榨出来的从血管里奔涌出来的真爱情……我吮完她手上的伤口,从衣袋里掏出一条绣着几朵鲜红凌霄花的洁白手绢,替她包扎,然后我像托一只小鸟一样,右手揽着她的屁股,左手揽着她的脖颈,她双手紧紧地搂着我的脖子,把那颗血红的脸蛋儿埋在我的胸膛里……她的秀发如瀑布顺着我的胳膊弯子一泻千里,犹如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我左手如抱泰山,右手如托婴孩,跌跌撞撞往上走,幸福之火熊熊燃烧,烧得我头晕眼花。我们忘情地拥抱在一起,我寻找着那两片玫瑰花瓣一样芳香扑鼻秀色可餐之唇……我们互相怀着感恩戴德的心情,依依偎偎拉拉扯扯搂搂抱抱拍拍捏捏向前走,革命道路艰难崎岖仿佛永远没有尽头。突然,前方垂柳树下站定一个人,黑干加枯瘦,好像一棵严冬的树。方碧玉终于出现了,在马成功的故事里,没有她的出现,整个故事将变得枯燥无味,犹如一潭死水。这时,我,翩翩青年马成功,应该仪态潇洒地走过去,主动伸出我那只腕上戴表的右手,镶着红点儿的秒针快速游走,表壳在夕阳余辉下闪烁温柔祥和之光。我的手细腻,她的手粗糙。我白,她黑。但是我决不骄傲。我握住她的手,轻轻地一握,然后稍微一低头,彬彬有礼地说:“碧玉姐,您好!”她一定满面愧色。我对她介绍我的她:碧玉姐,这是我的妻子,学名凌霄花,俗名爬山虎。然后再反过来介绍:爬山虎——对,应该叫她小爬或小虎——这是我在农村时的同伴,方碧玉。这两个女人会怎么样表现呢?她们会互相打量一番,然后必然是方碧玉自惭形秽,爬山虎醋溜兮兮。方碧玉,你现在该后悔了吧?我向你求爱,你竟敢嫌我小,嫌我没出息。现在你还怎么说?当然,我马成功不是那种得意忘形的势利小人,富贵不忘贫贱交嘛。我对你方碧玉也是辗转反侧心念旧恩呀!呀!呀!呀!乌鸦要归巢了,我们也该回家啦……亲爱的,让我们紧紧拥抱……
“马成功!”
我听到有人在耳边喊叫,并感到有人在拍打我的肩膀。努力定神,摆脱幻觉,才发现我正搂着一棵糊满了干牛屎的柳树啃树皮。我满脸都是幸福的泪水。
方碧玉惊讶地看着我,问:
“你得了失心疯了是不是?”
我羞得要命,支吾道:
“我故意出洋相逗你笑。”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发了几个钱把你欢喜疯了呢。”
“瞧你说的,碧玉姐,我马成功再没出息也不会到那种程度。”
“好吧好吧,”她说,“咱结个伴回趟家吧。”
“我在这就是为等你的嘛。”
“走吧。”
“走。”
踢着石头往前走。
“碧玉姐,你每天开多少钱?”
“一元二角五分。”
“你呢?”
“一元三角五分。”
“你们抬大篓子出大力。”
“挣钱多的不出力,出力多的不挣钱。”
“你知道孙红花她们几个干部子女挣多少?”
“我不知道。”
“一元三角。”
“比你们多,你不是技术能手吗?”
“那管什么用?”
我们悠闲自在地向前走,其实我并不悠闲,一方面适才那场梦幻的余毒尚未完全清除,我还把一半身心浸泡在幸福的药酒里——或者说我的脑袋还在天上身体在地上——幸福的感觉像发了疯的狗一样追逐着我狂吠,使我不能很实事求是地与这位被我臆造出来的爬山虎姑娘枪毙掉的方碧玉交谈——爬山虎犹如天边的彩霞渐渐消散,只剩下一团模糊的暗红存在于我的意识之中——另一方面我的靠心脏部位的衣兜里装着三个月劳动换来的人民币,我强烈感觉到它们的存在,感觉到它对我的心脏乃至神经系统所施加的巨大压力。它使我精神沉重肉体轻飘。上述两方面都证实了我与方碧玉同行的第一阶段我是一个精神与肉体分裂了的二元论者。

走着走着就晚霞满天了。爬山虎已融进晚霞,与我脱离了假想的夫妻关系。土路上有迈着沉重的步伐自田野返回的农民。他们脸上都蒙着一层厚厚的尘土。我和方碧玉与他们擦肩而过时,感到他们用仇恨的目光斜视着我们。我下意识地按按衣袋,人民币一沓全在。田野已基本光秃秃了,只有一小片一小片的棉花柴还没拔。偶尔也有一棵树在路边挑着碧绿的叶子,生出许多妖气来,因为别的树都已落叶惟独它不落叶。那次给我印象最深至今难以忘记的是一个体重足有二百斤的大胖子开着一辆用12马力柴油机组装成的小拖拉机。他端坐在驾驶座上,俨然一座巍巍肉山。车后的小挂斗上,竟插着八面大红旗,显得诡怪而神秘。开车的大胖子是我小学的同学,他把拖拉机的油门开到最大,黑烟滚滚,红旗猎猎,十分英勇悲壮。我和方碧玉向他打招呼。他对我们的招呼不屑一顾。他严肃的面孔在我们眼前一闪而过。
我跟方碧玉相视一笑,顿时觉得周身通电,精神振奋,如同中了魔法。我们同时转身同时说:
“追上他!”
道旁的百姓害怕这挂着旗子的车如同害怕一车烈火,纷纷闪到路边,有急忙中扭了脚的也不足为奇。有一头毛驴受了惊吓,拖着地排子车蹿到路沟里去了。赶车的农民扯着嗓子骂,不知他是骂驴还是骂车。那天的情景经常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闪出:一辆妖怪车在前跑,两个傻男女在后边追。
追呀追呀追呀追!
追上了。
大胖子刹住车,挪下车来,问我们:
“你们追我干什么?有事吗?”
我不满地说:
“开这么个破车,老同学叫着都不答应,要是开上吉普车,连你爹叫你也不会应。”
“老同学,你胡咧咧什么?”他弥勒佛一样笑着说,“我光顾聚精会神开车了,目不斜视,哪能看到你们?方碧玉你说对不对?”
方碧玉嘻嘻地笑起来。
“你开这车干什么去?”我问。
“不干什么。”他认真地回答。
“那你把我们送回家去行吗?”方碧玉问。
“当然行啦。”他说,“只要你大妹妹开了金口,甭说送到家,送到北极去都行。”
他站在车下拧着方向盘调转了车头,说:
“上来吧,你们。”
他跨上车,说:
“坐稳,走啦。”
扑扑通通一阵响,机器冒着黑烟,吭吭哧哧往前爬。
我说:“跑快点嘛。”
他说:“你别吵吵好不好?嫌慢坐炮弹去。”
忽听背后有人喊叫:
“方碧玉——方碧玉——小方——”
原来是李志高。
我说:“等等他。”
胖子说:“就你嗦,让他追就是了。”
李志高追上来,一个蹿跳上了车,跟方碧玉坐在一起,气喘嘘嘘地说:
“一转眼就不见了你们,我到处找,有人说你俩结伴回家啦,把我急得呀,在门口转呀转,一转眼看到你们在车上。”
“你不回家?”方碧玉冷淡地问。
“我没有家,”李志高说,“革命者四海为家嘛。”
“找我有事?”方碧玉问。
“没什么事,”李志高脸皮有点红,说,“反正我无家可归,想送送你们。”
“方碧玉武功超群,八个小伙子也近不了她的身,还用你送?”我说:“李大哥你回去吧。”
他说:“送送吧,这么威风体面的红旗车,我坐会儿过过瘾。”
夜色渐渐洇上来,一钩新月在西南方很矮地挂着。棉花加工厂那盏水银灯亮了,碧绿碧绿,像魔鬼的眼睛。胖子把车灯打开,本来有两只灯,坏了一只,只亮一只,独眼龙,一道略呈绿色的白光,照着崎岖的路面。
走了一会儿,胖子停车,说:
“你们下去吧,快到村了。”
“胖子,送人送到家。”我说。
“不行不行,我有任务,耽误了不得了。”
“下吧下吧,”方碧玉跳下来说,“你快回吧,耽误你功夫真不好意思。”
李志高也跳下来。方碧玉说:
“你就别下了,顺便坐回去吧。”
“不,不,”李志高说,“我愿意走走。”
胖子调过车头,一加油门,窜了。
方碧玉说:“老李,你快回吧,俺到村了,没法招待你。”
李说:“没事没事,我侦察过你们村的地形,村头有个麦草垛,垛上有一个大窟窿,送你们到村后,我钻到草垛里去睡一夜,明早你们回厂时叫我一声,咱们一块走。”
“你这人有神经病吧?”方碧玉说。
“我这人喜欢冒险,喜欢干别人不敢干的事情!”他说。
方碧玉再也没有吱声。
到了村头,李志高果然钻到草垛里去了。
方碧玉站在草垛前,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星光洒下来,一切都朦胧,失去了真面目。
后来我一直在想,如果李志高不英勇地夜宿草垛,就不会有紧随其后的浪漫故事。我猜想,事情发展到危急关头,方碧玉也许会捶打着李志高的胸膛,悲愤交集地哭诉: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在那麦草垛里过夜?到了这步田地,你又软了,熊了,像受了惊吓的鳖一样,把脖子缩了回去!
“多少缠绵曲折的男女爱情故事,都沉痛地证明和宣告:女人的爱情之火一旦燃烧起来,就很难扑灭;而男人,在关键时刻总是像受了惊吓的鳖一样,把脖子缩了起来。”十八年后,我喝了一大杯酒对着与我对饮的李志高说。
李志高头发根部颜色红黄,一看就知道是染过了的。他已是县棉油厂副厂长,四十多岁的人了。他喝了一口酒,用筷子挑挑捡捡夹了一根碧绿的菜梗放到嘴里,愁苦满面地说:
“活到如今,我只信命,别的什么都不信了。”
我正准备激烈地反驳他时,他的十八岁的女儿李棉花穿着一身艳丽的衣裳闯了进来。这姑娘很像孙红花。她咕嘟着嘴对李志高说:
“爸爸,我要改名字!”
“为什么?”李志高问。
她说:“你给我起了这么个破名字,丑名字,土名字,同学们都笑话我。”
“我跟你妈是在棉花加工厂里相识、结婚,然后有了你,所以叫你‘棉花’。”李志高说。
她反驳道:“在棉花加工厂里相识就叫我‘棉花’,要是在化肥厂里相识就该叫我‘化肥’,在橡胶厂里相识就该叫我‘橡胶’是不是?”
李志高苦笑着说:“胡搅蛮缠!你打算改成什么名字?”
她说:“我准备改成李口百惠子!”
李志高说:“随你自己的便吧,你改成山本五十六我也不管了。”
我相信,方碧玉和李志高的浪漫史上最幸福、最富有爱情特征的一夜,也是李志高夜宿草垛的一夜。过了这一夜,他们的关系便突飞猛进,迅速发展,很快把事情推向高潮,同时也推向深渊。
那天,他沾着一头麦糠与我们同归棉花加工厂。在冉冉上升的朝阳里,他头上的麦壳像黄金,他的微笑也像黄金一样灿烂。
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我虽然痛苦但却清楚地意识到:方碧玉与李志高才是天生的一对,我不是李的势均力敌的对手。我缺少夜宿草垛的勇气。我决定退居二线,发扬风格,为他们二人穿针引线,搭桥铺路,充当一个光荣、高尚的第三者。在我还年轻的时候,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方碧玉从她的花书包里掏出四个热得烫手的红皮鸡蛋,分给我和李志高每人两个。拿着鸡蛋,我的灵魂在哭泣。我意识到这鸡蛋是为谁而煮。虽然都是同样的红皮鸡蛋,但李志高那两颗重若泰山,我这两颗轻如鸿毛。一个早起捡狗屎的老头满脸冰霜地看着我们,吓了我们一跳。
她用我认为是充满了似水柔情的眼睛抚摸着李志高那张棱角分明的脸。他毫不客气地往口里塞着鸡蛋,鸡蛋黄噎得他泪流满面。她笑起来,并且用半握的拳头捶打了一下他的背。这一拳是他们爱情的定音鼓。一锤定音。这一拳看起来打在李志高背上,实则打在我的心脏上。完了,我已经被淘汰了。李志高大笑起来,鸡蛋残渣在笑声中喷出,好像横飞的弹片。随着笑声,他的头颅在抖动,头上蓬松的黑发跳跃,宛如啼鸣雄鸡尾巴上的翎毛。那时候已经流行留长发,那时候留长发是反社会反传统的鲜明标志。我听棉检室的“一撮毛”赵一萍说过,男人留长发是吸引女性的需要。她举了两个富有说明力的例子来论证她的理论。她说国外有一位科学家做过这样的试验:剪掉雄狮头颈上的长毛,那雄狮身边的雌狮立刻离它而去,去寻找头颈上有长毛的雄狮。剪掉雄鸡尾巴上的卷曲高扬着的翎毛,雄鸡便被母鸡们啄死。由此可见,毛发对雄性是多么的重要,这不但关系到吸引配偶,而且关系到生死存亡。我摸了一下自己光秃秃的头颅,在自惭形秽的同时,暗下决心要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头发,即便吸引不了方碧玉,也要吸引别的雌狮和母鸡。
一路说了许多话,其实都是废话。对话的内容对陷入情网的男女来说变得毫无意义,这时传递性与爱的信号的载体是他们各自的声音。我也说了不少话,看起来我们三人的谈话是一个和谐整体,实际上我的话是对他们互相传递爱情信号过程中施放的干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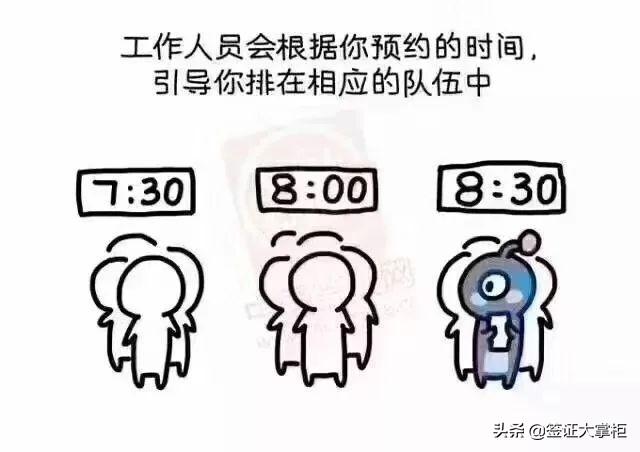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