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悉尼朋友—一位爱美优雅的老妇人

我的这位悉尼朋友名字叫Emy,认识她是在十五年前。那时我儿子在悉尼读预科,之后就读悉尼大学。儿子初中开始就住校,高二就去了悉尼读预科,是我的独生子。因为自小离家,所以在我的内心深处对他有种深深的愧疚。他在悉尼读书期间只要我有长假或年休假,我都会尽量的飞过去陪伴他。那时的机票也还便宜,从香港机场起飞到新加坡转机往往来回双程票5000多,运气好的时候还可以买的3000多的,所以工资的一部分就贡献给了航空公司了。我的朋友们经验之谈告诉我在儿子没有女朋友或结婚之前尽量多点陪伴,到了他有女朋友或结婚之后就不需要你的陪伴了,如果“陪伴”太多反倒引起他的反感,也就是说其实跟儿女在一起的时光是短暂的。我确实也是深有体会,于是给航空公司打工就打工吧,钱财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不必太在意。我先生的哥哥弟弟都在悉尼开中医骨伤科诊所,那时儿子跟同学一起租房住,我也就住到二哥的诊所了,早早晚晚或者没有外出基本上也就在诊所帮忙。我是学医的,做了二十几年医生,虽然不太懂中医,但互通还是可以的。诊所的病人里华人特别多,所以“结巴英语”的我也可以凑合。我除了国语外,潮州话、粤语、客家话都没问题,而在悉尼这几种话已经足够应付了。诊所以针灸为主,配合推拿,中药膏贴等等。所以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忙制作膏贴,陪客人聊天,解释病情等等,还是挺受欢迎的。
有一位客人经常光顾诊所,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她就是Emy。印象特别深的原因是她几乎与所有的澳洲人不同。她与不管来自全世界任何地方的澳洲居住者有着天壤之别的装扮。一般澳洲人穿着都非常随意,普通的体恤,牛仔裤或普通的毛衣和裤子。甚至是套头衫加“孖烟囱”短裤,包括冬天都可以是套头衫加“孖烟囱”短裤,外面再套件宽大的羽绒外套,男女都差不多。即使在CBD上班的高级白领也就是西装领带,手夹一个公文包。女孩子也只是一套干练的上班服。只有傍晚时分在夜总会的门口才会看到穿着黑色晚礼服的高挑女郎手挽着肥胖的中年秃头男士在街上款款而行。我曾经在下班高峰期很无聊的站在中央火车站出口一个多小时,目不转睛的盯着从火车站出来的人流,观察他们的服饰。很可惜的是几乎没有见到一例服饰漂亮得体的女士。而Emy当时五十多岁,中等个头,大约有一米六多一点,不胖不瘦,身材恰到好处,尤其腰身还是不错,没有中年人的水桶腰。几乎球形的脸庞圆乎乎的,脸蛋几乎是完美的弧线,没有任何棱角。眼睛大大的,不知道是不是假睫毛,看上去挺长的,眼睛经常半眯着,眼眸里含着微笑。鼻梁略显高耸,但不是西方人的高鼻梁,是典型的东方人种的高鼻梁。嘴裂稍长,嘴唇稍稍有点厚,但虽不是樱桃小嘴,配在她圆圆的脸庞上还是非常合理的配搭。脸上涂着厚厚的一层胭脂,大红的唇膏把这略显肥厚的嘴唇弄的特别显眼。尤其特别的是头发烫的非常蓬松,高高隆起,加着摩丝的固定,使通过头发的膨起可以增加人体的高度起码8—10厘米,因此整个人显得比较高挑。她几乎每次来诊所都穿着各种各样的漂亮裙子。第一次见她穿的就是略露丰乳的低胸V领,上臂泡泡状,前臂收紧,腰身紧缩,裙摆又是泡泡的长裙,上身白色为主带点粉红色小花,下摆略深的蓝色,裙子的材质应该是丝绸的。大红指甲的手里拿着一个镶嵌着黑色珠宝的小袋子。胸前的项链,大大的圆形耳环和无名指上的戒指都是由白金和钻石为支撑,中间镶嵌着一颗硕大珍珠的,看上去是一个系列套装。这些首饰在阳光下特别的闪耀。当她从奔驰650的小轿车下来,第一次出现在我的眼前时,我恍惚看到的是一位十八世纪的欧洲贵妇人款款而来,有点幻觉,有点神游。她跟二哥很熟,经二哥的介绍我知道她是印尼籍的华人,是我们广东的“客家妹”,于是在她做理疗的过程中,我们开始攀谈。她会讲普通话和客家话,也能看懂大部分的中文字。她的父亲是我们广东客家地区的,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到了印尼。估计当年就是从松口古镇出发下南洋的那一批,跟他信,英拉的爷爷,李光耀的父亲这一类到南洋讨生活的一样。她的父亲是有点文化的人,妈妈也是家乡一起过来的。在印尼定居做生意,她是在雅加达出生的。从小除了学校的功课之外一直在补习学校学习中文,学习普通话,家里坚持讲客家话。所以她除了英语,印尼话还会中文,普通话和客家话。十八岁就结婚了,也是嫁给一个印尼籍的华人。夫家拥有印尼群岛中的三个岛屿,全部都是种植珍珠的,是印尼的珍珠大户。她生育了三个女孩,也许是印尼的自然环境,很奇怪,在印尼很难生出男孩的,而印尼的法律是一夫四妻制,虽然她没有告诉我他的先生有几位夫人,但我估计她是大太太,因为她的年龄跟他的先生一样。她三十几岁就到了印尼定居,带着她的三个女儿。每年节假日也会回到雅加达居住。现在她五十多岁了,大女儿已经结婚,住在悉尼但离她家很远,故很少回来。二女儿嫁在雅加达。三女儿在美国读大学,所以她现在跟保姆一起住。也许是缘分,我这个从来不讲究打扮,永远都是衬衫长裤,从来不化妆,素面朝天的中年女人竟然跟这么一位浓妆艳抹的贵妇人很谈得来,真有点不可思议。她几乎每隔一天就来诊所一次,每次呆上两小时,而只要我在诊所,这两小时几乎就被她征用,慢慢的我们成了好朋友。每次都是她主讲,她几乎告诉了我她这一生的所见所闻,说到开心时会不顾一切的哈哈大笑。也经常让我告诉她爸爸老家的情况,我也如实的告诉她想要知道的一切。尤其是她说父亲告诉她家乡很穷,他们当时是怎样为了摆脱贫穷漂洋过海,差点丧命海中和到了印尼怎样的做苦力,做小生意等等艰苦奋斗的历史。我也告诉她我上山下乡的经历以及如何通过考大学改变命运和改革开放后高速发展的变化,邀请她到中国来玩等等。她很爱惜身体,于是我也就尽可能的给她听诊,检查,讲解身体健康和疾病的问题。还告诉她去医院检查哪些项目等等,俨然成了她的家庭医生。
有一个周末她盛情的邀请我们一家到她家做客。她家住在悉尼的东区,东区历来都是悉尼的富人区,房价是西区的N倍,是同样被誉为富人区的北区的二到三倍。不过尽管东区的房子很贵,但进入东区的道路却不是平坦笔直的大道,而是弯弯曲曲,起起伏伏的两车道。对于习惯深圳平坦大道的我真的很不习惯。路旁的建筑物虽然许多维多利亚式的欧洲风格,但也不少现代风格的 ,各种各样,琳琅满目,感觉有点“建筑博物馆”。我们的车行驶在这蜿蜒小道,途中经过库克船长当年登录澳洲的登录点,登录点除了一块大石头写着“库克船长登录地”之外就是一座不大的白色灯塔,其他就没什么了。经过大约一小时的车程到达了Emy的房子门前。房子的大门没什么特别,也不是非常豪华,但进入大门之后却是令我大为惊叹。大约有200多平方米的前花园种植着许许多多的花草,园林工正在认真的修剪枝叶。我认识的是玫瑰,好多的玫瑰花正以灿烂的笑容迎接我们这些远方的客人,还有许许多多的花我叫不出名字。花圃中还有几颗不大不小的树木,有一处火山岩石构成的假山,假山上流水潺潺,假山和流水下面有一个十几平方米的鱼池,池中美丽的红鲤鱼自由自在,灌木丛篱笆将花圃隔开一条人行小道。我们沿着人行道进入大别墅。别墅也是维多利亚式的风格,许多罗马柱和白色人体雕塑和花朵雕塑,蕾丝花边的屋檐和栏杆清一色的白。客厅中央有一大半圆圈的布艺沙发,沙发垫是粉红色的底色和深红色的大花,一看就知道主人一定是女性的。沙发前面白色流线型的茶几上摆放着一瓶很鲜艳的玫瑰花,旁边是水果盆。客厅的正中墙壁上是一个巨大的液晶电视。电视的下方是一个大的壁炉。墙壁的两侧一边是中国式的国画,也是花画,有牡丹、红梅、菊花等等,大约是四幅吧,因为这种画太常见了,反倒不是很留意。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客厅右侧的墙壁上镶嵌着一块有四平方米左右的陶瓷画,画中是福禄寿全图。Emy看我眼睛直愣愣地注视着这幅陶瓷画,她及时的解释说这是她专门找人从中国定制的。真不简单,在几乎完全欧式的房间里竟然如此和谐地摆放着这幅来自中国的陶瓷画,而且是古人最信奉的福禄寿。此刻我内心非常激动,无论身在何方,无论接受什么教育,骨子里的东西还是与生俱来的,这就是根,是深埋的根!主人家很大,房间很多,餐厅里摆放着一台可以坐十几个人的方形餐桌,餐桌上也是摆放着鲜花。餐厅的墙壁上挂着许多家庭生活照,其中许多是她和先生一起外出游玩的合影,可以看得出她是很幸福的,丈夫对她也是很宠爱的。另外有一间是Emy的工作室。她一辈子都没有外出参加工作,但她喜欢珠宝设计。设计台上有许多图纸,我随手翻看了几张。虽然我不懂珠宝设计,但也可以看得出设计很优美,很浪漫。她说她有固定的加工师傅,她设计完了就直接找这位师傅加工,然后卖给她的朋友或朋友的朋友,偶尔也放在悉尼CBD的一家珠宝店售卖,因为珍珠是自家产的,所以她选的都是最上乘的珍珠。那天她还送了我几颗很珍贵的珍珠,因为我几乎不带首饰,所以后来我找深圳的师傅加工成耳环、项链、戒指一套转送给了亲家母,这也算是我这辈子能拿出来送给她最珍贵的礼物了。
Emy的别墅实在太大了,除了别墅本身,前花园很大,屋后更是吓人。有一个两条道的恒温游泳池,桑拿房和一座凉亭。有一个可以比赛用的正规网球场,还有半个篮球场,还有后花园的许多树木。这是我见过最大的私家别墅了。不过因为房子太大人太少,她正准备卖掉。
Emy的保姆是印尼当地人,咖啡色的皮肤,个头不大,大约30来岁。她是拿着学生签证过来的,Emy负责她的全部学费和生活费,她负责家务和打扫卫生。Emy说一个保姆从读高中到大学毕业,大约七八年,全部费用她出。大学毕业后回去找工作,嫁人。每一个保姆最终都对她跟女儿差不多,就算是干妈吧。这种模式的保姆也是我第一次见的。
后来Emy卖掉了这所大房子,到city的情人港旁边买了个二百多平方米的公寓,270度海景房。有了微信以后我们的聊天就更多了,她常常发一些照片给我,告诉我她一家的生活。现在又在北区重新换了别墅,跟小女儿住在一起。看着她永远都那么漂亮,那么开心,一家人融融乐乐真为她高兴。疫情过后我如果再去澳洲,一定去她的新别墅做客。在异国他乡有这么一位美丽优雅的朋友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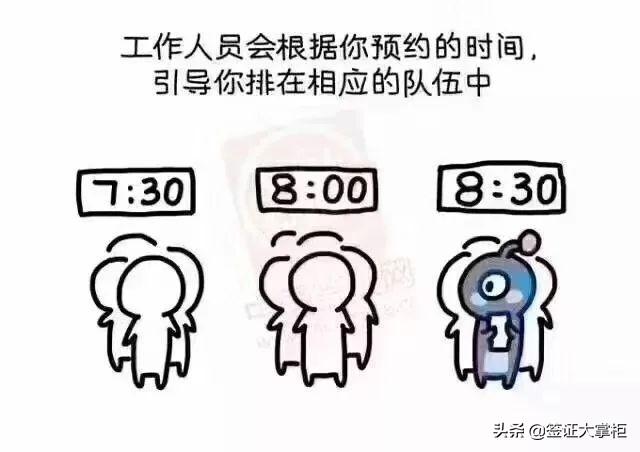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