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潘天寿、陆抑非先生习画事

1964年,经西泠印社第一任老社员朱醉竹、阮性山引见,周天初先生推荐,我有幸结识了潘天寿先生,并有意拜他为师。1965年初,潘先生在得到我父母同意之后,便让我到他家中习画,那一年,我刚满19岁。
 潘先生给我的第一个教诲便是“学画先学做人”。在他看来,绘画跟人的文学修养、家庭教育、文化背景都有着很大的关系,学会做人是画画的基础。潘先生向我详细讲述了自己的习画历程。少时,他从临摹《芥子园画谱》入门,可算是自学成才,时日久远,也积下了不少画稿;抗战时期举家逃难,他的画谱及习作被锁在家中,等抗战结束回到家乡时,家门已被撬开,他愕然发现自己临摹的作品竟被人拿来包了花生米。嗜画如命的潘先生立刻将所有包着花生米的画稿逐一买回,留存了下来。 潘先生经由褚闻韵(诸乐三之兄)推荐,结识了吴昌硕先生。当时他带着自己的画去请教吴先生,先生看后认为画得很好,但比较险,有如在悬崖峭壁间行走,成则独树一帜,败亦不无可能,他并委婉地说:“只恐荆棘丛中行太速,一跌需防堕深谷”,这番言语对潘先生深有启迪。此后,潘先生又画了一幅画请吴昌硕先生看,吴先生直言他“昌”气太重,应该有自己的面貌。自此之后,潘先生开始深入思考“个人风格”的问题,并在作品中予以实践。 某日,我拿了一幅兰花(上有“三片叶子一朵花”)给潘先生过目,先生看后连连点头,称赞我画得不错,构图很好,花画得尤其好,有个人特点,就是叶子稍微嫩了一点,并宽慰我慢慢来。此后,潘先生言传身教,多次向我强调绘画的个性化特征。他认为,一味模仿老师是“笨子孙”,他叮嘱我要多画,每次去他家,我都会带上新作品,他则会围绕着作品来讲解画法。潘先生常说,画画要多取景于自然,要画从诗出,做到“我发我声”,构图气局要大,要追求大开大合的境界,少画折枝以免落俗。多年来,我始终铭记潘师教诲,绘画风格深受其影响。 1966年文革开始,画中国画被批成了“封资修”,很多学画的人都不敢再画了,潘先生预感到中国画将面临劫难,他再三叮嘱我要将中国画传承下去,绝不能让它断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先生给我定下了学习的方向,要求我多看古画,多读古诗,在提高绘画技巧的同时,提高人文修养。 文革初期,潘先生就被学校造反派定为了反动学术权威,受到了很多不公正的批判。江青还直接指示造反派,诬陷潘天寿为国民党特务,要他写交待材料,贴在百货公司旁的墙边。潘先生手写的《我的检查》是傍晚贴的,围观者甚众,我晚上十一点钟去看时依旧人头攒动。第二天早上五点多我又去看,发现检查已被人揭走,当我告诉潘先生时,他露出了文革以来的第一个笑脸。 1967年的一天,潘先生接受批斗回家后痛心地对我说:”人心不古,我的学生当着很多人的面打我的巴掌,要我跪下去,我不跪他们就用脚踢我的腰。”那一回,他的腰被踢伤了,当晚就便血了,我想陪他去省中医院就医,他说:“今天就算了,如果明天早上我还便血的话你再陪我去看。”第二天大早,我便赶到潘先生家中了解情况,他告诉我小便已没有血了,但我印象更深的,是他后面说的一段话:“当年我去看病的时候,很多人是围着我转的,现在很多人看见我就逃,唯恐避之不及,既然没有血了就不要去了吧。” 潘先生的小儿子因为父亲的缘故被分配到了温州文城,大儿子则因肝癌过世,女儿在百货公司上班,工作忙碌,因此师母常嘱咐我多来看看先生,多陪伴他一下。那段时间,我每隔两三天就会去先生家中一趟。师母经常会跟我讲:潘先生今天在学校里又被批斗了。每次我去潘先生家,他总是拉着我的手先把我带到屋里去再说话。有时候他在学校被批斗还没回来,我就坐在他家中,一直等着他回家。 有一次,红卫兵造反派让病重的潘先生坐在垃圾车里游街,潘先生回来后对我说:“他们还要把我拉到老家去批斗,那是要我的命啊。”1969年,潘先生终于还是被押到了老家宁海去批斗,回来后,他整个人精神状态非常不好,没多久便因病重而住院了。他住在省中医院三楼楼梯口的第一个病房里,门口站着两个红卫兵,不允许人进去看望他。我再三申明自己是工人阶级,红卫兵才让我进门。潘先生看到我之后,只冲我点了点头,示意我不要讲话,我心领神会,只能紧紧地握住潘先生的手,在这样的高压之下,我们只能通过眼神交流,其情状可悲可叹。 这次批斗对潘先生的打击非常巨大,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某日,他将我叫至家中,语气沉重地对我说:“我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留念的,笔墨纸砚都被造反派抄家抄走了,画也都被抄走了,如果以后能归还,希望能送几张画给你留作纪念。”言毕,潘先生拿出了家中仅存的几张照片,一张是他的个人半身近照,一张是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作画时的照片,执意送我留念,这两张照片我至今珍藏,视若珍宝。那一天,他还对我说:“我现在身体越来越不好,想给你推荐一个老师,他叫陆抑非。因为我们浙江的画黑气太重,没有生气,这个人的色彩功夫自南而北是第一人,所以我把他请来美院教书,冲一冲我们浙江的黑气。我就是吃亏在没有学过写生,你去把他的色彩功夫和写生功夫学到手,要到大自然中去写生,不仅写形,更要写神,对你日后画画肯定大有帮助。”随后,潘先生就在报纸边上撕下了一条,提笔写下了推荐信:陆先生,我介绍我的学生谢伟强到你那里去学习,希望你能多多指导。 陆抑非先生看过这张纸条后郑重地对我说:“你是潘先生介绍来的学生,我必须要对得起潘先生。”就这样,陆抑非先生正式收我为入室弟子。此后,我便往返于两位老师家中学画,这段时期非常宝贵,我同时受到了两位恩师的指点,绘画水平大有长进。此外,潘老还为我引荐了多位师长,如诸乐三、吴茀之、余仁天、沙孟海等等,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帮助我,也希望我能博采众长、精进画艺。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沙老因文革之故已封笔,但在看过潘先生的推荐信之后专门为我开笔,书写了两幅毛主席诗词赠予我,并题上了“伟强同志正腕”的字样。 1971年8月,潘先生突然把我叫至家中,对我说:“你跟陆先生学画画总要有个笔名、有个斋号吧,我就给你取一个‘止庭’的笔名吧,斋号就叫‘兰若居’,希望你淡泊名利,诚心修身,凡事适可而止,能像在庙中修行一样认真学习。”我自然是欣然应允。“止庭”典出东坡,他被三贬黄州之后去看黄石谷,在途中看到一个凉亭想歇歇脚,但见凉亭匾额上书“止足亭”三个大字,东坡即恍然大悟,转身而返。他悟到了做人要知足,要淡薄名利。我心中明白,潘先生为我取笔名“止庭”,既是让我懂得适可而止,更暗示了师徒关系的薪火相传,令我感怀至今。为我取下笔名和斋名后的一个星期,潘先生便与世长辞了,现在想来,他定然已有预感,料想自己时日不多,便为我做了最后的指点。每每想到这段往事,我都唏嘘不已。 陆抑非先生收我入门之后,在绘画上一直对我严加要求,每次画完呈上,他都会细细审视评点,我至今仍然保存着陆师亲笔批注过的作品近百件。与潘先生的教法有所不同,陆师总让我从读画默写开始,并时常给我演示如何背临。记得某日,他拿出画册中八大山人的一幅《杨柳八哥》给我看,未几即拿开书背临,他画的是放大后的尺寸,但竟与书中原作几乎一模一样。陆抑非先生常说学画要从宋画起步,由规距入手,有了扎实的基础之后再学明清绘画,如此这般才能画得灵活生动。此外,他也经常让我临摹家中收藏的各类名人古画,尤其是对南田的枝法,芍药的勾花点叶法,陆恢的蔬果枝法以及任伯年的禽鸟设色等,均做了详细讲解和指导。陆先生曾说:花无定色、鸟无定名,不要拘泥于像不像,主要是传神为上,他的这番见解对我影响至深。 陆抑非先生对我视如已出,为我引介了多位上海名家,如王个移、谢稚柳、钱君匋、唐云等人。1972年10月27日,唐云先生来杭,到陆抑非先生家中作客。陆先生让我作陪饮酒,唐云先生三瓶酒后兴致极高,连续与陆先生合作了四张大画,唐先生又对陆先生说借个印给伟强画张兰。这张兰画得非常用心,陆先生看后连连夸赞。唐云先生一再嘱咐我说,陆抑非先生是位难得的好老师,你一定要努力。此后,法国画家赵无极来美院办展邀请了陆抑非先生,陆先生又将我引荐给了赵无极先生。总之,陆先生创造了很多机会,让我结识艺术名人,也使我得到了更加多元的滋养,可以说,先生在我的培养问题上可谓是殚精竭虑、煞费苦心,令我感激不尽。 陆先生对我极为信任,有时全家去常熟老家,便将钥匙交我保管,家中大小事务均由我打理,我也一直帮他处理各种生活琐事,如:买米、买煤、存钱等等。当时陆先生子女都不在身边,我们俩情同父子,他两次在浙二医院住院,都是我陪夜,在先生床边尽心照顾,寸步不离,但即便如此,又怎抵先生深情厚谊? 我如今能画几笔画,全都仰仗潘天寿先生和陆抑非先生的精心指导,也感激他们为我引介的诸位师长,两位先生的恩情我已铭记在心,永生难忘。
潘先生给我的第一个教诲便是“学画先学做人”。在他看来,绘画跟人的文学修养、家庭教育、文化背景都有着很大的关系,学会做人是画画的基础。潘先生向我详细讲述了自己的习画历程。少时,他从临摹《芥子园画谱》入门,可算是自学成才,时日久远,也积下了不少画稿;抗战时期举家逃难,他的画谱及习作被锁在家中,等抗战结束回到家乡时,家门已被撬开,他愕然发现自己临摹的作品竟被人拿来包了花生米。嗜画如命的潘先生立刻将所有包着花生米的画稿逐一买回,留存了下来。 潘先生经由褚闻韵(诸乐三之兄)推荐,结识了吴昌硕先生。当时他带着自己的画去请教吴先生,先生看后认为画得很好,但比较险,有如在悬崖峭壁间行走,成则独树一帜,败亦不无可能,他并委婉地说:“只恐荆棘丛中行太速,一跌需防堕深谷”,这番言语对潘先生深有启迪。此后,潘先生又画了一幅画请吴昌硕先生看,吴先生直言他“昌”气太重,应该有自己的面貌。自此之后,潘先生开始深入思考“个人风格”的问题,并在作品中予以实践。 某日,我拿了一幅兰花(上有“三片叶子一朵花”)给潘先生过目,先生看后连连点头,称赞我画得不错,构图很好,花画得尤其好,有个人特点,就是叶子稍微嫩了一点,并宽慰我慢慢来。此后,潘先生言传身教,多次向我强调绘画的个性化特征。他认为,一味模仿老师是“笨子孙”,他叮嘱我要多画,每次去他家,我都会带上新作品,他则会围绕着作品来讲解画法。潘先生常说,画画要多取景于自然,要画从诗出,做到“我发我声”,构图气局要大,要追求大开大合的境界,少画折枝以免落俗。多年来,我始终铭记潘师教诲,绘画风格深受其影响。 1966年文革开始,画中国画被批成了“封资修”,很多学画的人都不敢再画了,潘先生预感到中国画将面临劫难,他再三叮嘱我要将中国画传承下去,绝不能让它断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先生给我定下了学习的方向,要求我多看古画,多读古诗,在提高绘画技巧的同时,提高人文修养。 文革初期,潘先生就被学校造反派定为了反动学术权威,受到了很多不公正的批判。江青还直接指示造反派,诬陷潘天寿为国民党特务,要他写交待材料,贴在百货公司旁的墙边。潘先生手写的《我的检查》是傍晚贴的,围观者甚众,我晚上十一点钟去看时依旧人头攒动。第二天早上五点多我又去看,发现检查已被人揭走,当我告诉潘先生时,他露出了文革以来的第一个笑脸。 1967年的一天,潘先生接受批斗回家后痛心地对我说:”人心不古,我的学生当着很多人的面打我的巴掌,要我跪下去,我不跪他们就用脚踢我的腰。”那一回,他的腰被踢伤了,当晚就便血了,我想陪他去省中医院就医,他说:“今天就算了,如果明天早上我还便血的话你再陪我去看。”第二天大早,我便赶到潘先生家中了解情况,他告诉我小便已没有血了,但我印象更深的,是他后面说的一段话:“当年我去看病的时候,很多人是围着我转的,现在很多人看见我就逃,唯恐避之不及,既然没有血了就不要去了吧。” 潘先生的小儿子因为父亲的缘故被分配到了温州文城,大儿子则因肝癌过世,女儿在百货公司上班,工作忙碌,因此师母常嘱咐我多来看看先生,多陪伴他一下。那段时间,我每隔两三天就会去先生家中一趟。师母经常会跟我讲:潘先生今天在学校里又被批斗了。每次我去潘先生家,他总是拉着我的手先把我带到屋里去再说话。有时候他在学校被批斗还没回来,我就坐在他家中,一直等着他回家。 有一次,红卫兵造反派让病重的潘先生坐在垃圾车里游街,潘先生回来后对我说:“他们还要把我拉到老家去批斗,那是要我的命啊。”1969年,潘先生终于还是被押到了老家宁海去批斗,回来后,他整个人精神状态非常不好,没多久便因病重而住院了。他住在省中医院三楼楼梯口的第一个病房里,门口站着两个红卫兵,不允许人进去看望他。我再三申明自己是工人阶级,红卫兵才让我进门。潘先生看到我之后,只冲我点了点头,示意我不要讲话,我心领神会,只能紧紧地握住潘先生的手,在这样的高压之下,我们只能通过眼神交流,其情状可悲可叹。 这次批斗对潘先生的打击非常巨大,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某日,他将我叫至家中,语气沉重地对我说:“我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留念的,笔墨纸砚都被造反派抄家抄走了,画也都被抄走了,如果以后能归还,希望能送几张画给你留作纪念。”言毕,潘先生拿出了家中仅存的几张照片,一张是他的个人半身近照,一张是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作画时的照片,执意送我留念,这两张照片我至今珍藏,视若珍宝。那一天,他还对我说:“我现在身体越来越不好,想给你推荐一个老师,他叫陆抑非。因为我们浙江的画黑气太重,没有生气,这个人的色彩功夫自南而北是第一人,所以我把他请来美院教书,冲一冲我们浙江的黑气。我就是吃亏在没有学过写生,你去把他的色彩功夫和写生功夫学到手,要到大自然中去写生,不仅写形,更要写神,对你日后画画肯定大有帮助。”随后,潘先生就在报纸边上撕下了一条,提笔写下了推荐信:陆先生,我介绍我的学生谢伟强到你那里去学习,希望你能多多指导。 陆抑非先生看过这张纸条后郑重地对我说:“你是潘先生介绍来的学生,我必须要对得起潘先生。”就这样,陆抑非先生正式收我为入室弟子。此后,我便往返于两位老师家中学画,这段时期非常宝贵,我同时受到了两位恩师的指点,绘画水平大有长进。此外,潘老还为我引荐了多位师长,如诸乐三、吴茀之、余仁天、沙孟海等等,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帮助我,也希望我能博采众长、精进画艺。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沙老因文革之故已封笔,但在看过潘先生的推荐信之后专门为我开笔,书写了两幅毛主席诗词赠予我,并题上了“伟强同志正腕”的字样。 1971年8月,潘先生突然把我叫至家中,对我说:“你跟陆先生学画画总要有个笔名、有个斋号吧,我就给你取一个‘止庭’的笔名吧,斋号就叫‘兰若居’,希望你淡泊名利,诚心修身,凡事适可而止,能像在庙中修行一样认真学习。”我自然是欣然应允。“止庭”典出东坡,他被三贬黄州之后去看黄石谷,在途中看到一个凉亭想歇歇脚,但见凉亭匾额上书“止足亭”三个大字,东坡即恍然大悟,转身而返。他悟到了做人要知足,要淡薄名利。我心中明白,潘先生为我取笔名“止庭”,既是让我懂得适可而止,更暗示了师徒关系的薪火相传,令我感怀至今。为我取下笔名和斋名后的一个星期,潘先生便与世长辞了,现在想来,他定然已有预感,料想自己时日不多,便为我做了最后的指点。每每想到这段往事,我都唏嘘不已。 陆抑非先生收我入门之后,在绘画上一直对我严加要求,每次画完呈上,他都会细细审视评点,我至今仍然保存着陆师亲笔批注过的作品近百件。与潘先生的教法有所不同,陆师总让我从读画默写开始,并时常给我演示如何背临。记得某日,他拿出画册中八大山人的一幅《杨柳八哥》给我看,未几即拿开书背临,他画的是放大后的尺寸,但竟与书中原作几乎一模一样。陆抑非先生常说学画要从宋画起步,由规距入手,有了扎实的基础之后再学明清绘画,如此这般才能画得灵活生动。此外,他也经常让我临摹家中收藏的各类名人古画,尤其是对南田的枝法,芍药的勾花点叶法,陆恢的蔬果枝法以及任伯年的禽鸟设色等,均做了详细讲解和指导。陆先生曾说:花无定色、鸟无定名,不要拘泥于像不像,主要是传神为上,他的这番见解对我影响至深。 陆抑非先生对我视如已出,为我引介了多位上海名家,如王个移、谢稚柳、钱君匋、唐云等人。1972年10月27日,唐云先生来杭,到陆抑非先生家中作客。陆先生让我作陪饮酒,唐云先生三瓶酒后兴致极高,连续与陆先生合作了四张大画,唐先生又对陆先生说借个印给伟强画张兰。这张兰画得非常用心,陆先生看后连连夸赞。唐云先生一再嘱咐我说,陆抑非先生是位难得的好老师,你一定要努力。此后,法国画家赵无极来美院办展邀请了陆抑非先生,陆先生又将我引荐给了赵无极先生。总之,陆先生创造了很多机会,让我结识艺术名人,也使我得到了更加多元的滋养,可以说,先生在我的培养问题上可谓是殚精竭虑、煞费苦心,令我感激不尽。 陆先生对我极为信任,有时全家去常熟老家,便将钥匙交我保管,家中大小事务均由我打理,我也一直帮他处理各种生活琐事,如:买米、买煤、存钱等等。当时陆先生子女都不在身边,我们俩情同父子,他两次在浙二医院住院,都是我陪夜,在先生床边尽心照顾,寸步不离,但即便如此,又怎抵先生深情厚谊? 我如今能画几笔画,全都仰仗潘天寿先生和陆抑非先生的精心指导,也感激他们为我引介的诸位师长,两位先生的恩情我已铭记在心,永生难忘。
口述:谢伟强 笔录:王小仙2017年8月29日星期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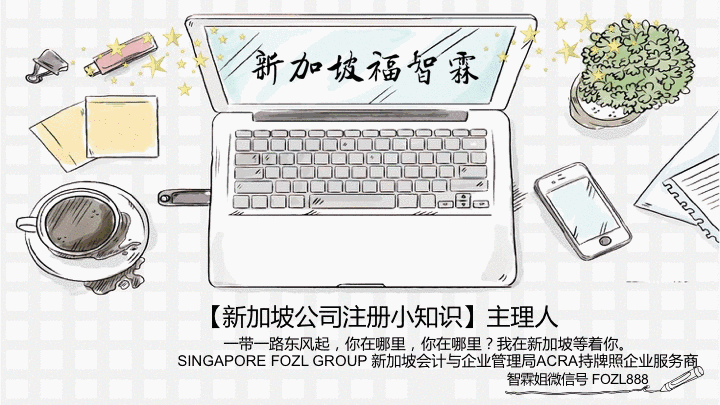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