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野:澳大利亚想与中国和好吗?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袁野】
在自吹和谴责了国会山暴乱一番后,特朗普结束了自己的总统生涯,留给世界的却是一地鸡毛,他的那些“跟班小弟”们也开始慌了,带头大哥走了,我们该怎么办?
澳大利亚就是其中之一。“五眼联盟”里,澳大利亚大概是最死心塌地的了,和中国交恶,则是莫里森政府“表忠心”的结果。特朗普拂拂衣袖走了,莫里森是不是要紧急掉头,而这个头该怎么掉,中国又会买账吗?
中澳关系为何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全世界的学者和研究机构,只要是在正经进行分析判断,不是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那种拿钱办事的,都得出了一个共识性的结论:和美国一样,澳大利亚还没学会适应一个崛起了的中国。
例如,前澳洲驻华大使芮捷锐(Geoff Raby)在其新书《中国的大战略和澳大利亚在全球新秩序中的未来》中强调,堪培拉的外交和战略政策必须建立在“对中国不可阻挡的崛起如何深刻改变世界秩序的崭新理解”的基础上。他说,澳大利亚需要用高超的技巧来驾驭一个新的“有界多极秩序”。
全球学者开给堪培拉的“药方”也是一样的:既要“应对”中国,也要与其合作。换言之,就是需要保持平衡,在竞合之间走钢丝。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研究荣誉退休教授休•怀特就写道:
“莫里森认为他可以与北京方面达成协议。但要管理与这个地区大国的关系,就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和妥协……中国是一个我们必须学会与之合作的国家,不仅因为在未来的几年乃至几十年里,没有哪个国家能提供与中国同样的出口机会。”
“我们必须做出妥协,在一些问题上让步,以便在其他问题上取得进展。有时情况不会很好,但当你与大国打交道时,这就是国际政治的运作方式。”
“现实情况是,国际关系像任何其他类型的关系一样,总是需要大量的妥协和让步……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必须做的,在一个我们不能事事随心所欲的世界里,我们要尽我们所能取得最好的结果。”
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所研究员梅丽莎•康利•泰勒说得更直接:
“当我听到有人说澳大利亚别无选择、只能与中国对抗时,我想起了新加坡驻华大使比拉哈里•考西坎的话:‘我曾经问过一名越南高级官员,河内领导层的变动对中越关系意味着什么。他回答说,每一位越南领导人都必须与中国和睦相处、并勇敢地面对中国,如果你不能同时做到这两点,你就不配当领导人。’”
“不幸的是,目前澳大利亚只做到了一半。”泰勒评论道。
法里德•扎卡里亚博士在澳大利亚罗伊研究所的2020年度演讲中也是这么建议的。这位哈佛博士拥有一大堆头衔:《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大西洋月刊》特约编辑、《纽约时报》多本畅销书的作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主持人,这绝对是西方主流舆论的代表了。他建议: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澳大利亚如何在保持其独立性的同时,继续确保与中国的贸易?……我认为,在某些方面,最好的样板是新加坡。李光耀曾对我说,他最骄傲的一件事是他能够维持新加坡独立的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被视为一个亲美国家,但从来不是一个反华国家,没有被中国认为是敌人。”
远在纽约的扎卡里亚可能是真的对西太平洋的情况不太了解,不然他不会建议让澳大利亚“屈尊”学习新加坡。他也许是忘了、也许压根就没意识到,新加坡能够做到这一点,首先是因为他没有堪培拉的那种对中国的种族和意识形态优越感。
走钢丝需要高超的政治技巧和手腕,但澳大利亚决策者目前还没有到讨论能力问题的程度,他们还停留在上一步:我愿不愿意走钢丝?我想不想在抗衡中国的时候维持起码的合作?
答案很明显:我不!

被种族主义困扰的澳大利亚外交
2019年,前新加坡外交官、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人们在做地缘政治判断时,靠的仅仅是冷静理性的分析吗?如果情绪影响了我们的判断,我们对此意识得到吗?还是说它是在潜意识层面里起作用?如果诚实地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承认:非理性因素总会发挥某种作用。
马凯硕是正确的。“中国不是高加索人种的国家,这本就是地缘政治竞争的一个因素,而且它或许也能解释为什么西方国家在情感上对中国崛起反应如此激烈。”
作为离中国最近的西方国家,澳大利亚的反应也是最激烈的,这并非巧合。“幸运之邦”对中国人的敌意比其建国的历史还要古老,从19世纪的“黄祸论”开始,这个国家就在坚持不懈地妖魔化中国,冷战时代这种妖魔化更是变本加厉,相较之下近几十年的和睦反倒像是插曲。
几年前,当中澳两国的关系开始紧张时,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国际关系学者潘成鑫就总结道,“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紧密经济联系未能动摇其历史思维方式,这或许并不令人意外”。他补充说,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地缘经济上的邻近似乎加剧了这种焦虑”。
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现代历史学教授詹姆斯•柯伦也在2020年12月的一场演讲中说,早在1893年,“澳大利亚殖民地杰出的知识分子”查尔斯•亨利•皮尔森就写道,中国是西方战略优势的最大潜在威胁,“澳大利亚同胞,那些生活在分隔白人和有色人种的边界上的人,将会是第一个敲响警钟的人,是第一个采取措施保卫西方文明的人。”柯伦教授说,在澳大利亚的国家战略心理中,“过去的幽灵”有一种反复出现的趋势,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冲动有时会压倒澳大利亚外交务实、理性的强大传统”。

新南威尔士大学的中国历史教授路易丝•爱德华兹(中文名李木兰)更深入地阐释了这一点。在澳大利亚世界中国研究中心的2020年度演讲中,这位曾翻译过《红楼梦》的教授直言痛陈,中澳关系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归根结底是因为澳大利亚人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
“澳大利亚与亚洲的关系正困在一台倒退的时光机里——我们的主流媒体、政客、公务员、文艺界和大学的的领导人都存在一个错误的观点:澳大利亚人是白人,他们的祖先来自利物浦、利默里克(爱尔兰城市)或是伦敦。很明显,他们无法真正看到这个国家的人口在语言、宗教、肤色和阶级上的全景。”
“澳大利亚的亚太观同样让人沮丧。我们是五眼联盟的成员——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但澳大利亚的眼睛却受困于战后的眼病——通常说这是‘斜视’。我们知道这种眼病,因为澳洲的许多高层在领导我们时一只眼睛盯着英国,一只眼睛盯着美国……而伴随着这些眼睛的嘴呢?它们似乎只会说一种腔调,并且只说英语。而耳朵则有些听力问题,尽管有很多先进的助听设备。”
爱德华兹直言不讳地表示:
“我认为,澳洲人们还不适应自己比亚洲人更虚弱、更贫穷、更没有影响力——尤其是与中国人相比。我认为在管理澳大利亚政策和叙事的关键机构中存在着种族问题。许多澳大利亚领导人依旧幻想着自己在将专业知识和更好的原材料居高临下地交到心怀感激的北方(指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手中。”
“世界的变化比澳大利亚领导人能够理解的似乎还要快……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变了,即便我们的国家依然被白人东方主义者‘纡尊降贵地施舍穷人和棕色人种,指导他们’的幻想所主导……不知为何,今天的澳洲还是有很多身居要职的人以为澳大利亚不仅向亚洲提供了矿产资源,还提供了优越的知识和技术。是时候有人该告诉他们开张视听,好好向亚洲学习了。”
“我担心,我们现在的这批领导人正在削弱我们的中等强国的地位——每次我们的领导人开口说话,我们都在变成一个更小、更令人厌恶的国家。我们针对的是谁?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一个正在崛起的军事强国,以及我们最大的客户。干得好,贸易国。”
“我们现任领导人的视野被一层东方主义的面纱所笼罩,它受困于过时的种族主义和文化等级制度。而中国的崛起意味着我们需要非常、非常、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个国家。掀开东方主义的面纱,揭开‘竹帘’——我们目前似乎正竭尽全力闭目塞听——可能会使五眼更有效地工作。”
爱德华兹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与亚洲的女性和性别研究,但却比很多国际关系学者更能直击澳大利亚外交的要害。如果不是要退休了的话,恐怕她也无法如此仗义执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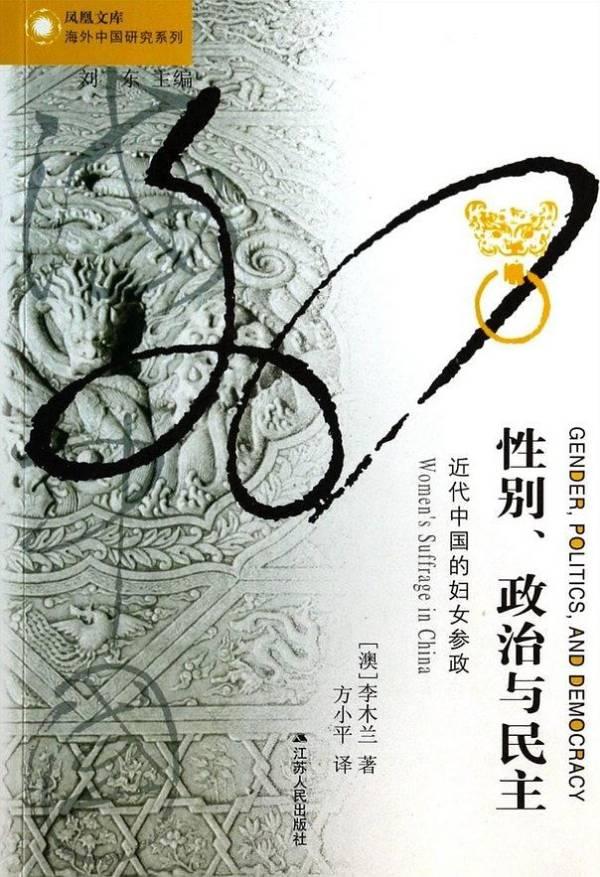
李木兰的作品
很多人正想要“新冷战”
爱德华兹和柯伦等人的批评是否“过火”,是否“冤枉”了莫里森?其实他们还多少有些“为尊者讳”呢。2019年5月莫里森意外赢得大选、正在欢天喜地之时,《对话》(The Conversation)新闻网就一不小心暴露了总理的另一面:虔诚到不行的教徒。在胜选时,这位总理第一时间感谢了“神迹”。
“莫里森的五旬节派基督教信仰(Pentecostal Christian faith)是理解他政治生活的核心”,《对话》报道称。该教派是20世纪初出现在美国的新教教派的一支,“它强调个人与上帝的直接联系为那些得救的人所专有,这导致了一种相当二元的世界观:有得救的和被诅咒的,有正义的和邪恶的,有虔诚的和邪恶的。”
“在五旬节派的这种排外观点中,耶稣是唯一的救赎之路。只有那些被耶稣拯救的人才有希望在天堂获得永生。在最好的情况下,它能使人谦逊;最坏的情况是自命不凡和傲慢自大。只有重生的基督徒才能得到救赎,穆斯林、犹太人、佛教徒、印度教徒、无神论者和非重生的基督徒都注定要在地狱的折磨中度过永恒的时光。”《对话》称。
这种信仰有助于解释莫里森为何敢于不顾一切地对抗中国。从现实主义的视角看,这位总理的蛮干劲头几近不可理喻,但从一位教徒的角度出发,就不难理解了:莫里森似乎认为自己已经被上帝选中,正引导着澳大利亚走向应许之地,这足以让他在水面行走、使死人复生,化一切不可能为可能!

在澳大利亚2019年即将举行大选的背景下,莫里森开通微信公众号。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有这么一位“受困于过时的种族主义和文化等级制度”的总理,盘踞在大位上的头脑和智囊们自然也就将澳大利亚历史中最阴暗的沉渣统统“发扬光大”了。理智的、至少有健全知识的外交官和中国问题专家们靠边站了,ASPI这样的反华军事游说团体和口无遮拦的反华后座议员们大行其道,中澳贸易的冲击波丝毫影响不到他们,他们对中国的真实情况也是一无所知。堪培拉也许真的想不通,面对高贵的“英语民族”的怒火,中国人为何不仅不惊恐万状,竟然还敢反击?
当然,也不能将澳大利亚的蛮行全部归因于种族主义和愚蠢傲慢,毕竟就算是再无脑的人,也不可能相信所有关于中国的谣言。从“中国渗透”、“中国威胁”到“中国出口禁令”,无非是为两个目的服务的:首先,转移人们对澳大利亚社会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的愤怒;其次,争取澳朝野对美国亚太战略的无条件支持。今年早些时候,《澳大利亚金融评论》的安德鲁•克拉克就指出,莫里森身边的一些人认为,他可以在下届联邦选举中使用“中国牌”作为他的王牌。
至于另外一些人,包括澳大利亚一些最知名的战略分析师,则早就迫不及待地宣称“冷战2.0”已经开打了。在与捉摸不定的恐怖主义进行了近20年的斗争之后,他们无比渴望像冷战时代那样,再次树起一个实实在在、清楚明确的意识形态对手。对澳大利亚、乃至对整个西方来说,“冷战”意味着美好的旧时光:对手最终分崩离析,柏林墙倒塌了,西方领导人们喜气洋洋地在圣诞节宣布胜利。这些难道不比小心翼翼地走钢丝更吸引人吗?
至少堪培拉目前似乎真的是这么认为的。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






















评论